美国维斯大学王敖博士的《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图学、制图学与文学》旨在探讨中唐地理学发展与文学空间想象多重互动的力作,近来由王治田博士译成中文出版,为还原唐代文人的空间想象、推动文学地理学的深度互动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启示。
本书选择的时期主要是德宗、宪宗统治的中唐,约在790-820年代之间。经历安史之乱的动荡,唐王朝多方面的秩序处在重整和新变之中,不断涌现的地理著作,即是文人面对帝国复兴挑战的一种回应。本书第一章概述了中唐及其之前地理学的发展状况,尤其指出贞元、元和间类如贾耽《华夷图》、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著作的修纂,体现出时人欲借“版图地理”之知识“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的努力。除了这些直接的地理文献,中唐文人对帝国空间的探索意识还体现在其文学创作中,这对中唐文学的新变和发展也形成一种推助力量。
唐代地图集大图和注释文字于一身,阅读地图成为一种观看方式。第二章聚焦中唐文人的阅图经验,考察其对中唐文学空间想象的影响。这一思路重视地图被悬挂或铺展观看的物质属性,将观看“大图”视为形塑文人空间想象的重要方式。但同时,研究也会遭遇阻碍,即唐代的地图文献在今天留存下来的并不多,如何以实证性文献证明中唐文人观看世界的视角受到制图学的影响? 作者的策略是,把握文学与地理的“类同”与“互动”,即基于当时文人和地理学者理解、观看世界的认识论的相似性,比勘文学文本是否存在被影响痕迹。本书重点探讨了贾耽的《华夷图》及文人观看相似“大图”时所作的诗歌文本,由此勾勒时人空间想象与地理学的关系。如果说传统绘画的卷轴形制隐含着时空延续、展开和无限流动的观念(蒋勋《美的沉思》),那么地图观看则强调“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的宏观视野,如此才可明确山川地理之形势,突出帝国包揽四极的阔大空间。作者由此视角出发,解读了李贺的《梦天》诗、柳宗元的《游黄溪记》等,发掘地图阅读对其空间想象的启示,为重新理解文本提供了新的视角。
如果说“大图”启发了中唐文人空间想象的方式,那么唐代丰富的图经则为文人官员提供了重构“地方空间”的知识来源。图经是隋唐时兴盛的由朝廷组织、地方编纂的地理著作,是历代累积的地方知识的汇集,“辅助并象征了朝廷对地方空间的统治权”。中唐文人往往毫不讳言对地方图经的参考,有时在体例上也会明显借鉴。本书第三章聚焦中唐文人面对帝国秩序在地方的动荡和断裂,如何借助图经完成传统的接续和政治意图的表达。阅读当地图经,一方面是文人官员流动至新任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重构地方空间的有效依托。作者以颜真卿的抚州碑铭为例,考察了颜氏借图经知识重建当地道教信仰传统、并将其置于皇权保障的文化谱系之下的过程,这不仅履行了地方官职责,也巧妙利用文学叙事达到了树立朝廷权威、宣扬教化之目的。此一思路,也同样适用于厅壁记、祝文等公文性质的文学体裁。如柳宗元《武功县丞厅壁记》、刘禹锡《和州刺史厅壁记》等,皆是利用图经达成官方叙事、寄寓政治批判的例子。而作者对中唐时大量出现的祭神祝文的探讨,则进一步体现了文人官员通过参考地方知识重构当地信仰空间的复杂过程。
第四章转向私人领域,以山水游记为中心探讨中唐文人在帝国“南荒”开辟新的地方空间的努力。本书的“南荒”,指8世纪中叶以前尚未充分开发的南方地域(如岭南)。对地理空间进行探索并改造为宜居性空间,既是中唐文人的个体需求,也是变动的帝国背景下激活新地标、创造新的地方传统的群体性行为。作者指出,大历文人元结通过对道州山水的命名,将自己的记忆和价值观附加其上,一方面是作为移民建立个人居住空间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将“个人家园的重建与王朝复兴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大唐中兴颂》即是将个人家园置于帝国广阔统治空间之中看待的显著案例。这种对地方空间的重塑,在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中唐文人那里得到继承。作者认为贬谪文人对南方空间的开拓,实际是早已开始、并持续在进行的地理变迁史的一个节点,游记中的文人主体已从一个游览的“局外人”变为积极改造空间的“参与者”,从而为“驯化荒蛮的帝国南部边疆”作出了集体性努力。
时间与空间向来是诗歌必不可少的要素,探讨地理和文学更为“亲密”的关系,还当从外部视角深入内部表情达意的艺术技巧层面。本书第五章聚焦中唐诗人元稹与白居易,探讨空间在元白唱和及其友谊维系中发挥的作用。作者指出,元白诗善用空间技巧以辅助诗意表达。如元稹《骆口驿》以“通蛮服”、“草御文”、东川看月等三个蒙太奇式的画面勾连起帝国南、北、中广阔的地理空间,既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也将“个人情谊转化为更大层面上对朝廷的热忱”。而在白居易《洛中偶作》中,长安、江州、忠州、杭州、洛阳不仅客观记录了他一生所经历的帝国空间,也成为他组织自传性诗行的要素。这一技巧在元白长篇唱和诗中得到更明显的体现。长篇、排律、次韵,每一项都对诗人的知识武库和诗学技巧提出不小的挑战,作者以白居易《东南行》和元稹《酬东南行》对读,指出元稹答诗有意使用空间对举的“双联”技巧,将江州和通州的地理信息并置、对照,这样既可在修辞上满足对仗要求,又能保障诗行持续推进;而在诗意上,则将天各一方的友人置于亲密互动的诗学空间中,同时又与北方腹地形成对比,强调两人同处南方边地的相似境遇。元白友谊,由此被进一步凸显。作者还关注到,空间对元白诗歌的传播也发挥了作用,时人乐于以不同空间“诗学同步”的戏剧性场景称道元白的默契。如白行简在《三梦记》中,就以唐传奇形式,讲述远在四川的元稹梦到白居易在长安游赏,而白居易在长安也同时怀念元稹,二人现实行迹又都恰如对方所写,这种刻意营造的“异地同步”的神秘效应,可见出地理空间在元白友谊塑造中的关键角色。
总之,本书对中唐语境下文学与地理的互动作了多元而深入、富有启示性的考察。中唐地理学的发展促进了文人地理意识的高涨,也丰富了文人的空间想象,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将地理知识、视角融入文学写作,既回应了动荡中的帝国社会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也在某种意义上推助了中唐文学的新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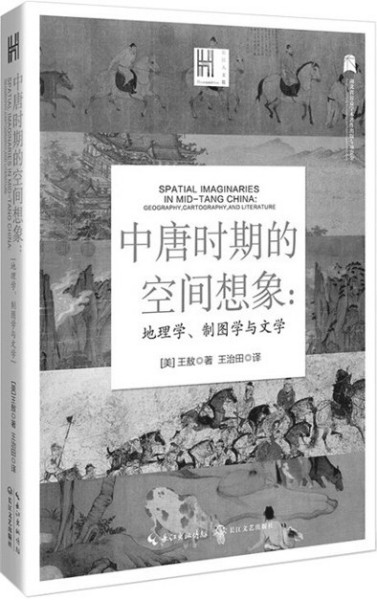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