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瀚光
最近读到吾淳教授《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感慨良多。这不光是因为作者是我近四十年的老朋友了,看到他退休之后仍有如此分量(近50万字)的学术专著问世,着实为他感到高兴;更是因为此书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哲学史上科学与哲学互动发展的详细轨迹,揭示了中国古代科学哲学思想的丰富多彩和精湛深刻,并由此拓展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空间和新领域。
大家知道,在我们现行的学科体系中,科学哲学是一个二级学科,以前称为“自然辩证法”,现在改称“科学哲学”,下面又分为“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等研究方向。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科学哲学这一学科领域里,尤其是在各个高校的教学体系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唯有西方科学哲学的教学内容和教材(例如库恩、波普尔、拉卡托斯等的科学哲学著作),而未有中国科学哲学思想的一席之地。那么,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哲学思想呢? 这是吾淳教授这部《古代科学哲学卷》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四年前笔者推出《中国科学哲学思想探源》(《周瀚光文集》第一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出版)时,也遇到过。我当时曾旗帜鲜明并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哲学对于自然知识(广义科学)曾经有过非常深刻的形上学反思和认识论探索,提出了一个由“道—意—言”三者构成的三个世界理论。在中国哲学的语境里,道(这里主要是指道家的道)是客观本真的世界(第一世界),意是人类对道的认识(第二世界),言则是对这种认识和领悟(意)的表述(第三世界)。“道—意—言”三个世界,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整个过程。人类一方面可以通过观察、分类、归纳、推理等各种方法去了解和认识自然,另一方面却由于其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相对性,又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了解和认识自然;语言一方面能够用来表达人的思想和意识,另一方面却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局限,又不能够完全准确地表达人类对于自然的领悟和感受。所以,“言不尽意,意不尽道”就成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常态。然而尽管如此,人类还是要用自己的意识去领悟那个道(自然),还是要用语言去描述自己对道的认识(意),而科学知识也正是在这种道、意、言三者既统一又矛盾的运动中得到了积累、提高和发展。人类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既能够认识又不能完全认识,语言对思维和意识既能够表达又不能完全表达,这样的深刻认识和辩证思维是中国哲学对科学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
其次,中国哲学在具体的科学学科方面也有很深刻的反思和论述,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国古代的数学哲学思想。《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中,就提出了一个“倚数—极数—逆数”的数理哲学思想体系。其中“倚数”是倚靠数学方法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思想,“极数”是穷极数的变化规律的思想,“逆数”则是运用数术去预知未来、预测吉凶的思想。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孙子算经序》说:“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万物之祖宗。”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说:“数与道非二本。”这都是对数学本质的哲学界定。
其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在认识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不仅提炼并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科学方法论模式。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曾经提炼并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学方法,例如《周易》的取象运数,孔子的举一反三,庄子的技进于道,孟子的苟求其故,《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吕氏春秋》的耕之大方,《九章算术》的由问而术,张仲景的见病知源,孙思邈的博学精思,沈括的验迹原理,徐光启的责实求精,宋应星的穷究试验等等,而这些科学方法又都具有勤于观察、善于推类、精于运数、明于求道、重于应用、长于辩证这几个主要特点。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科技的几个主要学科例如数学、天文、医学、农学等,还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共同遵循的一般科学方法论模式,那就是“实际问题→概念方法→一般原理→实际问题”,即首先从生产和生活中提炼出实际问题,然后提出相应的概念和方法去解决它们,再在这些概念方法的基础上抽象出一般原理,最后再把这些一般原理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方法论模式主要是一种科学发现的方法论而不是科学证明的方法论,这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古代何以能有那么多的科学发现、发明和创造。(参见周瀚光《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以上这三个方面,只是我提纲挈领、蜻蜓点水般地对中国古代科学哲学思想所做的一点简要的举例。详尽而系统的论述,则请读者们阅读吾淳教授的这部《古代科学哲学卷》。
在这部书中,作者按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与三代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再到宋元时期,最后到明清时期,对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互动发展和相互影响,做了极其细致的梳理和非常完整的论述。其内容既涉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命题、概念、范畴等重要思想,又涉及中国古代科技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学、农学等具体学科。与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专门著作相比,此书是迄今为止涵盖中国古代历史时期最完整的一部。李申教授曾于1989年出版《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其论述的历史跨度自原始思维至魏晋南北朝。本书则不仅涵盖了自原始思维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段,还涵盖了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宋元和明清时期,涵盖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时期。与以往的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著作相比,此书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与哲学思想相关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发掘、剖析和深化,凸显了古代科学发展对哲学思维的促进和影响,以及哲学思维对科学发展的反哺和引导。
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此书是中国哲学史著作中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互动发展的全景式通史类著作,是对以往中国哲学史研究空间的突破和拓展,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学术意义。
作者在此书的“导论”中说,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注视始于20世纪80年代攻读硕士阶段,那是因为深受恩师冯契先生观点的启发”。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张岱年、任继愈、冯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就提出要摒弃原来那种认为哲学思维就是来源于阶级斗争的片面观点,要求对历史上哲学思维与自然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做详细的考察。他们不仅积极呼吁,而且身体力行,一方面亲自撰写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另一方面则在研究生招生时新辟“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这一研究方向。冯契先生在这方面着力尤多,连续多年招收、指导和培养这一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我当时刚从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即被冯先生招入麾下,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协助他做一些这方面的教学辅助工作。为了让这些研究生们有一个良好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方面的知识基础,当时专门去请了著名科技史家胡道静先生来讲授中国农学史,请了著名物理学史家袁运开先生讲授中国物理学史,请了著名医学史家傅维康先生讲授中国医学史,等等。吾淳教授在他的这部《古代科学哲学卷》里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各个学科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时打下的中国科技史学科知识方面的坚实基础。
在冯契先生的引领和指导下,我们当时与国内外科技史学界的著名学者建立了广泛而紧密的联系,还主持举办了一系列专门探讨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学术会议。每次会议,吾淳教授都积极参与,筹备策划,讨论观点,出力多焉。1990年代初,袁运开教授和我合作主编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吾淳教授担纲撰写第一章“原始社会时期科学思想的萌芽”,洋洋洒洒5万余字,发前人之所未发,令该书大为增色。这次对照阅读他的新著第一章,发现许多论述比原来更加深刻、更加系统、更有内涵了。再以后,吾淳教授不断开辟和拓深他的研究领域,不断有新著问世,而且每次都把他的新作寄赠给我,让我先睹为快,受益匪浅。
总而言之,吾淳教授这部《古代科学哲学卷》凝结了他近40年来锲而不舍的研究功力,是对冯契先生所提倡和开拓的“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这一研究方向的最新总结性成果。冯契先生后继有人,当可欣慰。我作为吾淳教授的老朋友、与他一起探索的同路人、亲睹其一路奋斗的见证人,实在是不胜感慨,与有荣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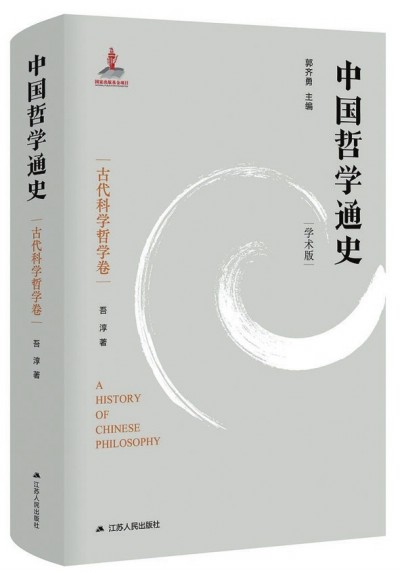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