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留欧生涯的开启正处清末“新政”时期,清廷推出的“仿行立宪”、倡导工商、兴办新学等一系列举措,虽无济于改变清廷灭亡的命运,但却激发了民间和学界的活力。在当时,经由此前洋务运动兴办新式学堂、译介西书,以及甲午战败后大规模兴起的留学潮,大大推进了“西学东渐”进程,“救中国必以学”的使命更为突出。蔡元培断然放弃世俗社会的地位尊荣,于不惑之年远赴“世界学术德最尊”的德国求学。这对于当时业已“进士及第、储才翰林”的他而言,远不止于兴趣驱使那么简单,有如此气度,非常人所能为也。
叶隽推出新著《蔡元培的留欧时代》,对辛亥革命前后,蔡元培赴德、法两国留学的那段历史进行了详细剖析。读者一路阅览下来,对清末民初之际留学先驱的所思、所行会有置身于其中的感触和认识。
蔡元培先后赴德留学、赴法游学 的 时 间 段,前 者 为 清 末(1907-1911),后 者 为 民 初(1913-1916),一前一后恰好形成对称。前者,蔡元培秉持“救中国必以学”的信念,在世界学术最为尊的德国,“异域求知苦做舟”,与孔好古、冯特、兰普莱希特等重磅级学者深入交流,吸收西方文化之精髓,并对德国教育有了切身体验与深刻认识。德国留学,多是汲取新知,并为此后的教育事功遥作铺垫。后者,既是出于对辛亥革命之后“道德沦丧、官方败坏”的失望,更是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筹办刊物、谋划教育、组织勤工俭学、从事著译等,样样做得有声有色,且极具开创意义。法国游学,更多展现事功,无意间也为此后回国大展宏图做了很好的预演。并且,一前一后,促使其回国的乃两大重要历史事件。前者是民初建元,百废待兴,蔡元培回国后即担任了教育总长,后因对袁世凯不满而愤然辞职,再度赴欧。后者则是袁世凯复辟丑剧谢场,“国事渐平,教育宜急”,再度经历欧洲游学的蔡元培被电请回国,正好一展身手。时代选择了蔡元培,蔡元培也必以赫赫教育事功回报时代。
作者对蔡元培先生作为“多维留学人”的客观定位,有助于客观梳理蔡元培的学识精进,亦有助于对留欧时代的蔡元培予以更为准确的评价。叶隽曾提出“一元留学人”与“多维留学人”这样一组概念区分,前者指留学国别为单一国家的留学生,后者则指留学国别至少为两个国家的留学生。蔡元培显然属于多维留学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先后留学德、法两个国家,也在于他留学期间于学无所不窥,广泛涉猎哲学、教育、心理、历史、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学科专业,并与当时德法两国的文化巨子、政界名流等均有深度交流,从而具有了宏大格局和广博视野,并由此对中西方文化有了更为深远的认识。就此而言,在当时可与之比肩者,似乎唯有陈寅恪等少数人。
“进士及第、储才翰林”所蕴藏的深厚旧学渊源,再加上“多维留学人”经历赋予蔡元培的广博而又深厚的西学素养,使蔡元培有着最不为世人所动的文化眼光和历史洞察力,从而既不同于后来的“全盘西化”,亦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更不能就此说蔡元培采取的是简单折中主义或一般意义上的中庸立场。“他关注的显然是中国文化如何汲取外来文化而获得自身凤凰涅槃的可能,但却并非仅就中国而论中国,而是纵横捭阖,古今中外,从广泛的世界经验中汲取精华。”(p334)在中西方文化激荡的清末民初时期,若无蔡元培这样的文化见识和胸襟气度,是不能成就此后北大“网罗百家,囊括大典”之气象的,也正是蔡元培“在北大这所具有象征性的中国首席高等学府中将历史的开创和传统的承继成功地组合在一起”,从而开创出一个先秦诸子时期那样文化灿烂的新时代。如果蔡元培没有前后两次的赴欧留学,很难说他能够成就后来赫赫有名的教育事功。
传记文学式的叙事研究手法,使得该书文字活泼生动,可读性强。作者择取传记文学式的叙述,我认为凸显出如下三点特征。其一,在生动的文字叙述中,还原研究对象的生活经历和所思所行,拉近了读者和研究对象的距离。文中并不避谈蔡元培生活困顿之际所采取一些为稻粱谋的做法,以及蔡元培在收到袁世凯汇款后采用的“太极推手”,从而再现出一个真实可信的蔡元培。其二:学人写学人,此种定位于“叙事研究”的传记文学式写作,乃是在留学史、德国文化研究领域著述颇丰,并且同样有着留德、留法经历的学人,对一百年前留德、留法先哲的追溯和梳理,当事者和作者在年龄上同样近似,从而也形成有趣的时空对称。其三,于传记文学式写作中开展研究,发挥学者型作家的专长。突出体现在敏锐的问题意识,作者于文字叙述中的穿插提问,既标示出研究的向度与深度,也是提示读者与之一同思考。在其中,作者于庞杂的史料间,蹚出一条探寻路径,发现许多尚未为人所发现的细节,揭示出蔡元培先生学识、事功背后的渊源,从而在此种意义上丰富了蔡元培研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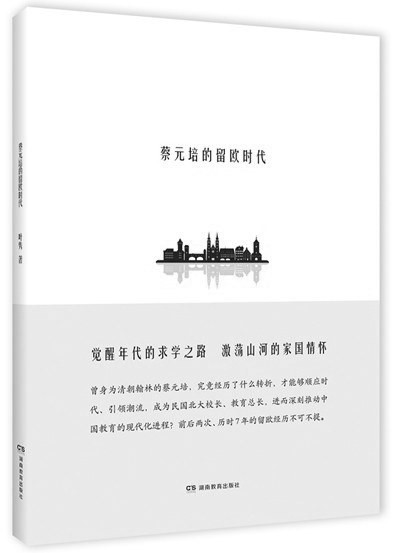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