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的镌刻是为了统一文本,有利于国家官吏的选拔。东汉光和六年,历经八九年的熹平石经刊成后,因当时尚无椎拓技术,纸张亦不普及,各地士子只能千里裹粮,辐辏洛阳,终日摹抄。六朝后期,掌握了椎拓方法,于是有一字石经拓本行世。魏徵接收整理隋朝皇家图书馆书籍,有不全本的熹平石经拓本七种,这些今文经本在古文经盛行的隋唐,已属珍贵文物,因为熹平原石刊成不久即遭损毁,之后数百年中,迭经战乱,一再迁徙,有改作精舍石材,或用为营造柱础,至唐已十不存一。可惜的是,传至中唐,不仅仅存残石混于瓦砾之中,连皇家图书馆保存的拓本也流散不知所终。北宋嘉佑间,洛阳掘地建筑,不时发现残石,好事者椎拓传观,视为古董玩物。石经不仅有文本价值,亦有汉隶字体价值,更有文物和怀古读经的文化意义,故三二有识之士,或取监本略作考订,视其异同;或摹录字体,以作楷式;亦或椎拓残石行款文字,翻刻新石,树之学宫。七八百年之后,此类考订文字、翻刻片石,摹录拓本多已澌灭无存,偶有一鳞半爪,即成鸿宝。清人的考证,只在洪适《隶释》所录文字上求索,而熹平汉碑经本和行款形态,就一般人而言,已是海客口中的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洛阳继大块三体石经(魏石经)后,又挖掘出百余块熹平残石,罗振玉率先指出其中一小石系《论语·尧曰》篇残文,马衡因亲往洛阳购得近百块,故又检出一块可与《尧曰》相拼接的残石,并写出第一篇汉石经考证文字——《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跋》,揭开了收集、传拓、研究熹平石经的序幕。此后十余年间,王国维、罗振玉、吴维孝、孙壮、吴宝炜、文素松、张国淦、关百益、屈万里等均先后作过校录、影拓,出过专著,更有钱玄同、方国瑜、陈子怡、刘节、吴承仕、郭沫若、胡小石、王献唐、余祥森等投入精力,撰文考证,使石经成为一时显学。
王国维1916年撰《魏石经考》,涉及汉石经文字、碑式,其对石经的开拓和石经学的建立,堪称首功。马衡于1919年因请教石刻与王国维缔交,之后即有书函往返讨论石经。王国维北上执教清华研究院,马衡与之往来更频,交流石经考证心得亦愈密,如《仪礼》所属家法文本,《鲁诗》章次空格行款和《小雅·采薇、出车》篇文字等。王国维自沉后,马衡继续收集新出汉石经残石拓本,并从孙壮议编次《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为罗振玉考订和张国淦复原奠定了基础。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搜罗宏富,是汉石经不可忽视的名著。张国淦参据罗书,撷取清孙星衍、李富孙、冯登府、皮锡瑞等人的今古文考证成果,第一次将一千七百多年前的石经做了复原,初步展示出熹平石经碑式和汉代今文文本。尽管罗、张的文字考订和碑式排列有诸多可商之处,但凭借六七千字残文复原二十多万字的七经碑石,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式工程。
张国淦《汉石经碑图》出版,兴盛一时的石经研究高潮渐渐落幕,只有个别如罗振玉、屈万里等少数人继续在收集研究。马衡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身份,在当时也是一个石经圈的中心人物,不仅曾亲往洛阳收集残石,更与王国维有较多的切磋机会,使得他既拥有大量拓本,又握有真正的残石,且其在古器物教学中引进石经一类,所以对石经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片面到较全面的认识过程。比如他最先定熹平所刻《论语》为鲁论,为学界所称道。后孙壮遗以大块《周易》残石拓本,他又撰文考定熹平《周易》用京本《易》,虽有钱玄同竭力表彰,并不为人认可。至四十年代,他又看到《周易》校记残石,证明确是用梁丘本《易》,乃作文纠正。总之,当时马衡虽身居要职,行政事务繁忙,无暇专心全面整理石经,但对石经研究动态却一直予以高度关注。
人生得失,很难一概而论,当其执掌北大考古学研究室和故宫院务时,忙于教学和播迁文物等事,无暇深入研究石经;及至五十年代因故受审查,随即离开故宫赋闲,有了整块时间,使其萌发了整理三十年来积累的汉魏石经拓本想法。在马衡之前,汉石经已有罗振玉和张国淦两位的成果,魏石经虽有王国维、吴宝炜、陈乃乾、白坚、章太炎、孙海波等研究成果,但马衡与王国维共同商榷补缀的整块《尚书》《春秋》碑石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王国维自沉,马衡曾抄录其《魏石经残石考》,发愿要为朋友续成写定,但此時他还是“先整理熹平石经”,将魏石经工作放在后面。
从马衡日记考察其整理过程,自1952年7月下旬至1955年2月,前后两年半时间中,可粗略分为十多个各有侧重的时段:先是整理自己所藏拓本,随拓本排列而考释;次取许光宇藏拓,孙壮、吴宝炜所编《集拓》,对照校勘、增补、考释,并重新复校一遍;次取罗振玉《集录》对校、增补、修正;又检寻出碎石多块,插入后再重新校阅一过;之后李涵础、许稚簧送来藏拓一批及罗振玉《六经堪》拓本,不得不再重新校录一次。经过反复校勘、增补,乃取清人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和胡承珙、徐养原两家《仪礼异文》校文字异同,取洪适《隶释》所录残石文字补入《集存》。再走访北京图书馆,冀有所得,但却徒劳无获;访张国淦,张赠送《汉石经碑图》一册,并嘱其将碑图方位补入残石序号之后,马衡似未实际操作。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二月初,撰写《概述》成,至此《集存》基本完稿。此时马衡深感“病后文思枯窘,精神不集中”,体力不支,故未逮清抄成定稿,即着手整理魏石经,可见其欲成此两书之急切心理。
由于马衡未清抄成定稿,所以其逝世后陈梦家、陈公柔等接手整理时,“原稿皆为散页,中为拓本,下注释文,而考释朱笔散记在四周,每一经编号为次”。所谓每一经编号为次,若《鲁诗》1970字,编号1-37,校记5号,无所属9号;《尚书》802字,编号1-22;《周易》1171字,编号1-20,校记2号,无所属1号。七经各自编号,总数为518号。1957年出版时统一编为520号,是加进了原无拓本的《隶释》《隶续》和马衡“有考释而未附拓本”者,这些拓本来自罗福颐的家藏。可见今本是经过陈梦家等增删合并重排的结果。
马衡《集存》成书晚于罗振玉《集录》和张国淦《碑图》二十多年,在参考、吸收罗、张两书优点基础上,无论是残石经文的考订和归属,还是文字的隶定、篇次的排列,都有青出于蓝的超越。加之罗福颐贡献拓本,陈梦家整齐全书,使其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出土汉石经残石以来的集大成之著。
《集存》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有人辗转从香港带到台湾。1976年,台湾联贯出版社和艺文印书馆分别影印发行,艺文还将编撰者改为“马无咎”,并不断印刷。屈万里学生重新复原汉石经和其他台湾学者所用多为艺文翻印本《集存》。相反,大陆学者利用率不是很高。笔者深感《集成》对汉代今文经本研究和出土文献对勘有唐石经和宋刻本无可替代的价值,故在承担“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项目伊始,率先影印此书,旨在让更多学者利用。影印时加入当年陈梦家因仓促未找到的第七二、第三三四号两张和马衡在《概述》中提到的熹平石经后记两张拓本,而溢出《集存》之外如关百益《残字谱》中的拓本无法补入。原书《周易》残石拓本系缩小影印,这次将之分割六块放大,俾清晰观赏文字点画。我在书前撰写“马衡与汉石经研究”一文,帮助读者认识、理解这位为汉石经付出极大心力的学者和本书编纂过程及其价值。由于撰文时《马衡日记》尚未出版,于其整理过程略有遗漏,这次趁重印机会,参据日记,补充作者撰作此书的某些细节,应该说较全面地反映了马衡先生与汉石经的因缘和《集存》编纂全过程,相信对读者利用此书有所帮助。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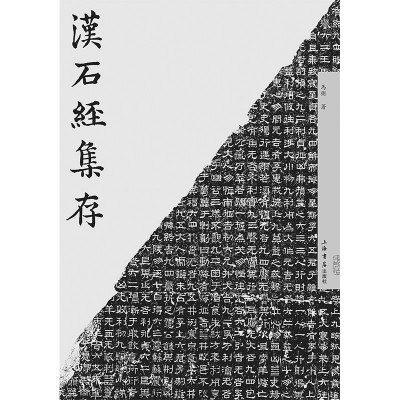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