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9日,四名北大青年学子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正式团员,兴致勃勃地随队踏上万里西行的征途。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位,是年仅19岁的理预科二年级学生刘衍淮(1907—1982)。正是以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为契机,刘衍淮的一生事业都与中国气象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时隔九十年后的2018年,刘衍淮先生之女刘美丽、刘安妮女士将流传海外的刘衍淮生前文物与文献无偿捐赠给了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其中包括11册弥足珍贵的日记手稿。2021年8月,经过重新整理的《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日记记事始于1927年5月9日,迄于1930年4月19日,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作者为期三年的西北科考经历,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气象组成员目前仅见的完整考察实录,更堪称刘衍淮作为一代气象学宗师在学术起步阶段的成长史。
一
气象观测是西北科学考查团工作的重中之重,刘衍淮等人最初就是以气象生的身份遴选入团。《日记》清晰展现出他在考察团中从事气象观测工作的三个阶段:1927年5月至8月,在包头北部呼加尔图河畔,随德国气象学家郝德(Waldemar Haude)学习测量方法,并开始实际操作;1928年3月底前往博格达山中的福寿山气象台作高山测量;1928年5月下旬至库车建立气象站,进行为期一年多的气象观测——除了行进途中,以及在哈密、乌鲁木齐等地的短暂停留,刘衍淮的西北科考生涯几乎全部都被“丝路风云”所占据。
考查团还在包头驻扎时,刘衍淮就已经开始学习使用气压表、寒暑表,进行一些简单的气象观察。作为赫德的助手,他从包头出发后,途中主要负责安置仪器、记录气候数据。赫德非常乐意指导这位勤奋好学的中国学生,不仅教他记热度数、用湿度表、填写气象报告等,还给他赠送气象学著作,鼓励他自己做测量。刘衍淮自身也异常努力,在呼加尔图河畔临时气象站,他每天早中晚三次记录百叶箱的气候变化数据,坚持抄录、翻译德文指南(Anleitung),自学《气象记录仪原理》(Mc Adie:The Prin⁃ciple of Aerograph),很快就能够自己独立工作。1927年7月21日考查团大队继续西进,刘衍淮与外方团 员齐 白满(Eduard Zimmer⁃mann)、马山(Wilhelm Marschallvon Bieberstein)暂留呼加尔图,继续完成7月份的气象观测。对此刘衍淮感到特别兴奋,一丝不苟地对待郝德交待的任务:“这气象台完全是我的事了,所以七点钟就起来了,自己作这一切的观测。”(1927.7.21)这个新手的实践水平显然已经不在两位外人之下,他在日记中记载:“我今日试风力多用风力表Windmeter,因为在自己的手下,今日之后的看气象是独立了的了,不是随着人家看的了。老齐不比我高明,他笨得很,他的其他的事情又多,所以这整天的事情都让我作了。”以实际行动回应了外方团员认为“中国人没有用”的偏见(1927.7.22)。
在博格达山进行高山气象观测期间,其时已至初春,但山中还常常下雪,条件艰苦。起初刘衍淮和马山搭档工作,后来马山提前离开,仅留下他一人独守空山。短暂的山中生活,对刘衍淮来说也是一次身心的考验。1928年5月,考查团派刘衍淮与德国人华志(Franz walz)到库车开展气象观测工作,6月初到达库车以后,刘衍淮便马不停蹄地着手建立气象站,投入气象观测工作。华志在库车时常外出考察,所以气象观测基本都是刘衍淮独立承担的,有了前期的积累,他的工作可谓得心应手。
刘衍淮每个月都要将采集到的气象数据做成报表,定期寄送赫德与南京政府。对待这些看似简单机械的工作,他也时刻保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如《日记》所写:“我又抄了张月表,备寄南京,发见十二月份最低温度负十五度下之度数,订正错了。夕又差人到邮局讨回给郝德的信,改正了这几张月表。”(1929.1.6)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坚守下,刘衍淮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由一个初学者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气象观测员。1928年9月华志回国,不久后考查团从迪化派来新招收的本地气象生张广福协助刘衍淮,刘衍淮又在距库车90公里处的喀拉古尔山中建立了一座气象台,指导张广福在此地测量山中气候,从而使库车地区气象监测工作在他离开之后还能够得以延续。
在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队伍里,以刘衍淮为代表的中国学生们凭借他们聪明好学的态度、踏实认真的工作,赢得了外方团员的赞誉与尊重。除了学习气象学知识,刘衍淮不放过任何一个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在考察途中,他一路都跟随斯文赫定学习如何在驼背上作路线图。在博克达山里,他一边例行记录山中风云变幻,一边学习《德文轨范》等著作,这些都为他日后学术道路的发展与开拓,奠定了全面而良好的基础。1929年1月31的《大公报》中专门表彰了刘衍淮等人的工作:“吾人最所满意者,此次参加该团之中国学生,皆努力工作,表现优美之成绩。”认为他们“重实习,耐劳动,屏绝世俗之嗜好,以探求真理为第二生命。一如此次考察团学生之所为,青年风气如此,革命成功之路也”(《大公报》1929年1月31日第二版)。也正因有如此优秀的表现,在考察接近尾声时,斯文赫定和郝德推荐刘衍淮至柏林大学学习,他很快从一个大学预科二年级的学生,成长为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生,并最终应验了斯文赫定“深信李(李宪之)刘二君对于世界科学将有重大贡献”(《大公报》1931年8月14日第四版)的预判。
二
刘衍淮《日记》还以个人视角记载了特定时代背景之下在西北地区的社会闻见,虽然没有波澜壮阔的景观与事迹,但也不失为“丝路风云”之一面。斯文赫定曾经将西北科学考查团喻为一所“流动的大学”(A wandering university),身处广阔内陆边疆社会中的种种经历与遭遇,对刚走出校园的刘衍淮来说无疑都是人生的历练。《日记》中以下内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西北科学考查团1927年底即将进入新疆境内之际,曾受到新疆省政府的阻挠。12月15日,刘衍淮和马山先于大队出发,前往沁城(今哈密沁城乡)找轿子接应生病的斯文赫定,他们在路上与杨增新的部队不期而遇,被带往庙尔沟接受检查。对此刘衍淮毫不慌张,他主动与带队军官交流,率先了解到考查团受阻的隐情:原来考查团出发时,曾电告杨增新将在新疆建立气象台,“引起了新省回、蒙王公、愚人等们的怀疑,上公式给杨,请挡驾。及杨电到京时,我们已在途中,杨无法,以后只好就添派军警稽查,布置要隘。及我们到了爱金河上,又有侦探传说,我们重要人外,带有二百打手等等的话,杨更疑,布置更密,传檄各军队,集中于东路的卡子,对于来新中外人等严行稽查”(1927.12.26)。为此,他及时给考查团中方团长徐旭生去信告知原委,并出主意请其解决误会:“晨写信一封致徐先生,托米纶威带,上述新省人众对我们考查团误会情形,请其急往哈、迪去解释。”(1927.12.28)经过多方协调,考查团最终得以进入新疆。而在新疆考察期间,考查团又正好遭遇了杨增新被刺的“七七事变”,这一消息在7月11日传到库车。杨增新虽然一开始对考察团有所误解,当后来事实澄清后,又提供过不少帮助,因而考查团成员对杨增新多抱有好感,闻知此事的刘衍淮也不禁感慨:“杨居官数十年,一旦遭难,殊觉可惜。”(1928.7.11)当时库车地区对杨增新遇刺一事多有流言,刘衍淮则极力制止谣言的传播:“下人云街人言冯玉祥刺杨之谣,余力辟之,并给用人训话,警告慎言。”(1928.7.15)在以上事件的应对中,他都表现出异常沉稳的心理素质。
科学考察过程中自然不免与各色人士交往,刘衍淮《日记》中所记载与他往来过的新疆地方官员多达数十人。他们中有的仅是一时泛泛之交,有的则彼此结下了难忘的友谊,例如在《日记》中频频出现的库车邮务局长朱菊人。刘衍淮1928年6月19日初到库车时,即“同华乘马访邮局局长朱”。此后的一年多里,两人交往日益频繁,朱菊人对刘衍淮也照拂有加。1929年8月底,刘衍淮即将离开库车,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与朱菊人难分难舍的临别之景:“五时遣车先行,而并坐之三人,则仍不时啜泣。回库车之轿车亦遣之先去。后勉拭涕泗,与菊人互相劝解。……六点十分各上马,同出店门,握手作别,一东二西,分道驰去。时心已碎,回顾则已无所见。然情虽如此,不得不强颜为欢,心痛时则骤马极奔,聊以驱去伤感。”(1928.8.28)刘衍淮和朱菊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考查团成员与地方官员的交往中是一个特例。它一方面生动鲜活地展现出民国时期新疆地方官员的精神风貌,对刘衍淮个人来说,他也能够藉此深入接触、感受边疆地区的基层社会生活,潜移默化中得到为人处世的锻炼,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
作为一名在五四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日记》中所反映出刘衍淮的爱国之情,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政治敏锐性,成为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他在考察途中时常阅读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思考边疆“将来实业计划问题”(1927.11.17)。与友人的通信、新疆当地官员的传闻,甚至已经过期的报刊杂志,都成为他了解内地政事的渠道。当他从杨增新处听说“济南惨案”发生,日军出兵山东,顿感“家乡糜烂,闻之痛然”(1928.5.19)。他在库车读到《字林星期周刊》《东方杂志》中有关日军占领济南的消息,也久久不能释怀:“拿来五月份《东方杂志》,内载五月初旬日人在济南演出之空前惨杀。……触目伤心,惨不忍闻。”(1928.12.9)在1929年5月9日“国耻纪念日”这天,刘衍淮更是在日历上大书“勿忘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数字,同年5月30日的日记中,也特别标注了“上海惨案纪念”之语。很显然,刘衍淮的爱国情感在身处异乡的时空阻隔之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并在日后赴德留学、抗战卫国的生涯中一以贯之,这些都是他在西北科学考察时的收获。
三
早在1928年底,刘衍淮赴德留学事宜即已经提上日程,结束新疆气象观测任务之后,他取道塔城,经由莫斯科、拉脱维亚、立陶宛直接至德国,进入柏林大学学习。1934年学成归来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任清华大学地学系讲师。1936年,出任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气象教官及气象台台长。1949年12月,刘衍淮随军迁往台湾,在冈山空军气象训练班服役。1960年起,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主任,创立地理研究所。1978年荣休以后,又担任台湾地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与李宪之先生并驾齐驱,成为中国海峡两岸气象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当刘衍淮晚年回顾起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时候,仍将之视为自己事业的起点,而他的《日记》则成为对这段特殊人生经历独一无二的记录。正因如此,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同仁发愿对《日记》进行整理。
整理本《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问世之前,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员的日记先后刊布者已有三种。分别是《徐旭生西游日记》、《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和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记》。由于考察任务各不相同,这些日记的内容也各有侧重,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前三种日记相比,刘衍淮《日记》具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保留了大量第一手的气象观测资料。西北科学考查团收集的气象材料,后期均由赫德负责汇集整理,可惜的是部分资料还未及公布就毁于二战战火。刘衍淮《日记》中的相关内容则提供了唯一可资参考的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损失。他自己也曾说过:“中古西北科学考查团数十人跋涉万里,辛劳累年,耗金巨万,所换来的完整气象观测成果,遭遇了空前的浩劫,从此胎死腹中,永无问世希望。……所幸作者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时期所作的日记,完整无缺,其中不同西北地方的气象观测记载,可以摘录整理,公诸于世。”(刘衍淮《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气象观测结果》,《中国气象学会会刊》第7期,第26页)第二,正如前文所揭,中国青年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的卓越表现,是这次考察的一大亮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次史无前例的科学考察,为中国学术界带来中外平等合作、协力创新的重要经验。所以,这部西北科考途中的成长史,也向世人展示了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到科学考察的世界潮流中来,并如何借助这一契机,成为走向世界的科学先行者。
就《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的整理而言,也有诸多值得称道之处,并非是对《日记》稿本的简单过录。首先,整理者对日记重新分段,根据实际内容提炼出提纲挈领的小标题,加强了日记内容的逻辑性与可读性。其次,整理本中配入了大量的照片。这些西北科考时期的旧影,大部分都是刘衍淮旧藏或亲自拍摄,它们被还原到相应的日记文本下,使相关人事变得更加立体、生动。最后,整理本订正了稿本中的若干错讹,还给部分生僻词汇加上注释,以帮助理解。在此仅举一例,刘衍淮《日记》中曾两次出现“虎洞巴扎”一词:“下午五时骑马出,过大桥下而北西北行,折至汉城北城门入。出南门,经靴子、帽子八杂而至虎洞八杂。出回城到大街,东过大桥、邮局以及于水顺街流之区,方折归。”(1928.8.16)整理者们最初对这一“奇怪”的地名倍感疑惑,经过反复推敲,甚至询问库车当地居民,最终判定虎洞巴扎大概是刘衍淮凭语音记录下来的词汇。注中如是解释该词:“虎洞八扎:今库车老城区东部、团结新桥附近的龟兹古渡巴扎,‘虎洞’疑为‘古渡’音讹。”较为合理地解决了这个疑问。
以上细节的处理,都令稿本《日记》焕然一新,为读者走进上世纪初西北地区的“丝路风云”、走进刘衍淮科学考察途中的成长历程提供了一部可靠的“新史料”。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将愈发彰显出独特价值。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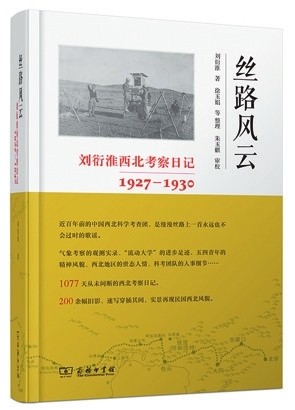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