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玲(Joanna Handlin Smith),美国著名汉学家,也是明清社会史研究的大家,《行善的艺术》为其代表作。作者在研读明代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晚明时期,众多慈善团体纷纷建立,一股前所未有的慈善热潮席卷了地方社会。韩德玲对这一现象产生了浓厚学术兴趣,随之开启了历时二十年的深入研究。在《行善的艺术》一书中,韩德玲指出,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争议的中国是否有慈善传统的话题已毫无意义:中国不仅有悠久的慈善传统,还有深厚的慈善思想。从对善会领导者道德和信仰的讨论到对粥厂和药坊日常运作的复原,从对地方社会资源的考察到对社交网络在慈善捐赠中作用的探讨,此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中国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生动画卷,也为我们了解晚明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以及宗教、文化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口。在该书中译本面世之际,我们约请译者曹晔对韩德玲教授作了访谈。
■受访人:[美]韩德玲(Joanna Handlin Smith,美国哈佛燕京学社)
采访人:曹晔(《行善的艺术》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曹晔:能否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当您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美国汉学界的情况如何?
韩德玲:自从1959年我开始上大学以来,美国的汉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59年,几乎没有美国的大学教授中文。事实上,哈佛大学以中文太专、太难为由,不鼓励本科生学习中文。在我念大学之前,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谈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哈佛大学的经历时写道,哈佛大学的中文教授们认为“十几岁的少年和大学本科生是不可能掌握中文的”。我是大一班上唯一报读中文入门课程的学生。
当时,对中国感兴趣的哈佛本科生可以选择在历史系学习近代史(大约从1800年开始)或者在远东语言系(1972年,该系更名为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学习前现代中国的历史。后者采用了一种可能被称为汉学的方法:它将语言训练与学习前现代中国(或日本)的所有方面——思想、宗教、文学和历史——结合起来,但它忽视了不同的学科方法。一门历史课仅仅按照时间顺序对重要人物和制度作一概览,没有对材料提出任何理论问题。一门关于中国文学的课程(以英文授课)同样考察了中国文学的伟大作品(如《报任安书》、汉赋、唐诗和一些元杂剧),但没有深入探讨这些作品的伟大之处。此外,文学概览并不重视小说作品,因为当时可以利用的译本据说并不准确。一门课程指定阅读《三国志演义》,但只教授中文,不作为文学分析的题目。事实上,在1959年,许多重要的中文作品还没有被全部或部分翻译成英文。如今,像《金瓶梅》《西游记》《三言》《拍案惊奇》《红楼梦》等明末清初作品已经有了优秀的英译全本。
在我获得了去台湾学习两年中文的富布赖特奖学金后,我于1965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攻读研究生。该系也采用了汉学的方法。由于关于中国的研究工具很少,斯坦福大学的课程花了大量时间来讲解汉语参考文献(从《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到“二十四史”),同样没有任何理论。如今,初学中文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超越这种训练水平,因为他们受益于一些辅助工具,如由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和房兆楹(Chaoying Fang)编辑的《明代名人传》(The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由贺凯(Charles O. Hucker)编辑的《中国古代官名辞典》(The Dictionary of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由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编辑的《中国历史新手册》(Chinese History:A New Manual) 以 及 由 魏 丕 信(Pierre-Étienne Will)编辑的《中国官箴公牍评注书目》(Handbooks and Anthologies for Officials in Imperi⁃alChina:A Descriptive andCrit⁃icalBibliography)等等。
比起研究中国历史的可利用资源的增长,更有趣的是,1959年以后,西方对中国历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最初,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们主要对政治制度、重大事件、杰出领袖和所谓的“伟大思想家”感兴趣。关于明代,他们关注的是明朝的兴衰和诸如监察、科举、税收和一条鞭法等制度,以及一些主要的士大夫(如王阳明、张居正)和宦官魏忠贤。总的来说,他们是从上往下看中国,尤其是看当权者(皇帝及其官僚们)是如何控制社会的。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明朝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将地方层面视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当时,西方学者认为慈善只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宗族可以巩固他们的权力,或者地方官员可以在资源匮乏时期防止起义。
1970年,《明代思想中的个人与社会》(Wm. Theodore de Bary and the Conference on Ming Thought: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出版,其中包括酒井忠夫的一篇文章,让西方人看到了晚明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变化。随着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我了解了王阳明的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弟子们,并第一次对酒井忠夫对学者精英所
做的关于“大众思想向上渗透”的重要研究有了认识。
在此期间,欧洲历史的领域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试图通过考察那些政治上无足轻重之人的生活来解释地方社会。
曹晔:您当初从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主修中国文学),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攻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主修东亚历史学)?
韩德玲:在斯坦福大学,我有幸和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一起学习,他是明末清初小说领域的大家。因为这个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还很年轻,所以课程作业必然是乏味的。注释文本很少。韩南认为研究像冯梦龙纂辑的《古今小说》这样的作品的第一步是破译每个术语的含义,识别故事的来源,并追踪文本关系。他的方法给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与此同时,我渴望思考这些故事的广泛含义,尤其是产生中国小说的历史条件。因此,我来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伟大的思想史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一起学习。(不幸的是,他在两年后的1969年去世了。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每次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时的兴奋。)列文森的方法与韩南完全相反。他从大的理论入手,并带着那些想法研读文本。最终,我从这些老师身上获益良多:细读文本的必要性和提出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性。
曹晔:跨学科的训练背景对于选择研究题目与分析方法是否有很大的帮助?
韩德玲:历史领域本质上是跨学科的。这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尤其如此,因为统治精英成员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他们从大量文献中提取词汇和概念,并经常提及古代文本。要理解明代的文本,我们必须对四书、唐诗,以及王安石、苏轼、朱熹等人的作品有所了解。我很感激有机会在斯坦福大学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一起学习中国诗歌,在伯克利和杜维明一起学习早期中国的思想。此外,通过阅读西方文学批评,我对如何识别可能有助于理解作者想法的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以及在尊重文本完整性的同时能够在文本表面意义之外走多远有了深入了解。
曹晔:西方世界对汉学研究者的培养有自己的体系与传统,请问作为母语非中文的研究者而言,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您克服了哪些挑战?
韩德玲:毋庸置疑,西方人经常发现阅读晚明文本具有挑战性。明代士大夫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作品有多重层次,寓意丰富。我相信即使是中国学者也面临着挑战。一个挑战是了解不同时代和文化的人。为此,人们必须运用有时被称为“历史想象力”的东西——试图将自己摆在历史人物的位置上。有鉴于此,我发现陆世仪和祁彪佳的日记特别有帮助。另一个挑战是处理信息的巨大差距,无论是因为材料丢失还是因为许多行动者(包括穷人和目不识丁之人)没有留下记录。每一次,一个人必须根据现有的信息,弄清楚自己能够归纳多少。因此,我要说(正如其他西方学者所言),历史不是科学,而是一门艺术。
曹晔:我们知道,韩南教授、魏斐德教授与杜维明教授均是西方汉学界的泰斗人物。作为其门下弟子,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印象?
韩德玲:已故的韩南教授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都是敬业的学者,杜维明教授也是如此。我发现最令人振奋的是,他们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深深地致力于精神生活。他们不期望学生能像他们一样思考;相反,他们重视独立思考。韩南明白我为什么要换领域;后来,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他邀请我担任《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魏斐德研究晚明历史的方法与我不同。他最感兴趣的是政治制度的崩溃,尤其是明朝的瓦解。当我表达出对吕坤(我的第一本书的主题)的兴趣时,他质疑《实政录》是否被真正用作管理指南,或者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尽管如此,他还是鼓励我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曹晔:您的书是英语学界中利用广泛的史料为我们呈现明朝地方社会运作细节的研究成果之一。您的研究尤其注意为个体人物留有一席之地,从而能够较为客观而全面地呈现历史时空下民众的生活世界,展现不同阶层的互动与博弈。请问当初在研究和写作这个课题时,您是如何解决西方主流研究范式可能存在的偏见问题? 在写作过程中,您又是如何处理丰富的史料所传达出的音阶不同的声音与表述,来揭示和理解晚明慈善事业的?
韩德玲:我对中国慈善的研究并不是以一种思维范式开始的,而是以一个让我惊讶的问题开始的(因为它与西方普遍认为中国人只对其亲属行善的观点相矛盾):为什么慈善会在晚明变得引人注目? 我从这个问题扩展到了许多其他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将放生算作一个善举? 为什么他们要把“不费钱”的施与算作一个善举? 等等。每一个问题都迫使我更加深入地挖掘史料。
尊重事实和文本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工作就没有说服力。然而,在我看来,书写历史不能完全没有偏见,因为历史学家会权衡哪些事实更重要。不同历史学家看待过去的方式难免不同,就像梵高和莫奈画的向日葵也不同。事实的收集可能是累积的,但是关于它们的问题会随着每一代人和每一个历史学家而改变。因此,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发现J. H. Hexter关于“每一代人都会根据自己时代的紧急情况重新解释过去”的说法非常有启发性,也很有解放性。
历史学家必须选择如何为他们的读者包装事实。最简单的方法是按时间顺序排列事实。然而,我认为这只是第一步。我选择按主题组织材料,以期概括晚明的慈善事业。书写历史没有固定的公式,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什么可用的资料以及历史学家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曹晔:请谈谈您的著作吧。
韩德玲:我的第一本书是《晚明思想中的行动:吕坤及其他士大夫的新 方 向》(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The Reorientation of LüK'un and Other Scholar-Offi⁃cials)(1983)。这里的“新方向”指的是从抽象的哲学理论到实践学习的转变。当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很少有西方学者关注《实政录》这样的作品,甚至鲜有人注意到像吕坤这样的官员和他的父亲会为儿童创作童谣,或者为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写作说教作品。
《行善的艺术:晚明中国的慈善事业》是我最重要的著作,是我多年来研究和思考的结晶。我非常喜欢做这项研究。晚明的材料——最主要的是陆世仪和祁彪佳的日记——让我了解这些人物的思想和社交生活。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开始研究的时候,脑海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结果却发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信息,这些信息迫使我不断重新组织和改写我的解释。仅举两个例子。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政治上无足轻重之人在书面记录中历历可见,并在慈善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让我意识到慈善的理由不仅仅是精英阶层想要控制地方社会。我还惊讶地发现了佛教信仰和善书思想是如何渗透到精英社会——以至于我现在认为在精英思想和大众信仰之间作明确的二分是错误的。最后,如何组织(以及多次重组)信息以形成连贯叙述,这很费思量,也让我入迷。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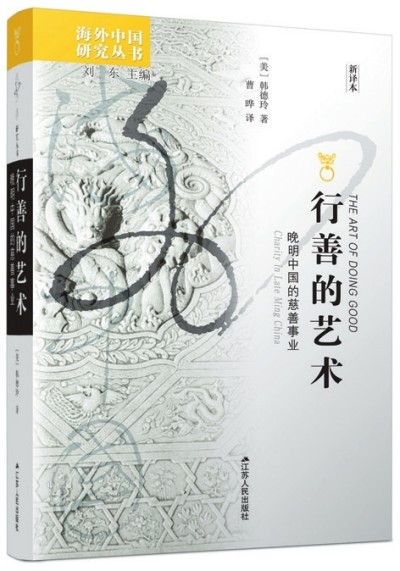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