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不是一。”
作为深谙经典童书之为“经典”的儿童文学大家,梅子涵老师十分崇尚“小文学”之“大道”,包括“哲学”之道。令我深感震撼的是,在这部颇为“热闹”的小说《打仗》中,竟也融入了很是深奥的哲学:“一不是一。”
懂吗? 似乎不太好懂啊!
别担心,故事是十分好读而且好玩的,依然是那个“自成一格”的梅子涵式的格调,娓娓道来,慢条斯理,有滋有味,有时直来直去,有时似乎又在绕来绕去。但请耐心等待,到后面一定会有某些时刻让你“拍案惊奇”。
这个关于“打仗”的故事,寄托了一代人的童年情怀,或者也可说是包含了一代代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们)的英雄情结。作者把几个少年去碉堡玩打仗游戏的迷恋讲得有声有色,尤其是不厌其烦地写他们纠缠不清的“争来争去”。这些言辞灼灼的“争来争去”,乍看吵吵闹闹、琐琐屑屑,甚至不无强词夺理,但跃动着孩子们对于战争历史以及好人坏人的探索和辨识,也彰显了孩子各自的个性气质。少年热血不就是这种样子吗?
这当中的头号角色是盛气凌人的陆幸,他口头禅中一个“屁”字让人看得胆战心惊——儿童文学可以这样反复出现“粗俗”的字眼吗? 别急,幽默的作者自有其化俗为雅的妙法,他让教语文的卫老师巧妙地“整治”了陆幸的顽疾。这一插叙的情节分外“妖娆”,语言文字在这位语文老师手中显然成了利器,见招拆招般的教导别出心裁、令人心悦诚服,大有“一笑泯恩仇”之风范。紧接其后的另一个小插曲同样令人拍案击节,那就是数学洪老师对于放飞螳螂的指示。他对抓了一只最大的螳螂的陆幸说,把螳螂送到外面去,“让它飞得高一点,不知去向。一是一,但是一不是一,你把它送到不知去向的地方去吧”!之后一只小螳螂来到教室窗户上时,同学们懵懵懂懂地感觉到了“一不是一”的含义。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即把老师们春风化雨的引领勾勒得十分传神,充满智慧,且有意趣。
“打仗”游戏是激烈的,作者对此的描写似乎“泼墨入水”,写了一次又一次,而实际上,其醉翁之意并不在打仗/争斗之“雄武”,而在于不打仗/不争之“温柔”——这个词作者“惜墨如金”地用了三次,但凡现身之处,都美好得令人屏息敛气。孩子们模仿敌我双方的较量,更多是一种逞能的游戏,根本不明白打仗意味着什么,带来的后果和伤痛是什么,直到他们偶然在碉堡附近发现了一座少年烈士的坟墓。当看清了这座坟墓,他们一下子变得不再吵闹,而是改为给烈士墓拔草,安静地拔草。陆幸很温柔地说:“我们轻一点,不要说话!”坚固的碉堡曾经刺激孩子们热血沸腾的争斗,而坟墓则让他们懂得了庄重肃穆,懂得了“温柔”地触摸碉堡上的弹痕。
格外令人“拍案惊奇”的时刻,要到故事的高潮:当孩子们听完那个曾经驱赶他们的老爷爷讲述了他和小烈士的父子关系之后,老爷爷就凭空消失了。虽然蹊跷,但是这次孩子们没有为此而争执,都信服了陆幸关于老爷爷放心而去的说法。作者无意去敲定老爷爷的去向,而就是让他像那只被放走后的大螳螂一样“不知去向”。这不得不说是神来之笔,以一种亦真亦幻的“聊斋”手法,带来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色彩,留给读者去揣想,毕竟——“一不是一”。作者亦无需赘述战争与和平的教义,因为孩子们在现实场景中已经默默地感受和领会,以满怀深情的歌声,以满心悲伤的泪水,去联结起过往峥嵘岁月的光荣与牺牲。孩子们最后一次去墓地拔完草,“我们的童年就在那一天干干净净地结束了”。这“干干净净”的一句话,产生了干干净净的力量,就跟“温柔”那个词一样,清澈又绵厚。
如夏丏尊所强调的,“文学的力量是从‘具象’来的,不具象就没有力量”。梅子涵的文学创作不以细腻的风景描写去营造抒情性的诗意,而是以具象地讲故事的本色,在平平实实、有张有弛的叙述中建立了内在的诗意。小说中的主要意象除了特别的碉堡和坟墓之外,还有一个朴素的日常意象——蚕豆,种在碉堡和墓地近旁的生机勃勃的蚕豆。读到“蚕豆”一处,不由联想起鲁迅的《社戏》,一群少年人看戏归来,去河边田里摘了罗汉豆在船上烧了吃,长大后的“迅哥儿”认为那是最好吃的罗汉豆。而对于《打仗》中的少年“我”而言,少年烈士生前爱吃的蚕豆,后来也成为他的最爱。小说的结尾句“我后来最喜欢吃蚕豆了”,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一不是一”吧?
当年长的梅子涵回首童年,他确切地看到了——“童年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不是一”。其实,又何止童年? 过了童年会怎样呢? 是不是就变成了呆板的“一就是一”,抑或出现了变异的“一不是一”,又或者,有了更多更多的“一不是一”? 反正,读完这部小说,这个哲学命题就会势不可挡地驻扎进心里,时不时地提醒我们去想想那“一”之外的许多“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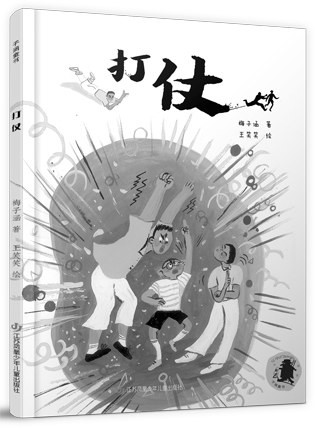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