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华书局出版了《项楚学术文集》,装帧典雅、印制精美。锁线装订,每页都能打开,且打开后不会自动闭合。用纸也甚好,用钢笔划不会泅,用铅笔写不会滑。更难得的是,文集整理的理念和做法深获我心。《编校后记》称“项先生提出尽量保持原书面貌而不作大的变动,一方面避免因重新编排而产生错漏,另一方面也方便读者或整体或有选择地购买阅读”。这是既为学术史考虑,又为读者着想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已刊学术论著,特别是论文编入集子时,最好不要一改再改;即使有了新资料、新想法,也要用适当的方式加以说明,而不是直接改动。这一方面保持了学术史的原貌,使商榷者不至无的放矢;同时,也方便了后学者对学术史的梳理。这方面处理得最好的,我想到的是裘锡圭先生。他在编集自己的《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时,特别说明:“编集时,基本上保持各篇文章的原貌。如有需要说明的问题或应该补充的资料,一般写在外加括号插入文内的‘编按’或附于文末的‘编校追记’中。”如果在编集时,随意修订,无疑会给后学梳理学术史增加很大麻烦——二十年前的文章,表
达的却是二十年后的新认识。
为读者着想,更是充分体量到了像我这样好买书却又异常吝啬的人的心情。当年上海古籍社出版项先生《敦煌文学丛考》时,我还是在校的学生,感觉此书定价颇贵,想耗一耗,等遇到折价时再购。不料,一晃,就很难再遇(毕竟仅印了1800册)。有了孔夫子的平台,寻书方便了,但想捡漏却更加不易。2003年商务出版其《柱马书屋存稿》,当年即幸运偶遇五五折而购得。此次出版文集,完全可以将已收入《柱马屋存稿》的文章,与尚未结集出版过的《柱马屋存稿二编》合为一册印行(两本书相合,分量大约与《敦煌文学丛考》相当吧)。但仍各自成册,这就使像我这样已购得《柱马屋存稿》的读者,只需补配《二编》即可;同时,另购《敦煌文学丛考》更能稍慰当年未能购得上古本的遗憾。这样为读者打算的作法,在近年的出版界,可称绝响。这很有当年影印《永乐大典》的遗风——1960年中华书局曾线装影印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大典》残本七百三十卷;1984年出版精装十册本,其中新增六十七卷。为了方便此前购置过线装本的读者可以配齐,特又将此新增部分“仍印制红黑套印线装本”(《重印说
明》),共两函二十册,与精装十册本并行。现在重印书,大概不会想到此前读者曾经买过其中一部分这回事了吧。甚至同一部书中的不同册,因前后出版拖了若干年,每一册的印数都不相同。甚至有出到半截,便整套定价推出;以前购得者,便成鸡肋。当然,如果在这套文集所收的每本书的后面,能针对这本书此前的出版情况作一说明,就更加完美,特别是对一些一版再版的书。另外,项先生研究的重点是语词考释。如果能编一涵盖全书的语词索引,应该是很有用的吧。
整理当代学术论著,也应秉持整旧如旧的原则。《顾随全集·出版说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19)称:
当时的语言文字习惯与今天的文字规范用法有较大差异,如当时用“皮气”,今天用“脾气”;当时用“卤莽”,今天用“鲁莽”;当时用“担搁”,今天用“耽搁”;当时用“计画”,今天用“计划”;当时用“了草”,今天用“潦草”;当时用“孤负”,今天用“辜负”,等等。现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对这些文字逐一进行了规范处理。
这个整理原则是大可商榷的。举的这些例子,都说明这些词汇是先有
语言、后有相应的文字来表示对应的意思。这样的规范和统一,一是抹煞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同时又让几十年前的人用现在所谓规范的用字,予人以时空倒错之感。倘若本着这样的原则来整理诸如《朱子语类》,我们大概就不知道朱熹是生活在哪个时代了。好在研究语言的学者,不会使用这个整理本作为依据。
对整理文史著作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用现在通行的古籍点校整理本,来核校此前论著的引文。时下甚至整理清人的论著,也要用现在通行的本子如点校本廿四史来核校引文。这是过度整理,既不必要、也不应该。比如,清人所使用的,可能是监本或汲古阁本;同时,他们往往引用大意,甚至为通顺起见,用自己的话加以概述或勾连,我们如何能用点校本去核校呢?点校整理本,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方便得用的本子,并不是说,只能使用它。我们应当把点校整理视作该书的一种研究成果,如句读、如施划专名线等。如果作者在征引时,能保证自己对所引用者理解无误、且无足以动摇其结论的重要异文,那也完全可以不使用点校本;或者对相关文句用点校本加以查核,而不必
非引用点校本。《项楚学术文集·编校后记》于此特别加以说明:“在校核引用文献的过程中,如无特别需要,我们尽量采用项先生当年所用的版本。”并举了《法苑珠林》《景德传灯录》,称前者乃据四部丛刊影印明径山寺百二十卷本,后者仍用日本影印福州东禅寺崇宁藏本,而没有使用通行的点校本或大正藏本。当然,也有一些变通,比如《云溪友议》,项先生既引用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的排印本,又有引用了《稗海》本。如果不作统一,就需要在相应的每篇文章中标明各自所依据的版本。这就很麻烦。为避免这个麻烦吧,此次文集统一成了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这个变通是可取的。
我想,整理古人论著中的引据,如果与通行本有实质差异,应出注说明,不应据现在通行的整理点校本作改动;整理现代学者论著,也要尽可能以作者所使用者为依据,进行核校,避免用现在通行点校整理本,来替换、统一、规范此前的引文。这一点,实在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要“整旧如旧”,不要过度整理。即使引文有错,那也是作者的错,也是常有的事。把作者
的错误修删殆尽,也是对历史的一种篡改,特别是作者已故时。
得益于项先生为读者着想的善意,成全了我所收集的项先生论著的百衲本样貌。《敦煌文学丛考》《柱马屋存稿二编》,乃中华此次所出文集本;《柱马书屋存稿》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王梵志诗校注》乃上海古籍1991年版(托朋友于2002年五月费55元购于敦煌),《寒山诗注》是中华2000年版(次年十月以半价购于太庙书市),《敦煌歌辞总编匡补》系巴蜀书社2000年版(次年杪以半价得于北大书摊)。《敦煌变文选注》最有趣,1995年9月即于琉璃厂12元(卖家仅减0.15元)购得巴蜀书社1989年版;后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增订本,分上下两册,正在纠结时,2011年末偶于北师大对过盛世情书店遇下册,花四十元购下,颇有讨一大便宜之快(因版权页在上册,迄今我仍不知此书印刷于哪年。“下篇”扉页编一该册目录,极便查阅),这也是受惠于项先生将一册增订为两册时,分割之明晰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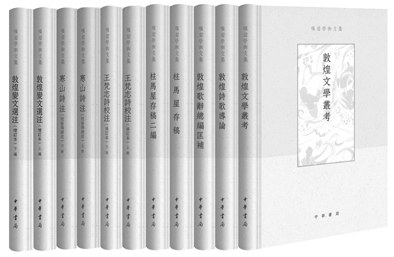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