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但丁逝世七百周年。
但丁的《神曲》在中国传播亦已有一百多年。百余年来,众多译家为国人奉献了风格多样的多个译本。其中,黄文捷译本系从意大利语直译,采用诗体,兼顾忠实性和艺术性,备受好评。日前,该译本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新版,并被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组织的专家委员会选中,作为意大利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阿尔贝剧院/拉文纳剧院和但丁协会合作制作的有声书中文朗诵底本。
《神曲》无疑是经典,甚至可称经典中的经典。但也有人说:“所谓经典,就是大家都认为应该读而没有读的东西。”离开但丁的时代七百年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神曲》?我们可以怎样读《神曲》?另外,《神曲》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接受史?《神曲》各个译本各有何特色?……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神曲》黄文捷译本新版序言作者、意大利语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文铮先生。
——编者
中华读书报:《神曲》最早进入中国是在什么时候?您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任何一个文化或者社会变革的节点上,我们都能看到但丁的名字和《神曲》这部巨著。”请您具体谈谈《神曲》对中国的影响?
文铮:《神曲》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比我们现在一般人知道的,甚至比很多学者知道的更加深远。但丁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为了启发中国的民智,在日本做了很多编译工作。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但丁,他认为但丁在中世纪意大利起到的的作用,对中国特别有参照和借鉴的意义。中国也需要这样一个大文豪和知识分子,从民族语言和文学入手,启发民智,对民众产生强烈的凝聚力。其实,但丁形象也是梁启超本人效法的榜样,他也想成为但丁那样的文人,所以他把但丁的形象写进了他的一个叫《新罗马传奇》的戏曲剧本里,这个剧本曾在广东的一家报纸上连载,但最后没有写完。这部戏剧以但丁为串场的角色,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穿越的形象,梁启超借但丁之口,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心声。梁启超对但丁的崇敬不只是因为但丁本身,更因为但丁所属的意大利民族——刚刚完成民族复兴伟业的意大利使梁启超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明确提到以但丁和《神曲》作为参照。后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认为刚刚完成民族国家统一的意大利的处境:在强邻的觊觎之下,四分五裂,老百姓没有统一的语言,更没有属于他们的文学,当然也就没有凝聚力,但是自从出了但丁以后,这一切就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胡适觉得中国也可以效法意大利,把那些封建的陈腐的文化和文学打倒,创立我们白话文和新文学,有了新的语言就有了新的社会。
中华读书报:请您谈谈《神曲》的翻译史。
文铮:虽然但丁的名字很早就进入梁启超、鲁迅、胡适这些中国思想家、文学家的视野,但是《神曲》的翻译却比较晚一些。100年前,为纪念但丁逝世600周年,上海发起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其中《小说月报》计划做一期纪念但丁的专辑。这期间,编辑意识到,中国至今还没有《神曲》的中译本,于是开始物色译者,找来找去,这个事情就落到北大教授钱稻孙身上。少年钱稻孙随父母在意大利生活了一段时间,曾在罗马大学读书。他从意大利文直接翻译了《地狱篇》的前三歌,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中译名为《神曲一脔》。钱稻孙的中国文学底蕴很好,他把《神曲》译成了屈原的离骚体——因为《神曲》的句子很长,每一句都是11个音节,用中国传统诗歌的五言或七言翻译不了这么长的句子,而只有骚体比较自由一些。钱稻孙还在音韵格律上下了一番功夫,尤其是第一歌和第三歌,韵脚非常好。
在诗歌语言上能与钱稻孙媲美的译本还有新月派诗人于赓虞和燕京大学才子吴兴华,他们都节译过“地狱篇”,但鲜为人知。
我们说,中国人第一次读到《神曲》中译本是在一百年前的《小说月报》上。然而《神曲》全译本却很晚才问世。1930年代初,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译本。第一个译本的译者王维克是数学家,是居里夫人的学生,也是发现华罗庚数学天才的伯乐。他热爱文学,尤其痴迷但丁。他依据法文本,同时参照英文版进行翻译。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个全译本直到1948年才在上海出版。这是《神曲》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因为《神曲》诗歌形式的难度,王维克决定翻译成了散文体。出版时他还请柳亚子写了题记。《神曲》另一个译本是上海诗人朱维基从英文本翻译过来的,译成了无韵的自由诗体,这个译本晚于王维克译本几个月也在上海出版。
此后,这两个译本就成为中国读者主要的阅读文本了。由于有了恩格斯那句话(“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拥抱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神曲》没有受到批判,而且西方文学教材中也有但丁,只不过是把他定位为批判教会黑暗的革命文学家。
文革后,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注意到中国没有从原文翻译过来的《神曲》译本,于是找到了当时北大的田德望教授。田德望教授曾在佛罗伦萨大学留过学,是中国高校里首位开设《神曲》课程的人。1983年,已经退休的田德望开始从意大利原文翻译《神曲》。田译本的特点是:第一,散文体;第二,严格忠实于原文;第三,将历来优秀的注释全部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占了2/3的篇幅——这是他的伟大之处。1999年,意大利总统访华,那时田德望已经卧病在床,意大利总统专门到他的下处授予他大十字勋章。2000年,田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1年,北大另一位教授黄文捷,也在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神曲》译本。黄译本的特点是,译为诗体,严格地按照行数一一对应,而且还部分地保持了诗的韵脚,因为原文是aba,bcb,cdc,ded……就这样连环像锁链一样,而且每一行都是11个音节,重音都落在每行的倒数第二个音节。
作为意大利文学研究者,我特别推荐黄文捷这个译本原因在于:第一,研究时能一行一行地跟原文对照,这点特别重要;第二,这个版本可读性强——其实《神曲》最初就是用来当众朗读,当成故事讲的。如果从艺术角度和学术角度的平衡来看,我个人觉得黄译本比田译本做得更好一点。
中华读书报:综合来看,您如何评价众多的《神曲》译本?
文铮:钱稻孙的译本很古雅,很多人都很推崇钱译本,但他的楚辞体和但丁面向老百姓讲故事的初衷可能有些差距,更何况后人很难拥有钱稻孙那样的才华,即便他本人也不能够在三首歌中完全把音韵译出来,所以钱译本只能作为一个完美的标本。王维克和朱维基的译本作为最早的全译本也都可圈可点。尤其是王维克译本,第一个译成散文体,相对也很忠实,只不过没有田德望译本那么精确和学术性强。朱维基的译本开创了诗体翻译的先河,但从音韵、语言表达以及对原文的忠实程度来讲,都有不足,如果跟黄文捷译本相比,是逊色的。黄文捷译本从忠实性和艺术性两端,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后人是超越前人的。
其实在这之后,2004~2005年又相继出版了张曙光和黄国彬两个译本,两个译本共同之处是都译成了现代自由体诗,但张曙光是从英文译过来的,而黄国彬参考了意大利文,两位译者都是诗人,所以译本的诗味都比较足,艺术性都很高,学术性方面相对弱一些。
中华读书报:《神曲》在当代意大利以及欧美的接受情况是怎样的?据说《神曲》的英译本有上百种之多,为什么英语世界要不断进行重译?
文铮:其实,经典是需要很多译本的。《神曲》的英文译本或者其他语言的译本,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而且每个世纪都会有各自推崇的优秀译本。译本的语言风格和理解随时代变化,所以译本越多,风格越多,越有助于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接受。
但丁死后的几十年,对他的研究和推崇就一直在走上坡路。他死后名声如此大是由于《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但丁逝世那年薄伽丘才8岁,到二十几岁时,他疯狂地喜欢上了《神曲》,他到佛罗伦萨走访但丁的家人和生前友好,写了第一本《但丁传》。薄伽丘还第一个开设关于《神曲》的讲座。但丁在逝世后的三五十年里,名声如日中天,成为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一个耀眼的明星。艾略特曾经说过,从但丁到莎士比亚,没有第三个人,从文学角度来讲没有第三个人。
西方大学里古典学或诗学传统的课程,都会开设关于但丁的课程,会对《神曲》进行文本细读。《神曲》是中世纪集大成的作品,在神学和哲学方面有很多开创。但丁根据当时托马斯·阿奎纳或者奥古斯丁的神学或哲学的体系,将基督教世界进行分层分级,尤其是还发明了炼狱这个概念,从此深入人心,广为人知。我们以前有的教材说但丁反宗教,其实不然,相反,他对宗教尤其对基督教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华读书报:当前中国的但丁研究情况如何?
文铮:这一百年来,我们对但丁的了解和研究还是很表面,但是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趋势,一些有海外留学背景,尤其是古典学、古代和中世纪文学、古典哲学专业的青年学者,他们在不同的学科背景下系统地研习了但丁的著作,对但丁的理解和研究非常深入,已经开始跟国际接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中华读书报:但丁被称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也被认为是“新时代的开启者”,意思是说《神曲》对中世纪文化作了集大成式的呈现,也是文艺复兴的重要作品。您觉得《神曲》总结中世纪文化的成分更大,还是迈向现代的新观念、新理想的成分更大?
文铮:恩格斯这句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意大利文译本序言。我个人觉得,但丁还是中世纪的诗人,很多人说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其实他死的时候文艺复兴还没有真正开始,只不过他对文艺复兴具有启蒙的作用而已。第一,他脱离不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当时的神学,尤其是宗教,而且他本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抨击教会,是因为他觉得教会影响了天主教的发展,从他的学识、才华等多角度来看,他都是中世纪文化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
有人说《神曲》就是把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形象化或者诗歌化了,他的思想根本没有跳出托马斯·阿奎纳经院哲学的体系,没有脱离奥古斯丁的神学和哲学的体系,但是,为什么他有这种新时代的思想,其实恰恰是他的基督教理想促成了这一点。他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神曲》的精神世界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上升到一个神学—哲学的高度,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像宇宙一样有秩序的世界帝国。从客观角度来看,其实这个理想也是世界走向新时代的开始。
中华读书报:《神曲》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让我想到《红楼梦》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同时也包含很多新的观念(如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对女性的尊重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是否《神曲》之于西方和《红楼梦》之于中国有一定可比性?
文铮:如果从对后世的影响、在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以及划时代的意义来讲,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它们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红楼梦》是中国社会百态的反映,是世俗性的,虽然也表现为神圣与世俗的冲突,但归根结底,还是面向现实社会生活的;而《神曲》则是精神性的,是神学的,尽管观照了人间的种种,但最终还是指向天堂,指向信仰,呈现上升的趋势,是人与神的统一。而《红楼梦》就没有这些,它告诉人们“好就是了、了就是好”,无可奈何。
中华读书报:《神曲》是七百多年的作品,阅读难度又很大,那么,中国读者今天还要读它吗?我们可以怎样阅读它?
文铮:但丁那个时代还没有印刷术,《神曲》是通过朗诵而传播给绝大多数受众的,因为当时的手抄本一般人看不起,所以但丁在写作过程中特别重视朗读性与故事性。一个好的《神曲》译本,你会从中感受到它叙事的想象力,可能不亚于我们的《西游记》。中国的读者觉得阅读困难,并不是语言问题,而是《神曲》的典故太多,这些典故涉及宗教、古希腊罗马神话、历史人物等等,需要看注释才能明白。
如果你想具备基本的人文素养,最好是读读《神曲》,因为整个世界的文学受《神曲》的影响太深了,歌德、艾略特、庞德……不胜枚举。中国现代以来鲁迅、胡适、茅盾、老舍、巴金等等,都受到但丁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重要,歌德重要,可是某种意义上,但丁比他们更重要,所以《神曲》还是应该读。只不过作为普通读者,我们没必要研究得那么深入。如果只把它当故事来读,也会很有收获的。如果你希望体会它的美,你可以把它当作诗歌去读。如果是一个优秀的译本,应该能同时满足读者的这两项需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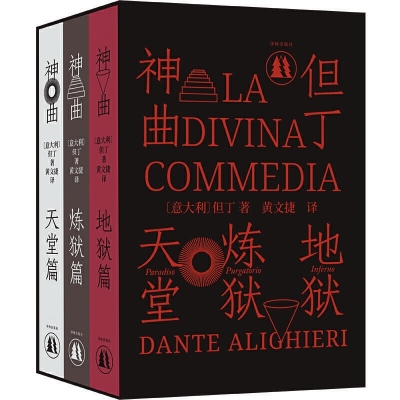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