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之一,而《〈自然〉百年科学经典》是一套10卷本的文章选集,包括从1869年到2007年的八百多篇文章。
我很喜欢这套书,已经写过7篇书评,每次都试图为一卷提取一个主题:在第一卷的书评,我强调了编选的宗旨和阅读的目的;在第二卷的书评里,我讲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对各个科学领域的影响;在第三卷的书评里,我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等等。但是,这套书毕竟是文章选集,入选的文章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的方法、内容和结论都迥然不同,唯一的共性就是它们在历史上都很重要,现在仍然有些影响。强行为每一卷提取一个主题,只是反映了我本人作为一名读者的偏好。这篇书评讲讲《〈自然〉百年科学经典》作为文选的一些特色,也许可以让其他读者对这套丛书的了解更多一些。
第八卷选录了从1993年到1997年的61篇文章,其中物理学2篇,化学9篇,生物学18篇,天文学14篇,地球科学18篇。
物理的文章很少,但是都很有趣。《无序介质中光的局域化》用光学方法研究无序材料中一种不同寻常的传输特性(安德森局域化);《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利用光子的纠缠态,把量子系统的状态传递到其他地方并重建,这是量子信息领域里的一项重大突破,曾经入选《自然》杂志的“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这篇文章的第二作者潘建伟当时是通讯作者蔡林格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后来为我国的量子通讯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墨子号”量子通讯卫星),最近他的团队还用光学方法验证了量子计算的优越性,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
物理的文章很少,但不意味着物理研究不重要,更可能是因为分类的方法有些随意。比如说,临界温度超过130K的汞钡钙铜氧超导体为什么就被归入化学了呢?《类太阳恒星的一个类木伴星》是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工作,却被归到天文学里——我不是说这个分类不对,而是说,人们的看法总是随时间转移的:20年前还有很多人认为天文学不属于物理,可是在过去的5年里,诺贝尔物理学奖已经4次颁发给天文学领域的发现了。地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一直是《自然》关注的热点,而相关研究工作采取的很多研究手段都是不折不扣的物理方法(比如说,测量冰芯的电阻率)。
新的探测方法可以提高我们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认识。《雷达干涉测量技术得到的兰德斯地震位移场》就是利用了卫星搭载的“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法”,进一步揭示了地壳里应力的积累和释放;微引力透镜效应帮助我们发现了银晕里存在暗天体的证据。
计算机性能的提高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地球内部670km深处的矿物吸收相变对地幔对流模式的影响》《地磁场倒转的三维自洽计算机模拟》《人类对大气温度结构影响的研究》是三种截然不同的突破性科学成果,它们的共性就是研究对象和地球有关,研究手段都依赖于大型计算机。大规模的数据采样和数据分析,更是离不开计算机,《地球内核差异性旋转的地震学证据》《深部地幔流动的全球层析成像证据》都是很好的例子。
还有一些挺好玩但也挺难归类的文章。比如说,《柯伊伯带天体候选体1992QB1的发现》开启了“冥王星覆灭”的旅程,人们逐渐认识到,冥王星只是很多的柯伊伯带天体中的一个而已,最终在2006年被“太阳系九大行星”除名(现在被称为“矮行星”,但是我个人还是把它当行星看——就算是为了回忆我的从前吧)。《音乐和空间任务表现》证实了“音乐可以提高智力”的说法基本上是瞎扯淡,然而,正如写在十多年以后的“编者按”里所说的,“尽管如此,儿童的‘大脑音乐’已经成为一个小的营销行业”。《DNA指纹分析争议的平息》说明科学研究往往不仅是科学的正确与否,还有社会接受与否的问题,“没有科学理由怀疑法医DNA分型结果的准确性,现在主要的障碍是说服公众相信DNA指纹争议已经解决了”,但引起我关注的却是很次要的一点:因为版权的缘故,这篇文章里有一幅照片不能用在选集里(该处是空白),充分说明了这套书的编选者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当然,作为5年里具有代表性的科学成果,第八卷里还是有一些文章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彼此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正如其他各卷一样)。《从体外培养的细胞系中通过核移植获得克隆羊的方法》(1996年)和《胎儿和成年哺乳动物的细胞可以产生存活后代》(1997年)反映了生物学里克隆技术的迅猛发展,著名的“多莉羊”就是证明。
克隆羊的工作来自于同一个研究小组,而其他很多工作从一个不同的侧面说明,科学研究中“赛跑”的现象愈演愈烈:不同的小组研究同一个问题,荣誉通常只给第一名——第二名就是最大的输家。《紫杉醇的全合成》我是一点不懂,但是“编者按”里说的“这项研究与……《美国化学会志》上发表的另一条合成路线的文章或多或少有些巧合”,却让我浮想联翩;在《类太阳恒星的一个类木伴星》这篇文章后面的《修订中的说明》里,作者马约尔和奎洛兹(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马西等人“及时与我们交流结果表示深深的谢意”,而这位马西一直都被认为是诺奖的有力竞争者,最后只是因为(至少是很多人猜测的)“MeToo”运动(反对性骚扰)而落马。
上面这些例子还是比较弱的间接证据,第八卷里还有很多很强的证据说明科研竞争的激烈性:有很多文章是“背靠背”(backtoback)发表在同一期上。关于单层碳纳米管的工作,有《直径1nm的单层碳纳米管》和《具有单原子层管壁的碳纳米管的钴催化生长》;关于DNA自我复制的研究,有《回文双链DNA的化学自我复制》和《回补配对的寡聚核苷酸的自我复制》;关于自组织材料生长的研究,有《一种基于DNA将纳米颗粒合理组装成宏观材料的方法》《利用DNA来实现“纳米晶体分子”的组装》。在天文学观测中,有《大麦哲伦云的一颗恒星可能存在微引力透镜效应》和《利用微引力透镜效应发现银晕中存在暗天体的证据》;在环境改造的试验里,有《在赤道太平洋海域生态系统中队铁假说的验证》和《赤道太平洋海域对浮游植物光合作用的限制》。这些还不包括发表时间间隔很短的不同文章,比如地球科学里关于冰芯研究的几篇文章,天文学里关于伽马射线暴的两篇工作。
顺便说一下,我注意到,在这一卷里,中国人的名字显著增多了。刘丽杏、何大一、林潮、宋晓东、金煜,还有很多只能从拼写方式里看出(因为中译本最多只给出前两位作者的中译名,而全体作者的名字出现在文章的最后)。而李天虎、张一影和魏西平虽然是第一作者,但是他们的名字后面都有个括号标明了是音译,也就是说,他们的中文名字被“埋没”了。即使发了Nature亦如此。看来,科学界的竞争太激烈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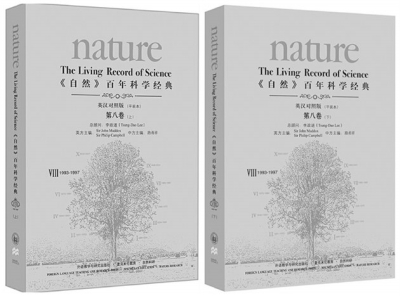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