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就其数量(民族众多)而言,还是就其历史的复杂性(几大支系盘根错节)而言,西南民族史都是中国民族史研究最称棘手的问题。大学本科时,师从杨耀坤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毕业论文原想研究川东民族,后来放弃了,因为连续数月的材料阅读,不但没有使我对廪君蛮、板楯蛮等川东民族的渊源了然于胸,反而更见晕头转向。研究生毕业后,去云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云南本是民族大省,历史研究无法回避民族问题,不得已重新拾起西南民族历史的相关研究论著细读,自以为这次可以豁然开朗了,结果仍是一团乱麻。已有的研究论著没有让我对西南民族关系有一清晰的历史认识,是因为这些论著本身也多不甚了了,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而已。由此深知,厘清西南民族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虽然耗费了很多学者的心力,而其收效却未必令人满意。近日读到刘复生先生的《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自以为可以释然了,纷繁复杂的西南古代民族关系终于有了一个考证精详、持论公允、线索清晰的研究成果。
“西南古代民族”生发于司马迁的《西南夷列传》,包容了自甘南而至广西区域内的众多民族,语属上卷入了汉藏语系的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藏缅语族,系属上涉猎了传统中的濮僚、百越、氐羌三大系统。将这些不同语属、系属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段的消长进退、你我互嵌辨析厘清,是此前类似著述没有完成——至少是没有令人信服地完成——的任务。刘复生先生的这本《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我以为,是目前所见完成最佳的著述。
该书以“西南古国的民族关系”开篇,梳理了先秦时期蜀国、巴国以及秦汉时期夜郎、滇国、邛都的材料,并参考、吸收了前人值得信赖的研究成果,认为古蜀五国的统治者来自不同的地方,应属不同族系,不能笼而统之地言说;“巴”则是一个区域的泛称,包括了许多势力大小不等的族群(如板楯蛮、廪君蛮等),统一的“巴国”并不存在;夜郎、滇国、邛都是司马迁《西南夷列传》称其有“君长”的几大族群,继秦灭巴蜀后,汉武帝时被纳入了中原文化系统。总体上,它们应都属于泛称的“濮僚系统”,但却“不能与现代民族的分类完全对应起来”,因其“与百越在文化上(已经)有了许多交叉”(第47页)。
旧时西南民族史研究,习惯用氐羌南迁解释藏、羌、彝、白、纳西等17个藏缅语族民族的许多问题,但刘复生先生注意到藏缅语族之下,他们还有藏语支、羌语支、彝语支、景颇语支等不同语支的分别,笼而统之的研究将被许多似是而非的情形蒙蔽。故在“藏缅语民族的南迁与演变”一章,作者认同氐、羌当为两个民族后,不认同将藏缅语族民族全部归入“氐羌系统”的看法,“证据显示彝族或纳西族并不是羌人或氐人之后”——“藏缅语族不止氐羌两族”(第53页)。虽然后世建构“羌族史”过度使用了“西羌”的材料——因其“并不都是后世所说的羌族”,但羌族南迁则是事实,而且打破了“蜀汉徼外蛮夷”的平静态势,导致了原住夷系民族的大规模“内属”与南迁。这是西南民族史上民族的大规模易位,于“蜀汉徼外”形成了新的民族分布格局,乃至今天的西南民族分布格局仍然带有它的影响。
《后汉书·南蛮传》将廪君、盘瓠和板楯三部归为“南蛮”,民族关系极为复杂,《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运用两章的篇幅分别加以讨论。廪君蛮以白虎为图腾,不同于“射白虎”的板楯蛮,主要居住于巴郡、南郡,后与中原南下的卢戎并江西西上的彭氏融合,形成了今天多元成分构成的土家族。盘瓠蛮被认为是苗瑶民族的先民,与西羌无涉,原活动于荆楚等地。尊蚩尤、盘瓠为远祖,后来分化出苗瑶语族的苗、瑶、畲三族,又在“与中原政权和其他族群交往冲突中,部分向南、西南、东南流徙,造就了后世苗瑶之民遍及西南和华南以及东南亚的状况”(第298页)。板楯蛮世居嘉陵江流域,以其所缴赋税称“賨”又称“賨人”,天性劲勇,俗喜歌舞,曾助汉高祖伐秦有功。成汉政权灭亡后,板楯蛮(时号“巴氐”)主体融入了汉民之中,少数则被纳入了泛“僚”。成汉时期,大批僚人或自南入、或从山出,形成大规模的西南民族异动。“入蜀僚人是分散的,不同族群的习俗或信仰并不完全相同”,作者通过崇拜“竹王”、凿齿穿耳、使用铜鼓、葬行悬棺等巴蜀原住居民不曾有过的文化习俗认定,他们大部应该主要是从古牂牁来,其语言“具有壮侗语族的特征”(第120页)。晋唐之间,“中原政权的开拓和扩张,昆明族人的西向北向拓展,壮侗苗瑶民族的东向流动,终致西南‘濮僚系统’民族社会支离分散而至衰微”(第298页)。
以语族为线索的辨析梳理之后,作者又分别考察了南诏、长和、天兴、义宁、大理、罗殿国、罗氏鬼国、自杞国、特磨、毗那、白衣、罗孔以及黎州诸蛮与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的交涉与互动,认为“宋挥玉斧”是一个历史建构而非事实、“云南八国”为“云南”与“(西山)八国”的合称而非大理的八个行政区划、“广马”贸易的文化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以及对自杞国历史的考订、罗殿国与罗氏鬼国的辨析、特磨诸道的梳理、黎州诸蛮的分说,常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最后,《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用两章的篇幅,专门考察了中央王朝治理西南民族的制度变迁。从秦汉的道制、左郡、属国到唐代的羁縻州府,再从宋代的“虚像”羁縻到元明的土司制度,个中经历了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制度演变,不能混为一谈。它们是西南民族治理的历史过程,也是西南民族治理的宝贵经验。到清代中期废止土司制度,西南民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全书读罢,除了为其严密的逻辑论证与频出的独特见解称绝,最关键的是关于西南古代民族消长进退的过程有了非常清晰的轮廓。这是此前的很多著述没有完成的任务,虽然有些著述的篇幅很长。
历史性地辨析厘清出了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外,《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在方法学上也有很多值得表彰的地方。首先是有清晰的学科视野,作为人类学分支的历史人类学与作为历史学分支的民族史学,“前者重主观认同,后者重客观实证,这是两种治学路径和方法,或者说是两种认识体系或解释体系”,方法学上“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第3页)。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显然应是民族史学的课题,应该以客观实证为学术立场,吸纳其它学科的新知卓见,力求避免主观想象。正是把握好了此一学术立场,该书在考察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时没有陷入此前某些著述的含混交缠。再者是将西南民族演变与中央王朝治理分开讨论,前者重点在于源流、交涉,可以单向切入;后者重点在于政策、制度,必须宏观考虑,虽然两者都是西南古代民族关系演变的因由,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若非如此,和此前已有的很多著述一样,该书即很有可能陷入两者都无法说清的尴尬。其三是分时分地动态讨论西南古代民族关系,避免静止地、不变地观照它们。正如刘复生先生自己所说:“由于多语族民族的交汇和相互渗透,族群流动,西南民族关系史的场景是丰富多彩的,历史舞台的变幻往往应接不暇,瞬息即纵,无论是诸族群和民族之间还是它们与中原政权之间,民族关系都是动态而非静止的”(第301页),“从空间上追溯民族迁徙流动之迹,从时间上洞察前后同一族称掩蔽下的不同族群,或者是同一族群因时代不同和书写习惯相异而产生的不同称谓,进而观其民族融合之势,从不同的视角对‘史料’细加辨析,正是民族史研究者面临的任务”(第3页)。具体的实例可以举出僚人消长的论述,以及“巴人”二蛮(廪君蛮、板楯蛮)的各有分属,但最精彩的还是关于“僰国”的讨论。历史上并不存在“僰国”或“僰侯国”,以此代指僰人聚居之地而已。秦汉时有“僰道”之僰、“滇僰”之僰、“篇笮”之僰,后人将此不同时地的“僰”连接起来,形成一种西南迁徙的想象,并进而引为云南白族的来源,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汉时筑僰道城,“斥徙”僰人,仅仅是将它们分散到附近山区而已。宋明时期,“僰国”地区民族称谓“泸夷”,包含了当地的僰人、晋代入蜀留住的僚人以及唐宋扩展而来的乌蛮。就中,属于僚人入蜀留住的都掌蛮崛起,雄霸此一地区数百年。在当地僰人被都掌蛮与乌蛮夹击破灭后,都掌蛮袭称僰人,最后是在明军的镇压下被迫同化了。葬行悬棺本是都掌蛮的习俗,后人不察,遂致张冠李戴给了僰人——误称成了“僰人悬棺”。在此辨析与梳理中,如果不分时分地动态地加以考察,就会盲从前人、以讹传讹。
总之,无论是就其内容还是就其研究方法,《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都是一部堪称优秀的典范之作。以其所辨析厘清出来的西南古代民族关系为基础,参借刘复生先生在该书中展示出来的研究方法,相信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将会展开一个全新的天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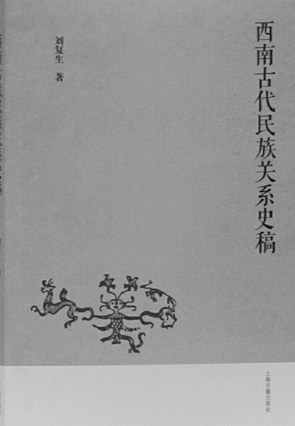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