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欧洲地区早在19世纪末期即已问世中国文学史,美国自20世纪以来,也相继出现了多部中国文学史。相比之下,21世纪初分别出版于美国和英国的两部各超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和《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可谓诸多欧美版中国文学史中的代表作。
今天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学史,首先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恐怕一般读者对此会不以为然,觉得这并非问题。但仔细推敲一下,你会发觉,这确实是个很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从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看,有些虽然其书名皆称为“中国文学史”,实际涉及的内涵却并不包含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中国人和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书中所述及的多是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汉族人群的文学及其发展,以及汉族人用汉语书写和创作的文学史,很少或几乎不包括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书写和创作的其他55个民族的文学,很少或几乎不涉及港澳台地区文学,更遑论海外华人或华侨的文学创作了。对此,两部欧美版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美]梅维恒主编),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实际概念上的中国文学史所蕴含的中国范围内,文学史本身范畴的定义问题。两书的作者在编写中体现出这样的内容安排:中国文学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应该包含中国所有的民族——既包括汉族群体,也包括少数民族群体,还应顾及港澳台地区和中国边界之外(境外)的华人离散群体。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做法。从理论上说,所谓中国文学史,必须也应该涵盖今天地理、文化、民族概念上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学,不能也不应该偏废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否则它就称不上真正的中国文学史,而只能称为汉民族文学史。
文学史如何做到古今贯通?这个所谓“贯通”,不是刻意牵强地硬将古代和现代挂起钩来,而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在描述或评论近、现代文学时,将其与古代相联系,找出其中内在的必然联系,说明其间存在的尚不为今天人们所知晓的规律与特征。这方面,《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作出了努力,该书的编排方式,兼取了年代与主题,全书不严格按朝代为序,也不完全弃朝代于不顾,而是以超越时间与文类的全新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将传统习惯划分的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阶段完全打通,使之融会贯通,从而使全书汇成一编,浑然一体,将从古到今的文学发展历史,在一个整体的文学史卷册中得到完整的体现,这样做,既便于对中国文学生生不息、沿袭不断的特征作充分的展示,也便于现时(现代)与过去(传统)文学之间的相互回应、相互联系、前后对照。
对于文学史整体框架的总体设计与编排,《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在接受剑桥大学出版社编撰任务时,即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这部文学史,不光适合西方一般读者作为文学史专书(不是学术著作)的阅读需要,更要在西方学界原有既成中国文学史体式上有所突破,从而写出一部既有创新性、又具说服力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史,力求避免机械地以文类分割的做法,把一部文学史完全写成文体分类史,以致割裂各类文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不出作家本身能够从事多种文体创作的综合能力及其风格特点。为了突破这个框架约束,两位主编设想出了以整体性文化融入文学史的做法,努力把这部文学史写成文学文化史(historyofliterarycul⁃ture):一方面,拟建构起文化史的大框架,在文化史的范畴内容纳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辅之以文学文化的叙述方法,并尽可能不排斥文类出现和演变的历史语境,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更为关注历史的语境与写作的方式,使得这部文学史完全不按往常出版的文学史模式出现,由此,《剑桥中国文学史》成为了一部不同于一般文类文学史模式的具有文学文化特色的文学史著作。
对于历来令文学史研究者都甚头痛的文学史分期问题,两部欧美文学史的主编都认识到,关键在于能否摆脱历史朝代的传统束缚,建立起与历史朝代既有联系又不受拘束的框架结构。他们觉得,作为一部史著,自然不能完全脱离历史发展演变的轨道,但毕竟文学史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是一部围绕文学展开的历史书,不是单纯的历史著作,如果完全围绕历史朝代转,看不出文学本身的发展轨迹和线索,那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了。为此,两书主编力图改变完全按历史朝代顺序划分文学史阶段的做法,而是循着文学本身起伏演变的过程来确定分期。这方面,《剑桥中国文学史》显得尤为突出——它将先秦与西汉贯连,把西汉、东汉分隔;将西晋、东晋分离,让东晋与南北朝、初唐连接;将初唐与盛、中、晚唐分开,而把盛、中、晚三段合并为“文化唐朝”;将明代分为初、中、晚三个阶段,让全书的上下两卷,以明代的1375年作为分界年限;将1937年作为分割1841年到1949年的界年,不按通常的1919年划分界限。这样,充分显示了文学史打破历史朝代拘囿,别创一格的特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抓住了东方中国与西方世界在语言文字上的差异——西方字母书写,东方汉字(方块字)书写,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影响决定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也影响决定了读者对中西两种不同文学表现形式的阅读、理解、欣赏和接受。这充分显示了梅维恒主编作为西方汉学家的卓越之处——该文学史开头部分的“基础”一编,首当其冲第一章“语言和文字”,详细介绍了汉语书写系统的基本元素和主要特征,提出对汉字和汉语主体性质的把握,是准确理解和真正欣赏中国文学的基础和前提。抓住了作为汉语方块字书写的中国文学的根本特色,从某种角度说,这正是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乃至世界范围内其他语系文学最大的不同。能够认识和抓住这一点,是梅维恒主编及其同仁们的慧眼独具,也是这本文学史与其他多种文学史著作相比的出众之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文类、文体、文本为核心,建构起了自身的文学史框架,从而体现了文学本位的思想。相比之下,《剑桥中国文学史》强调了文学发展中的文化因素,将文学史看作了对文学传统不断建构的历史文化过程,尤其关注过往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所过滤,并加以重建的文化因素。可以说,两部欧美版中国文学史,都有着可供中国文学史研究学者借鉴的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很好地参考。
当然,两部欧美版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我们不必回避。比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三、四、五之三章,分别论述:早期中国的哲学与文学、“十三经”、《诗经》和古代中国的说教。单看这三章标题,我们就发现,三章内容显然有交叉重合:早期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这个所谓早期自然是指先秦(也包括西汉),这个时代其实已经问世了“十三经”中的多部经(包括《诗经》),这些“经”,大部分编定时间是在西汉,这就把“十三经”所产生的时间和所包含的内容几乎都包括了;而古代中国的说教,实际上与早期中国的哲学与文学,以及“十三经”(包括《诗经》)都有着关系,我们不能单说《诗经》与古代中国说教有关,其实“十三经”中的其他不少“经”与古代中国的说教也有关系。由此,笔者以为,这部文学史中这三章标题所示内容,实际上很难截然分开,无论是历史年代还是实际内容,现在这样的三章内容,逻辑有点混乱,条理也不清晰。此外,中国早期的先秦时代,实际上文史哲还没分家,其时人们习惯上并没有哲学、历史、文学明显分家的意识,特别是文学,远没有单独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文学史编著者应该在“基础”编中予以特别指出的。还有,该书下卷第六编第四十四章,专辟有“经学”一章,笔者认为,“经学”实际上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它本身是个独立的学科,可划归史学类。如果真为了说明中国儒家经典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笔者建议,可将这部分“经学”内容安排到“基础”编,与第三、四、五章内容融合,重新加以组合,分章予以说明,这样或许会更好些。
因为是集体编著,无论《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还是《剑桥中国文学史》,都明显暴露了体例上的不统一或不规范,这给两书各自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带来了不该有的遗憾。比如,两书的目录部分其实很重要,是全书纲目提要的全面展示,也是全书的核心框架,读者拿到一本书,首先浏览的是目录,以便了解概要、心中有数。遗憾的是,两部书都存在各章标题历史年代写法上的不统一和不规范——有按历史朝代顺序的,有标以世纪的,也有书西历年代的,各行其是、中西混杂。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第三章,章的标题是——“从东晋到初唐”,而章以下节的标题,居然全部标以“世纪”,真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还有,如《剑桥中国文学史》章节标题中所列的作家作品,显然不符合历来文学史对其成就与地位的评价,如曹操、建安七子居然未见于章和节的标题,而杜笃和冯衍却入了标题,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重要的文学理论代表著作,居然章和节的标题难觅踪影,令人大跌眼镜。这在中国学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绝对不可能出现。凡此种种,都是瑜中之瑕,有待改进。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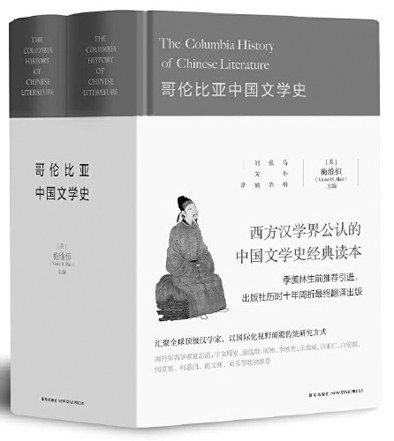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