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使命之一是揭示生活的秘密,浙江作家张忌、雷默、杨方和朱个对生活有着很强的感悟能力,他们以自己富于灵性和个性的笔触,追摹过往生活烟云,为岁月留下印记,给当代现实中的一个个鲜活个体立心立言,启迪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人生,作品的饱满度与完成度,都十分令人欣喜。
张忌出生于1979年,文学创作上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他的不少作品厚重蕴藉,长于深入探求人生,于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中,揭示世道人心。长篇小说《出家》没有简单罗列社会世相,而是于个人和家庭的颠沛中,见出世间各色生活。作品中的方泉和秀珍是这个世界上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组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家庭后,为求生存而陷入日复一日的琐碎烦恼,主人公在小物事的推移变化中,看着自己的孩子出生长大,见证着小日子在大历史变迁中的颠簸,那些充满细枝末节的悲苦未必有多少惊心动魄之处,却真切演绎着我们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诸种负杂,从而提醒人们,在看似习以为常的日常中,有着更值得关爱的广阔,有着更须放眼挽回的人生。从长篇小说《南货店》我们看到,由老马、老吴、老齐和秋林构成的小世界,逐渐在时代的冲刷中发生着不经意的裂变,小小的南货店所容纳与盛放的,有世情图景,更有命运沉浮中的残酷与温情,秋林人生的多次峰
回路转,对应和诠释着生活中的多种可能性。但小说贯穿始终的是人作为个体努力挣扎中的坚守,对自身价值的不懈探寻,张忌善于揭示人生百相中的人心隐秘,揭示出被宏大话语遮蔽的更为丰饶的一切。秋林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既是大历史的参与者,又仿佛是一个随身携带着一只万能摄像机的旁观者与记录者,全方位、不动声色地记录下周遭事物,一路沿途发生的一切,既见作者自己之心,也彰显时代和他者之心。《出家》《南货店》延续和发展了张忌诸多中短篇小说的风格,有局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致,更有对时代大势的透彻领悟,结构宏大,构思精微,民族气派、现实主义,美学上承继了中华美学的理路,作品弥漫着的浓浓的“乡愁”,纸上重构了立体的江南,汤包、酒酿圆子、冬笋肉片、姜丝黄酒,以及斧头包、象牙秤、紫檀算盘,日常生活中具体的物件,既作为江浙地域内符号化的“风味”,又是代代相传的人间真实样态,让文本更为厚实可感。
雷默引起文坛注意已经有一些时间了,记得我数年前阅读的短篇《祖先与小丑》时,就对其巧思与结局留下深刻印象,他的作品篇幅不长却余味无穷。作品写到,祖先故去一个耐人寻味的结果,是在葬礼过程中给未来的后代留下一个名字,提醒后来者抓紧时间延续生命。如此,逝去的
长辈、承担延续血脉的小俩口及最终被命名为小丑的孩子,看似使情节带有偶然性的特点,实则暗含了生命流转的一些“规则”。从前一代到下一代,血脉的流转传承每天都在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先辈逝去了,人们以为会慢慢地将之忘却,其实根本无法忘却,后代普普通通的一句问话,便可以使人顿时内心柔软起来,血缘的自然规律难以抗拒。小说《告密》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引发的血案”,写了由“揭短”引出“打脸”,再引出一个命案,牵扯出一个个很复杂的话题。在封闭小镇的现实生活中,“话传话”在不经意中导致的,看似是一次次偶然事件,实则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是经常发生的贫与富、疏与亲、自卑与尊严的持续较量,小说只不过揭开了人性的一角,把人心的复杂多变展示给了大家。人生中那些无常和不确定不对等,迷惘的亲密的及隔膜的一切,是雷默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话题,作家经常营构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情境,赋予小说丰富的意义。他喜欢用第一人称叙事,《大樟树下烹鲤鱼》《祖先与小丑》《幽蓝》《告密》《你好,妈妈》无一例外,这些作品里面大多有一个明智的叙事者,见证着人间发生的一切,与小说里的其它人物一起欢笑和悲伤,生活细节得以纤毫毕现的展示,使人回味无穷。
朱个的写作状态始终很放松,在小说创作方面,她从不做超
出自己能力的事情,其作品大多取材于熟悉的社会生活,自自然然、力所能及地经营着文学小天地,举重若轻。在她的文学领地里,经常出现是男女间的小吸引、小风波、小失意,没有赴汤蹈火的大事,更无争优创先的追求,那些都市里的教师、文员、白领及准白领们闲适自在,并且不时陷入种种的不如意,更抱着很大的希望,像是要去费劲地拼一个完整的图,但最终发觉,即使找到了相邻的一半,也已经时过境迁,况且,人们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机会找到相邻的那半拼图,就像写东西,涂涂改改,折腾好几次,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字句和感觉一样。朱个还善于写人物身上说不清、道不明,又时时影响着人物正常生活、正常感情走向的“暗物质”。恰如《暗物质》里的萧遥所感觉到的那样,“无数人在她呼吸间赢得人生常规赛的规定分数,而她不仅犯规出局,至今还在孜孜不倦地练习着自选动作。”她们试探着接触异性、试探着走到更远的天地里去,但总不能如愿,或总是事与愿违,如小说《夜奔》所说,“三月的柳枝是细碎的鞭子,带着绿色的小倒刺,如若树下经过的一个人正有颗柔软的心,那不免要被抽打得千疮百孔。”小说《火星一号》和《秘密》里有个同名人物左辉,他似乎没有什么生活目的,无论声称怀有乘坐“火星一号”向火星进发的梦想,还是手持照相机招摇过市,他内心的空虚,行为的荒
诞都是一样的,朱个像是手持锋利的解剖刀,不经意间挑开了现代人某些病症绚烂外表之下的伤痛,促使人们去深入思考。
杨方是创作上的多面手,其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曾入选2009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由诗歌到小说,跨越令人惊喜。杨方长于书写普通人及所处的困境,《苏梅的窗子》里的主人公苏梅在小说中是一个逝去的普通农民,出乎亲戚好友的意料,她生前曾经公开与一个叫高峰的男人同居,死后她手机里被发现留存着的一组尺度惊人的照片——身上什么也没穿,在毫无遮拦的窗子前被拍,更颠覆了人们对她的认知。就这样,围绕一个人的逝去,各色人等的嘴脸得以显现,而主人公死后被翻出的照片,从另外的方面说明,人在精神层面的兵荒马乱原来如此的普遍。小说《不会是世界尽头》围绕老人临终所展开的一场人性两难的较量,揭示了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假使老人已病到失去任何治疗价值,在陷入经济与精力的双重压力之时,儿女和配偶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这是作者揭示出来提醒与我们共同思考的。杨方的作品大多带有鲜明的新疆背景与底色,故乡对她的文学建构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伊犁、伊宁、羊毛胡同等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边地的气候、物产、植被、水土、食物,甚至语言,被嵌入了小说的结构之中,大
巴扎、博格达山、亚麻、胡麻、啤酒花,是作者回忆的对象,同样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和经常见到的风物,而在《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里,作者还写到了曾经的俄罗斯人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种种影响,一只手风琴所链接起的人生际遇,人在历史与现实中的际遇,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以及人物的个性在小说中得到很好体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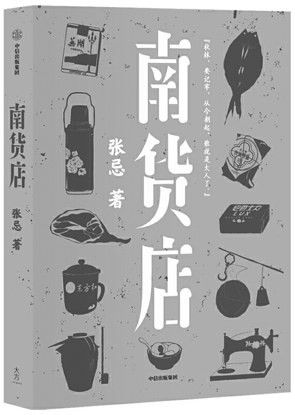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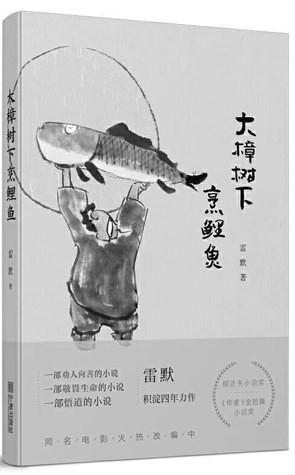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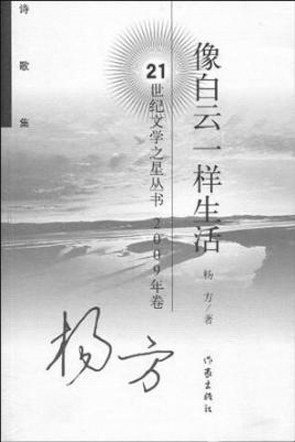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