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闻一多曾提出著名的“三美”主张,“音乐美”和“建筑美”着眼于新诗形式建设,“绘画美”则旨在克服早期新诗的浅露直白。后来艾青为“绘画美”带来新的气象,但其借鉴主要是美术的。
真正让诗歌意象摆脱排比句似的简单堆砌,让画面流动起来有一定叙事功能而又不过于破碎的,应是诗人痖弦的创作。他的《上校》《坤伶》《C教授》《红玉米》《乞丐》等诗,其词语连缀方式如同电影蒙太奇,将一个个意象镜头连接成有意味的片断。
有人说痖弦主要受戏剧影响,但戏剧基本单元是场面,只能在近似真实的有限时空中展开故事;而电影基本单元是镜头,场面衔接自由,节奏可快可慢,时空不连续性是其重要特征,更与诗歌艺术有融通之处。
《上校》一诗第一节,浴血玫瑰、战场硝烟与断腿负伤的抗日军人,如同三个镜头从远景推至特写。“而他的一条腿诀别于一九四三年”这句诗,大词小用的手法叫人心头一震,幽默感罕有地转向崇高。第三节诗镜头节奏慢下来:咳嗽药、刮脸刀、房租账单、缝纫机前的老伴和小憩的老军人,不复当年英雄气。可那一句“什么是不朽呢?”仿佛是在战场幻觉与和平阳光下打盹的老军人的喃喃自语,又像是诗人在把被时光遮蔽的血色碑铭指给人们看:没有当年将士的民族大义,哪有今天的寻常生活?然后再回味第二节诗,仅仅一句:“他曾经听到过历史和笑”,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其主题和历史观不可能是反讽的。诗中的“上校”形象,如同纪录片中的活生生个体,没有拔高或象征,但琐碎时日连接的依然是生活逻辑的内在庄严:他们老一辈人已经尽了责任,这是无法一笑置之的。
痖弦这类诗总是能够通过蒙太奇般的组合激发想象,展开叙事。词语单个看似乎疙疙瘩瘩的,有些跳跃,连缀起来却挺流畅,同时又能言简意繁,计白当黑,明显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与氛围。正是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让我们容易走进《上校》一诗中的老军人内心。而在《坤伶》中,“杏仁色的双臂”,这颜色用得多么感性,连同“小小的髻儿”的特写,让人叹息天生丽质的坤伶“十六岁她的名字便流落城里”。而“夜夜满园子嗑瓜子儿的脸”等意象,活画出传统戏园生活。台上带枷主角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苦啊……”,究竟是发自《玉堂春》中苏三的还是坤伶自己的呢?然而无论捧红还是过气,都是“一种凄然的旋律”。而《乞丐》一诗,仅仅“关帝庙”和晾晒着袜子的“偃月刀”一组镜头掠过,中国读者眼前便闪现出一幅热闹的江湖场面。再加上市井小调的反复穿插:“依旧是小调儿那个唱,莲花儿那个落/酸枣树,酸枣树/大家的太阳照着,照着/酸枣那个树”。原汁原味中自有一种乡土的感情。
痖弦代表作《红玉米》底蕴厚重,但一开口仍像哼民间小曲:“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这以后不断的重复,让“红玉米”这一意象构成旋律和情调,渐渐有了深意,叫人起了敬意。在此之前,收获的玉米一串串晾挂在中国村庄的屋檐下,如同院子里的石碾、扫帚一样不为人注意,它们只是冬天的食粮。当代新诗中“玉米”的意象多起来,但照例是“金黄色”的,与“翻金浪”的小麦和“沉甸甸”的谷穗、稻穗一起,承担着五谷丰登的欢庆功能。直到痖弦的《红玉米》,人们才第一次注意到,中国乡土风味的玉米是红色的,但不是西班牙斗牛士手中挥舞的那种热烈的红,而是赭红色的,忧郁沉静如同月光下农家小院熟睡时朦胧的光泽。即使丰收的年景也有忧郁,即使“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疯狂地吹着,那吹过玉米串的风仍是血汗挥洒在干瘪的玉米粒上凝结的岁月。正是“红玉米”一遍遍风铃般穿透的沧桑,我们才进入了遮蔽久远的过去,看到了故乡的雪、道路、乡村、先人和曾经热气腾腾的生活。“红玉米”恰似中国的底色,叫人怦然心动,又沉默不语。
沉默自有沉默的力量,如同诗人痖弦,发表诗作不过百首,至今停笔逾半个世纪,但其佳篇每每令人称奇和琢磨,仿佛诗人从未远离诗坛。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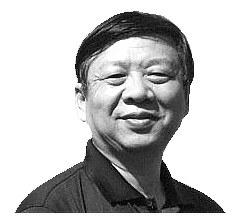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