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写了不少小说,现在终于进入一个摆脱了再去努力证明自己的阶段,会更加随心所欲地找感兴趣的题材和体裁。
“一个人哪能两次落到同一条河里呢?我偏偏就落了两次。”这是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张翎新作《廊桥夜话》中,阿贵妈对古希腊哲学家“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辩证表达的乡土化理解,而在这部反映当代浙南乡村生活的作品中,几位女性人物的命运因时代、个性等因素的差别,存在着变化中的偶然,也有不变的必然,恰与上述哲学表达和现实理解暗合。
已经写作近三十年的张翎曾创作出《邮购新娘》《金山》《余震》《阵痛》《劳燕》等多部讲述中国人在海外或带有海外元素中国故事的佳作,获得海内外诸多文学奖项,但如《廊桥夜话》这样的当代乡村题材写作却是第一次。出生、成长在城市,成年后也生活在城市的她在这部新作“后记”中写道,“我从未深入过农家的真实生活,也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写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不过变化还是发生了。而且,在写作题材、文本呈现方式上的变化,从她上一本作品《三种爱》中就开始了。在《三种爱》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她选取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乔治·桑三位女作家,通过实地探访她们的故居、墓地等留下生平印记之所在,回顾她们的人生历程特别是情感经历,亦对她们的作品有另一层面解读。这样的探访与写作,在张翎此前的创作中也没有过。
因新冠疫情在加拿大多伦多居家的日子里,十年前已辞去听力康复师工作的张翎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精力投身阅读和写作。拜当今网络社交方式多元、便捷所赐,日前,张翎通过微信、电邮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谈到《廊桥夜话》《三种爱》的缘起和写作过程,也说起了她现在的创作状态。
中华读书报:《廊桥夜话》“后记”中提到这部作品的写作缘起,以及您听到建议您涉猎乡村题材写作而没有松口,当时没有写,出于怎样的考虑?后来怎么又动笔了?
张翎:在创作《劳燕》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一群关爱抗战老兵义工队成员。其中有小江和阿田(化名),两人老家都务农。他们和我讲一些发生在乡野的趣事,听起来像江南农村版《聊斋志异》。他们都希望我能写写他们的乡野,可是这对我来说,是隔了很多层的生活体验,我一直未敢轻易动笔。
2019年春天,我恰巧在温州,不时和小江阿田聊天。小江讲起他们村里的廊桥,还有与廊桥相关的一些民俗民风。小江嘴里的廊桥,是浙江泰顺县境内一系列特殊桥梁,和《廊桥遗梦》里的美国路桥南辕北辙。小江还谈起了他们村子里的越南新娘。小江老家处在浙闽毗邻之地,和大部分江南平原地区相比,属于贫困区。前些年,有些家境窘迫、身患残疾或者长相欠佳的大龄男人,因交不起娶当地新娘的彩礼,就通过中介讨越南、柬埔寨女人为妻。
那次我跟着去了小江老家,和小江家人有了接触。数年来小江讲给我的乡野家族故事带给我的灵感,一下子落了地。以我的写作习惯,很难完全凭案头资料动笔,采风几乎是必经的历程,连《三种爱》这样的非虚构作品也是如此。那次春耕之旅带给我鲜活的生活印象,小说就有了一些地气作铺垫,写起来感觉气场顺畅。
中华读书报:感觉《廊桥夜话》的故事走向还有继续展开的余地,或许这个故事具备一部标准长篇的体量,为什么没有写成长篇?
张翎:这是我不熟悉的农村题材,可以从离乡多年的留学生阿意回乡探亲的角度书写,但也只是浅尝而止。更长的篇幅需要更深切的生活体验。以后当然可以探索这个可能性,但现在不行。
中华读书报:《廊桥夜话》涉及三代女性的情感和命运走向,以前采访您,我也提到过您的作品中女性角色塑造尤其出彩,一方面,这应该与您的女性身份有关,另一方面,您会将此视为某种“局限”吗?
张翎:只能说在书写自己的性别故事过程里,运用想象力时可以少费一些力气,毕竟有些经验是现成的。作家能把自己的性别写好,然后尽量真实地写出从自己性别眼中看到的异性,已经很奢求了,所以我不视书写女性为“局限”,尽管我也不只写女性,比如《劳燕》《金山》,都很难说是女性人物占中心位置的小说。我在写作时没有特别清醒的女性意识,在性别认同的问题上,我不属于格外的警醒者。
中华读书报:看到“后记”中小江的乡土回忆,还有您实地体验的乡土风貌,感觉《廊桥夜话》是虚构作品,又有浓厚的写实性,书中若干人物都有现实对应,在现实之外,书中哪个人物是您纯粹虚构的,设计这个人物有哪些文学层面的用意?
张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阿意是《廊桥夜话》中一个纯粹文本意义上的“虚构”人物,因为小江阿田的乡野故事里完全没有这个人物,我借了她的眼睛看故土。但是这个人物,反而离我最亲近。同样经历过留学大潮、在海外摸爬滚打多年的我,不难理解这个人物对故土的复杂感情,故土是在她离去的那一刻生出来的概念,却会在她回乡的那一刻消失。这种若即若离的心理已伴随我多年。用阿意的眼光看故土,在乡人眼里是硌硬夹生的,但对我来说完全真实。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国内现实题材避而远之,感觉自己缺乏现实感受。现在我觉得可以尝试,因为我接受了自己是局外人的现实,局外人的感受也是一种感受,所有的感受在文学和美学的意义上是平等的。
中华读书报:《廊桥夜话》的写作,在您的写作经历中算是相对轻松、顺利的一次?
张翎:这是无心插柳的作品,不需要做大量案头,而且与故事发生地的人物有着亲切贴身的感觉,写起来自然妥帖。因为毫无奢望,所以随心所欲地追着感觉走,反而情绪充沛。这是一次奇异的尝试,离我个人生活经验很远的经历,却没有感受生涩挣扎,整个过程饱满快乐。写完后第一个给小江看,他说“还像那么回事”,我立刻乐瘫。真希望每一次写作历程都是这样的——那当然是白日梦。
中华读书报:与《廊桥夜话》中侧重女性人物与话题的写作相比,《三种爱》则是关乎三位女性不同情感经历、人生的书写,在不同之外,她们也颇多殊途同归之处,您怎样看待她们命运、情感经历的共同点?
张翎:《廊桥夜话》和《三种爱》中的女性,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但她们在精神和物质生活层面上有一些共同追求,都渴望在婚姻中有情感沟通,都希望能掌控钱包上的拉锁。其实她们都在追求伍尔夫所说的“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道出了人类(不拘泥在女性上)的某些永恒不变的普世追求。这个话题,还会被小说家不停地发掘更新。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西方文学阅读谱系中,女作家的绝对数字想必很可观,为什么选择书中这三位作为书写对象?
张翎:我有一系列感兴趣的欧美女作家名单,如伍尔夫、奥斯丁、勃朗特姐妹、蔓殊菲儿、乔治·艾略特、玛丽·雪莱、杜拉斯……选择这三位,是因为她们的故居或墓地落在了我采风相对顺脚之处。从兴趣来说,这一群欧美女作家离我早年的英美文学底子最近,能引起我许多灵感。
我当然希望能够持续写出系列作品,但是需要考量采风的巨大成本。比如蔓殊菲儿是我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但她的故居和纪念馆在新西兰,跨越重洋的采风之旅对于我这样完全独立、很难得到任何体制资助的写作人来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你也知道,目前作家得到的稿酬与这样昂贵的调研成本不相匹配。所以我只能顺其自然,看下一阵风把我吹到哪个角落。
中华读书报:从《三种爱》到《廊桥夜话》,接连两部作品都不是你既往写作中的常见文本类型,这两类写作是否会在您接下来的创作中占据一定的比重?
张翎:我已经写了不少小说,现在终于进入一个摆脱了再去努力证明自己的阶段,会更加随心所欲地找感兴趣的题材和体裁,当然也可以选择什么也不写,完全安静读书行走。对将来的写作没有任何计划,也没有任何禁忌,可以进行任何一种形式的尝试。应该会有不同的作品出来,完成后再告诉你。
中华读书报:在海外这么多年,感觉上您以纯粹海外生活经历为背景的作品并不多?
张翎:这三十多年,我行走在大洋两岸,对于哪一岸来说我都是游客和观察者。基于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观察是我写作的基石,我不太会去写完全脱离中国元素的“海外”故事,也不太会写完全脱离海外元素的“中国”故事。我的小说大概永远是发生在国内、但夹杂着海外元素的中国故事,或者是发生在海外的中国人故事,或者是这两者的某种掺杂。我无法改变文化意义上的“失根”和“夹生”现实,只能在这两个庞大的文化传统之间找一个空间,写一些独属于我个人感受的故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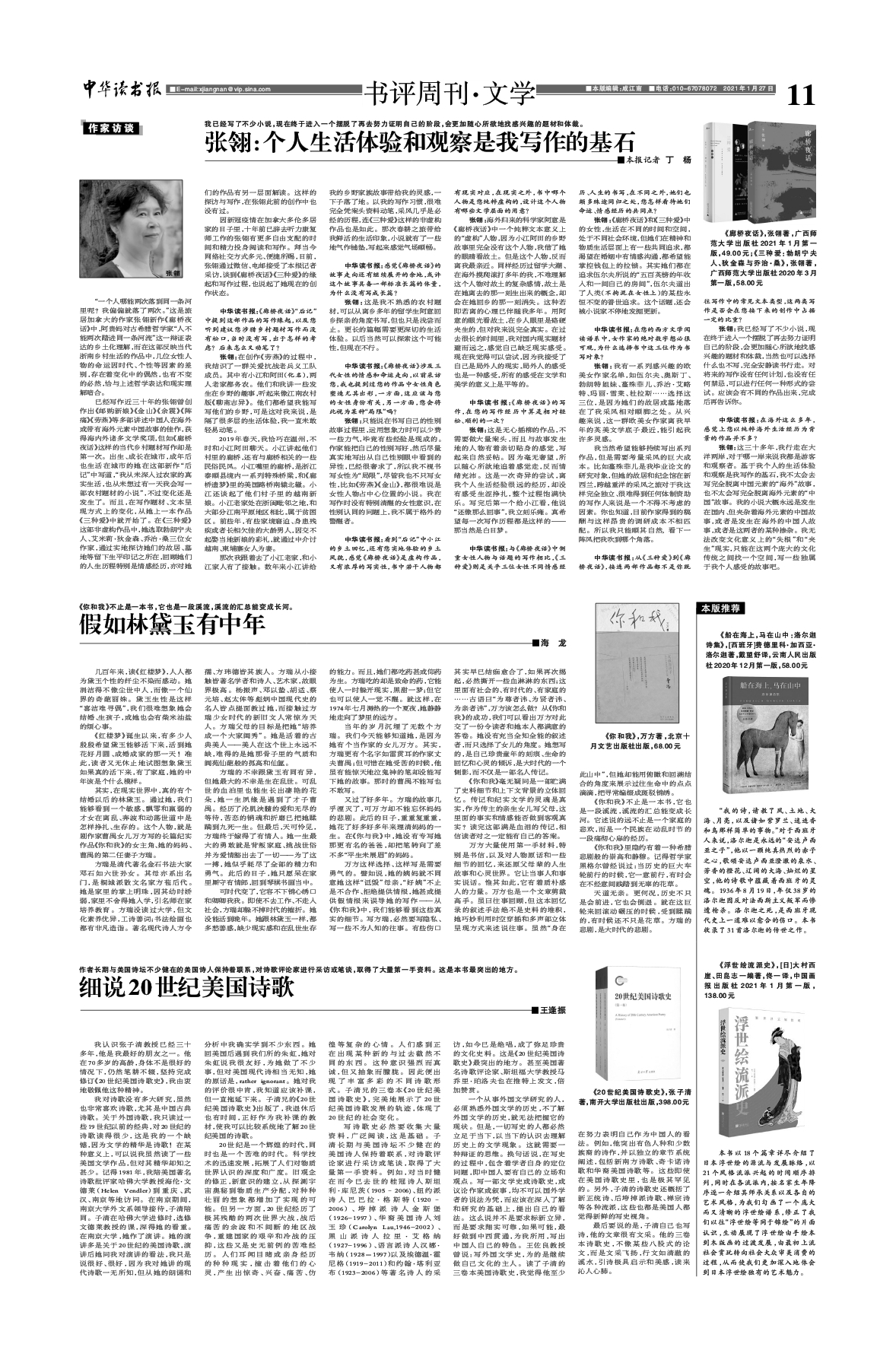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