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文不甚深”,相较后世某些文派,反而是明白易懂的,但对于大部分现代读者来说,直接进入《史记》文本依然是有门槛的。此外,《史记》是司马迁在经历了巨大磨难之后所成的“一家之言”,纾忧发愤,甚至被称为“谤书”,因此,即使具备了一定古文基础的读者,在读懂《史记》文字的同时,能否读出司马迁蕴蓄其中的史观和情感,仍不好说。因着这两点,循着专家的引导,逐步进入《史记》的世界,便成为一条走进经典的可靠路径。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就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引路”之作,此即“陈正宏讲《史记》系列”。该系列共4册,第一册为《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
陈教授讲《史记》,不光讲文本,讲故事,更把重点放在《史记》的编著史上,讲承载这些故事的文字是怎么来的。正如作者《后记》所言:“我在本书里讨论的,更多是《史记》的各篇是以什么样的文献为基础被编写出来的,以及为什么它们会呈现这样或那样的文本面貌。”举例来说,《秦本纪》写得详实精确,是因为可资利用的文献多,而战国七雄中其他六国历史的记述就较为单薄,这是秦朝焚书,把秦国之外史书销毁殆尽的结果(《六国年表》叙文中,司马迁感慨道,他编年表依赖的“独有秦记”)。再比如《史记》记载商纣还没灭亡时西伯就已经称王,且在伐商成功后砍下纣王的头,这些记载遭到后世儒家学者的质疑,但司马迁还是写进书里,因为,唯一能让他尊重的,就是看到和听到的“文献”,他的写作不会被任何既有观念所束缚。还有,《三代世表》矛盾之处很多,司马迁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还是决定向孔子学习,尊重原始文献,“疑以传疑”,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通过对《史记》成书过程的分析,司马迁对历史的看法以及作为优秀史学家的卓越之处,便一点点呈现出来:“他似乎更喜欢让自相矛盾的史料在他的大书里互相较量争斗,以此显现历史的纷繁复杂与难以捉摸。”
陈教授还通过对古代文献形式的分析,来推测《史记》所遭逢的命运。比如《天官书》大胆的劝谏和《封禅书》辛辣的讽刺能逃过被删削的命运,应该就与古代的文献形式有关,即目录在最后,配有提要,古人读书先看提要,特别在纸张发明之前更是如此,由于这两篇的提要司马迁写得十分“官方”和“平庸”,故很有可能武帝不再有兴趣读下去,从而躲过了像《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被删那样的劫难。
更进一步,陈教授是借文献解读的方式,来探究司马迁写作《史记》时的隐秘心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司马迁时时不忘观照现实,尤其是自己身处的汉武帝时代。将《五帝本纪》作为全书第一篇,除了司马迁时代认为黄帝是历史之始外,也有如下考量,即朝思暮想做神仙化黄帝的汉武帝被层出不穷的方士骗得团团转,司马迁对此深恶痛绝,才写了这么一个带有明显人性的黄帝,而且置于首篇,作为后世历代帝王的榜样。另外,不吝溢美之词描述文帝时代政治的宽松,比如“除肉刑”,就是为了反衬武帝时代的专制残忍。
第二,《史记》写历史,终极是写人。陈教授说得明白:“(司马迁)借着描述一个很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把人性的各个方面加以彻底揭示。”因为“推动任何特定区域历史演变的基本动力,其实是生活在这个区域中的人的普遍人性”。正是因为聚焦在人和人性,才更显出《史记》的深刻与超越时空的魅力,也是它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中显得卓尔不群的根本原因。举例来说,《史记》以后的正史中基本都有《地理志》,相对客观,而《史记》却独有自然与人事纠葛的《河渠书》,讲漕运和水患,说明司马迁更关注制度背后的人。再比如司马迁在《礼书》中鲜明阐述自己对于礼仪的理解:“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此外,《平准书》写经济,但并不关心具体的经济数字,而是围绕经济写经济以外的问题,最后的“太史公曰”写道:“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更是说明司马迁关注的,始终是历史中的人,以及人的活动导致的历史变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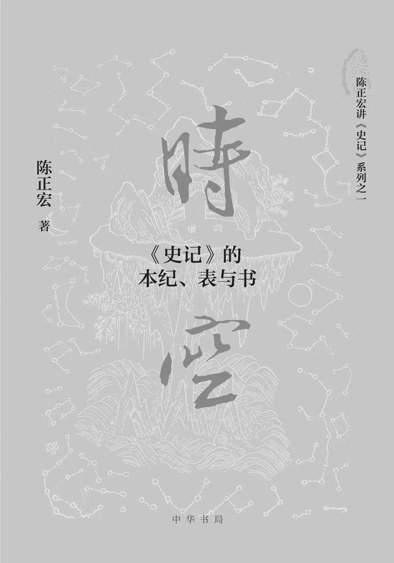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