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可以任性,想不到有人写书也这么任性的。”我一拿到江弱水的新书,就翻到这么一句玩笑话。他真的想不到么? 开篇写罗隐的那篇,他说《迷楼赋》“有一种任性的调调儿”,我看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的文章。但不同于罗隐的是,心态却未必放松——江弱水向各位看官试示的,并非一割的铅刀,而是反复磨洗的吴钩。他不甘心文章被人认定为“随笔”“小品”。《十三行小字中央》二十二篇,不故作高论,但都经锤炼、剪裁,弘深肃括。
江弱水又何止任性,简直任侠。他的招子亮而且狠。不过拿“侠义”来形容江弱水不太恰当,这个“义”字被他在《〈水浒〉里的人情》中掀翻了:哪怕最讲义气的《水浒》,“义”也是充当“人情”的门面。江弱水的侠行是不讲人情的,其行迹近乎游侠,而修为堪称散仙。他以郭在贻《训诂丛稿》修理《杜甫全集校注》,凭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黜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旁征博引非为自矜,是祭法宝的姿态:请宝贝转身! ——然后径取人首级。江弱水对待引文,像陆压那样要打上一躬,因它们非仅工具性的法器,他欣赏这些伟大的灵物。收回之际,卓烁异彩仍能削去《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顶上三花。
作者的神通,就是打破了某些传统习惯。这种“颠覆”往往不是创造了什么,反倒把平日里“狃于常识,囿于错觉”的歪门邪道暴露出来,泄露本该是天理的“天机”,美文、课文的恐怖勾当无所遁形。这样洞若观火的能力原应是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可在今天属实稀罕。
《十三行小字中央》读了每每拊掌,想跟作者浮一大白,借微醺的劲儿笑劝他:饶了那帮人吧! 在他们眼里,自己还是被人供着的、了不得的文曲星呢。
虽然江弱水自谦于古典文献和考据是“门外汉”,但无人不服膺他的考镜与细读功夫,便是真立在门外,只无那些冬烘先生的习气,不是学院中人而是书斋中人,所以写得煞是好看。他又不肯安坐,从网上拍卖场经过,入眼一件“朱竹垞太史审定南宋拓本十三行”,便借了来组缀章句,敷叙兴致,铺陈朱彝尊的恋情秘史。其实上头早有姚大荣三万余字的《风怀诗本事表微》比勘精严,分析详密,极尽迤逦委曲。但江弱水别出机杼,能以一己心绪接古人情思。与之相形,孙康宜《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大体承袭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而来,谢正光批评孙著的大量主题、材料、术语、结论,甚至失误,都直接搬移《别传》,亦步亦趋,神踬而情涸,真是何苦写这么一本书。
学人文章,有涉拍卖品者似不多见,如谢正光《倪瓒〈霜柯竹石图〉之新赝与旧伪》写2006年嘉德拍卖藏品,全篇以诗文著录佐证其真假。江弱水则对拓本本身价值不感兴趣,由此细节稍显疏忽,醉翁意难得糊涂,且容细表。
据传《洛神赋》碑版打捞自西湖,于是龚自珍说,玉版拓本“有篙痕者善”,这就是说那“墨老虎”上会印出原碑突兀凹陷的白斑。江弱水认为“篙痕”实指王献之真迹所在麻笺的“粗麻筋”,我权用网络语言回应:华生,你发现了盲点。“篙痕”之说,确为附会。本处知识点大概触及到了江弱水的盲区,他的推断亦不准确。
“粗麻筋”,或是江弱水理解中古纸表面混合的麻丝、线团、绳头等杂质,但这种现象多见诸西汉早期造纸的粗糙产品。如今能看到的麻纸出土实物,即便稍早的东汉“旱滩坡纸”,业已纤维组织紧密,分布匀称。世所皆知,天下第一的王羲之名笔《兰亭序》系用“蚕茧纸”写成,按照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的观点,蚕茧纸即是“麻纸有滑泽者”。老子的纸细腻如此,儿子的笺卷又会差到哪里去呢?
再者,纸片不够匀净,作书顶多是笔画微皴,断无“斑驳满深创”的道理。书中附了图片,十一处空白“篙痕”分明可辨,正是“篙头”似的鸟蛋大个疤。杨龙石的跋语说得很清楚,盖因宋人在玉版上钩摹原迹之时,麻笺已有缺蚀,工匠照样保留罢了。打捞时的一尾竹篙能将玉石凿得坑坑洼洼,那才不可思议。何况这块“碧玉版”,后来证实是山上挖出来的,用不到篙,料想工人也不至粗暴到留下“镐痕”。江弱水此番是献疑却误解了。
然而文章可爱,也正在于这“篙痕”。江弱水盛赞郭在贻对杜诗的诠训,也微憾郭氏的解释也不是尽善尽美。痛快批驳孙著的谢正光后来同样发现自己存在疏漏,将《朱子庄雨中相过》的朱氏错当成朱重容,而子庄实为表字相同的朱茂暻,他的侄子正是朱彝尊。
落回到号称朱彝尊重新装裱的这件拓本上来——且慢,这“落拓”倒能望文生义地刻画江弱水:不谐世俗,自是不消说了,否则他也不会做这些文章;不护细行,也不在乎有没有,乐得在泥巴里曳尾伸脚。但我未能免俗,到底煞风景地检索了拍卖纪录:“朱竹垞太史审定南宋拓本十三行”最后以二十万五千人民币成交。
江弱水倾心顾随、俞平伯,二人同属传统色彩较浓的学者系列。江的治学经历有意无意追随了这一精神谱系。他博士毕业进入国际文化系任教,相当熟悉西方文学理论,却始终力求“援西入中”,使之与中国古典诗学融会贯通,使当代中国的诗学活泼、周正,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
我们都读过《撕扇记》了,知道江弱水不同意读书是读“气质、声调、品位、身段”,那读此书读的是什么? 至少我承认,我乐意读江弱水的“格调、韵律、音节、意趣等等”。这是他摘引的潘天寿诗论,绘画能与诗相通,挪到文章上无疑也成立,毕竟文章“无非是诗歌以其他方式的继续”(布罗茨基语)。江弱水说,诗人只把名字留给了诗,他笔名“随便加上”的一眼“水”,让人想见其“文”:一支如棹的大笔,时到中流击水,激荡成文。但做无韵之文章,从来都不是放松的事。
此中心思,甚至不需翻找书里边的字眼,只看书名,“十三行小字中央”,仄平平仄仄平平,没有一个难字,免于繁简转换的错位,题签一竖排列,基本沿中轴线对称。这教人想起张大春得意于《大唐李白》书名四字分属平上去入,可是张大春通晓平仄,稔习旧诗,并不是为了写《大唐李白》,更不是为了写这个书名。江弱水当然也不是为写下七个字的书名。也正是文同此心,心同此理?
《十三行小字中央》较江弱水以往的著作,更多些自由的小趣味,既非黄钟大吕,也非里巷小曲,但和者亦寡,若论感均顽艳,那是不可能的。不过,写作者放言高论,但求惬于己心,别人怎么想有甚要紧? 謦欬之间,我还是能听辨江弱水一把好嗓子,只要他愿意,随时能“喉啭引声”,唱出“真挚而深切的热情,甘美的情味,销魂而广漠的哀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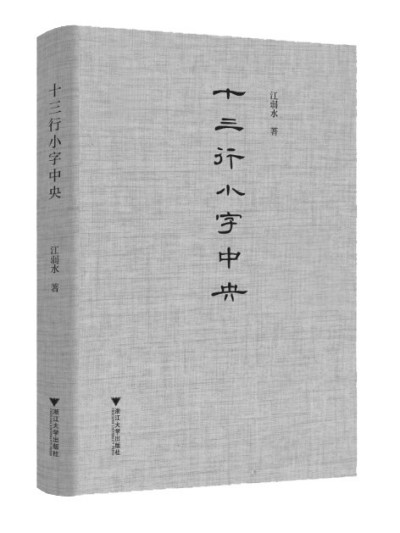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