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质见证”。它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见证历史,见证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文物的教育作用,更是显而易见。它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美的外在形象,具有不同反响的感染力。因此,人教社的历史教材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物知识,同时还遵循我国“左图右史”的传统,使用了大量文物插图。人教社的领导和历史室的编辑们对文物作用的重视和发挥,使我以文物为媒介和人教社结缘。随着岁月的发展,不仅关系日趋紧密深化,而且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我由学习历史课本的小学生、中学生,变成了历史课本编写者、审读者。
1962年5、6月间,馆办公室将人教社寄来征求意见的一套初中历史教科书批转给我们部门(当时叫群众工作部),要求我们认真阅读并征询专家意见后,直接反馈给人教社。因为我是讲解队伍里学生组的组长,部门领导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赶忙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先后请沈从文、史树青先生审阅,并记下他们的意见。不久,王剑英先生代表人教社来听取意见,这便成为了我和人教社历史室的第一次直接接触。5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王剑英先生一手拿本,一手拿笔听得非常认真,还一次又一次地询问这意见是沈先生的还是史先生的。当时我们主要就课本的插图提了一些建议,希望多一些文物和历史人物的插图,如四羊方尊、司马迁访大梁、黄巢、毕昇、李自成等。许多建议都被采纳了。
自第一次接触后,联系日加紧密,其中和臧嵘先生、王宏志先生联系最多。凡有重大考古发现我和他们都会及时沟通,以便尽快在课本上有所体现。比如,越王勾践剑、曾侯乙墓编钟、马王堆帛画、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等,都在考古发掘不久就进入了历史教材。1983年初中历史课本上册在小注中写道“禹都阳城即是今天河南登封”。恰好我馆考古队参与了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发掘,我本人不仅到过现场参观,还参加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登封发现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是阳城遗址,但还不能称为都城,更不能确定是大禹建都的地方。为此我将相关信息告诉了臧嵘先生,第2年的教材便删去了那句话。还有一次,我看到课本讲明代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和王宏志先生通电话,按最新研究情况改为东起辽东。1980年有专家写文章称“灞桥纸不是纸”,颠覆了几十年来的社会公认,造成很大影响。同时有社会团体坚称蔡伦发明造纸,不是改进造纸,要求课本作修改。为此臧嵘先生打电话问我历史博物馆是怎么处理这一问题的?我告诉他中国通史陈列中仍然陈列着灞桥纸,仍然讲蔡伦是改进造纸,而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人教社便以依据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为由,拒绝了那些人的要求。
对历史教材中文物知识的关注,也促进了我个人的成长,原本我对那些文物也知之甚少,以著名的司母鼎为例,我刚从事讲解工作时只能按照讲解稿上写的讲4句话:“这是商代的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是商王为祭祀他母亲而铸造的,反映了3000多年前我国青铜铸造业的高超水平。”那时连“司母戊”三个字铸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在日常我接待的观众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学生,为了有更好的讲解效果,我就在熟悉历史课本上狠下功夫,不仅每年都买一次新课本,认真看其间的各种变化,还到几所中学去旁听历史老师给学生上课。对其中的文物知识更是多方求教,史树青、王天木、沈从文、杨宗荣等专家是请教较多的几位。他们不仅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而且还介绍了一些书籍文章。正是在这种学习中,我才发现了课本中文物知识的某些错误,同时也注意到中学历史教师在文物知识上的盲区。随着文物知识的积累,我在1982年夏天,大胆向北京崇文区的历史教师提出给他们讲一次历史课本中的文物知识课,没想到竟然一炮走红,老师们一致反映我讲得非常实用。很快,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历史教研室就邀请我给全市的历史教师连续讲了13次文物知识课。这次讲课还直接造成我编写的《中国历史文物常识》出版发行,这是我正式出版的第1本书。从上述过程上看,可以说文物知识使我和人教社双双受益。
2000年6月,我到了退休年龄,突然接到王宏志先生电话,邀我到人教社谈编写七年级历史教科书事。到了社里才知道由我和马志斌先生共同担任此次教材编写的主编,这实在是太意外了!自己没有高等学历,没有中国历史和教学教法的学术论著,没有社会知名度,怎敢担此重任。然人教社就是要不拘一格选主编,加之陈梧桐、臧嵘、余桂元等的诚挚鼓励,推脱一番后,我就硬着头皮应承了。接下来的日子成了我既非常紧张又极为充实的时光,白天和大家逐章逐节、一字一句地认真研读、推敲,晚上带着问题查资料、写文稿,12点上床都是早的。各位编辑那扎实的功底、严谨的精神、负责的态度、协作的氛围,使我收益颇多,可谓终生难忘。上级领导要求这套书的编辑应有一些创新,大家设计了导入、练一练、活动与探究等新栏目,我大胆提出每节课后设一“自由阅读卡”,讲一件与课文相关的文物小知识,既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又可以拓展他们的视野。建议得到编委会领导和各位编辑的一致同意,我也承担了这一小栏目的撰稿工作。这个小栏目,大大丰富了课本的文物知识量,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后来其他一些省、市编的历史教材,也效仿了这一做法。
当时为了使更多教师更好地认识和运用这新编教材,人教社在多个省市举办了教师培训班,我按照历史室的安排在培训班讲授教材中的文物知识,先后到了太原、佳木斯、三亚、昆明等10多个地方。由于历史教师们在任教前,都没有系统学习过文物知识,在教参中也不可能对文物知识作更多介绍,所以我向教师们较详细介绍了教材中的文物知识,还讲了一点在课堂上如何运用这些文物知识的建议,使他们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我还带了彩陶片、瓷片、石斧、小铜镜、钱币等标本给老师们触摸,以加深印象。特别是在屏幕中展示出秦兵马俑的彩色复原图时,往往都会传出一片惊呼声,老师们大多会流露出惊喜的眼神。2016年起我和马志斌主编的教材被齐世荣总主编的教材所取代,然人教社组织教师培训时,仍安排了我的文物知识课,这反映了文物在历史教材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教社在历史课程中安排一定的文物知识,确属于明智之举。
2016年人教社遵照教育部意见,历史教科书采用全国统编教材,这使我有了又一次和历史室深度合作的机会。当年约5月的一天,余桂元以责编身份告诉我采用新教材的消息,并邀我配合新教材为教师录制一些有关青铜器的解说。为此我希望能看一下新教材,以使所讲内容更贴近教材。当我打开新教材后,发现有关文物的表述有欠严谨的地方,比如: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织布机”(实际只发现了两个不知用途的小木棍,有一位专家认为可能是卷布轴),“在已发掘的三个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陶俑和陶马共有8000多件”(实际上只出土了1100多个,专家推算可能共埋藏有近8000个)等。这令我非常担心,深夜便和桂元联系,请他向领导反映。很快相关领导同志来电询问,并在人教社安排了一次座谈会。那次,我和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的一位专家提出的教材中和文物相关的修改建议都被当场一一采纳。
这次座谈会,给与会者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其中李卿在场可能感受更多一些。后来,在她主持编写澳门地区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时均在完稿后亲自邀我审读,她诚恳认真的态度使我更加用心细读。大到一件文物的选用,小到一字一词的表述,都一一关注,尽量避免纰漏。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们通过电话反复切磋,那情景也堪称抗疫中的浪花一朵。
时光荏苒,人教社迎来了建社70周年,屈指一算,我和人教社合作也快一个甲子了。希望在有生之年,继续发挥余温,为历史教材中更恰当地选用文物知识和更生动、更广泛地讲述历史教材中的文物知识而努力奋斗。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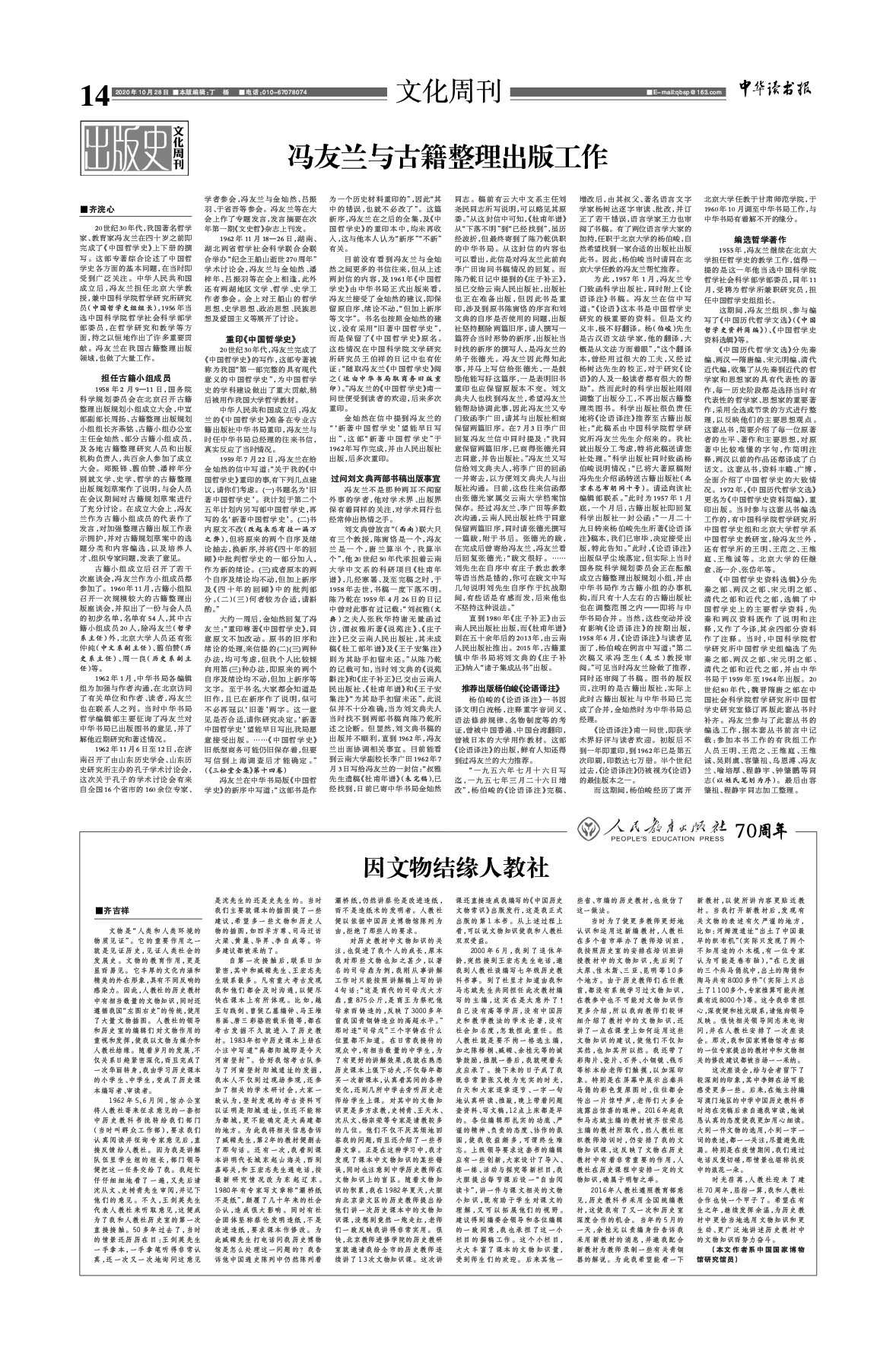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