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饰(珠子及小型饰件)具有装饰、宗教、货币,以及财富和地位象征等多重作用,更因其美丽、稀有、便携、耐久的特性成为地区间远程贸易的理想商品,是文化、经济和技术交流的重要载体。
西汉武帝时期派遣船队前往东南亚、南亚进行海外贸易,正式开通了官方海外贸易交通航道,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珠饰成为汉王朝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中海地区输入的奢侈品,以至有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宝石之路”。
建城始于公元前214年的广州,秦汉时被称为蕃禺。由于位处珠江入海口,南邻大海、北通中原,蕃禺城具有发展海上交通贸易的独特地理区位优势。《史记·货殖列传》中将蕃禺城列为西汉帝国九大都会之一,“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亦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两部官方史书都提到“珠玑”是蕃禺汇聚的重要物品。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发掘了数千座两汉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材质丰富、形状多样、色彩斑斓的珠饰,证实了《史记》与《汉书》的记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从1953年至2016年广州已发掘的1500余座两汉墓葬中,筛选出242座出土珠饰的墓葬,对其出土的21303颗珠饰材料进行全面收集、细致观察,从中挑选了400余件代表性样品,利用现代科技检测技术进行了科学分析,经过系统整理与综合研究,公布了珠饰的出土地点、年代分期、材质、颜色、形状、数量、尺寸、纹饰、穿孔、化学成分、物理结构、工艺特征、图片等信息,大部分属首次披露的第一手资料。
广州两汉墓葬中,出土珠饰的墓葬较为普遍,且数量不菲。从出土情况看,珠饰的拥有者地位较高,处于社会的中上阶层。单座墓葬出土珠饰少则数颗,多则数百至上千颗,不同材质的珠饰常常组合成串,装饰于墓主的头、颈、胸、腰、足部。还有4座墓,以上千颗珠子编缀成珠襦殓葬,极尽奢华。广州出土珠饰之多、品种之丰富、器物之精美,不仅是厚葬之风的体现,还从侧面印证了蕃禺都会的富庶。
从材质上划分,广州汉代珠饰分为人造材料和天然材料两大类。人造材料包括玻璃、费昂斯、陶、金、银等5类,以玻璃珠的数量占绝大多数。天然材料包括红玉髓、绿玉髓、玛瑙、水晶等11类无机质、有机质的宝石与半宝石及动物骨骸。
珠饰的形状多种多样,有圆球形、扁圆形、圆环形、动物形等30余种,体现了不同的工艺特征与制作技术,不同材质的珠子常常具有相同的形状,又反映出制作工艺的共通性。
在制作工艺上,人工材料珠饰需经人工合成或淘炼,再经熔融、冷却等工序制作而成,可塑性强,成型与装饰手法较为多样,模压、缠绕、拉制、上釉、镶嵌、焊接等各种工艺灵活施用,生产出各种形状、颜色的单彩珠以及多彩的蜻蜓眼珠、马赛克珠、条带纹珠等。天然材料珠饰主要通过切割、打磨、钻孔、抛光等冷加工方式制成,只有少量经过后期热加工处理。天然材料珠饰以自身的色泽、纹理与造型取胜,一般不做更多的装饰。仅红玉髓珠中,出现有蚀刻白色条纹的装饰手法,可能是模仿玛瑙珠的条带纹理;玉珠、陶珠中出现刻划、戳印纹饰。
世界各地的珠饰产生于不同的物质条件与精神追求,具有不同的地域特征。《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从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宝玉石珠的矿物产区与制作传统、珠饰的器型风格等方面对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的来源进行探讨。
经检测分析,广州汉代玻璃珠包含铅钡玻璃、铅玻璃、钾玻璃等七种成分体系。铅钡玻璃与铅玻璃学术界公认为我国自制,广州出土的这两类玻璃珠可能从湖南或中原传入,也有可能在广州本地制造;钾玻璃包含低铝高钙、中等钙铝、低钙高铝3种类型,以中等钙铝型钾玻璃数量最多,低钙高铝型钾玻璃数量亦不少,这两种类型的钾玻璃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期,东汉时大量增多,其部分源自南亚或东南亚,部分为交州自制;低铝高钙型钾玻璃仅发现1颗,其化学成分、器型与战国时期楚地常见的钾钙玻璃相似,推测产自湖北江陵地区;植物灰型钠铝玻璃、矿物碱型钠铝玻璃则可能来自于南亚地区;植物灰型钠钙玻璃和费昂斯可能来自于西亚,泡碱型钠钙玻璃则主要来自地中海沿岸地区;混合碱玻璃与钾铅玻璃为技术吸收与发展的产品,多产地的可能性较大。
从器型风格来看,广州部分汉代珠饰为域外输入,如蚀花珠、系领珠、狮形珠、马赛克玻璃珠、装金或银玻璃珠、条纹玻璃珠、沟槽珠、多面焊珠镂空金花球等,部分为岭南地区工匠利用外来的原料进行我国传统器型的加工制作,如琥珀胜形饰、红玉髓、琥珀耳珰等。还有一些珠饰,为岭南当地工匠利用本地的原料对外来器型进行仿制,如铅钡玻璃体系的蜻蜓眼玻璃珠、多面体玻璃珠等。
研究表明广州汉代珠饰蕴含中国岭南、内陆和异域等多文化因素。西汉前期珠饰的数量不多,集中出现在南越王墓和少数贵族墓葬中,以国产铅钡玻璃珠、玉珠为主,表明广州地区与岭北、中原地区联系较为密切。西汉中期以后,不同成分体系的玻璃珠与来自南亚、东南亚的宝玉石质珠在广州大量出现,不同器型风格的珠饰共存,表明岭南地区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密切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甚至与更远的西亚、地中海地区也存在一定的贸易关系。自西汉晚期开始,岭南当地的工匠也可能利用本地材料仿制具有外来风格的珠饰。
或直接从域外输入,或进口原材料加工,或对异域风格器物进行仿制,均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科技文化相互交流、影响与融合的过程,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甚至是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实物见证。不同来源的珠饰荟萃,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与发展兴旺存在密切关系,是蕃禺作为汉王朝对外交往都会的确凿证据,实证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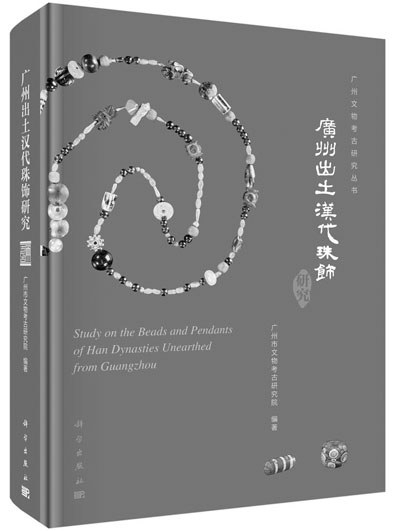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