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典籍与文献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文化交流的主体之一,长期以来陆陆续续东传,不断滋养着日本文化。
进入晚清,日本学者为研究中国,在财团的资助下,一拨接一拨来华学术访问、考察,而访书是行程中的重要内容。钱婉约教授辑录翻译的《中国访书记》一书中的文章就真实再现了部分当年情况。书中文章作者有内藤湖南、岛田翰、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吉川幸次郎,主要是汉学家。文章选自他们的调查报告、游记、日记、回忆录,信息量非常丰富。
本文谈谈书中的几位日本学人,以其在华活动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学术考察
内藤湖南先后十余次访华,与我国学者交往也颇多。早在1905年,他去沈阳的黄寺、故宫等机构,见到满蒙文《大藏经》《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以及文溯阁《四库全书》等珍贵典籍,并拍照复制了蒙文《蒙古源流》《汉文旧档》。1906年他又去了一趟沈阳,通过行贿拍摄了满文《蒙古源流》《西域同文志》《旧清语》《满文长白山图》《盛京全图》等。1910年,他与狩野直喜等几位学者受京都大学派遣,到北京调查伯希和发现的敦煌文献以及清朝内阁大库档案。1912年他与京都大学的羽田亨等再到沈阳,故技重施,进入旧宫,他们花了一个月时间,将《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拍摄复制完成,雇人抄写了《四库全书》中的几种珍本,还查看了翔凤阁的古书画。这些资料的获得,为日本汉学界奠定了研究基础,使日本走在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前列。也许是因为收获多多,内藤说:“没有比奉天(沈阳)再好的地方。”
学术考察与研究之外,内藤本人也喜欢藏书,家有包括宋元版在内的古籍善本三万册。最得意的珍宝之一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他有专文记述得书过程。《说文解字》有刊刻之后,写本在流传过程中大多已经散佚了,只有“木部”幸存。该残本于1861年由学者莫友芝发现,后被端方收藏,内藤见到真本,从此梦寐难忘。端方亡后该书落入其亲戚手中,其人故后再度易手。内藤一直追踪此书动向,几经周折,终于在关注了十七年后到手。他的兴奋与得意,在文章中毫不掩饰。这样一部国宝级文物,辗转流传,最后到了日本。内藤湖南的详细记述,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非常有价值。
内藤湖南对于我国的藏书文化非常推崇,在介绍藏书家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嗜好散尽财产,尽全力收集书籍、作藏书志,又翻刻善本,与其说是为了使自己的藏书以贻后世,不如说是由于藏书家内心夙愿的驱动。这种不可思议的嗜好,是近代中国发达之处。”这番话,似也可看作夫子自道。
武内义雄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曾在北京留学,在华北与江南寻访文化遗址。读了清代学者的著作,他循着蛛丝马迹去访碑。在易州访到唐刻道教经幢与佛教石碑,在焦山访到唐刻道德经幢,不畏荒山野岭,悠然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他将访到的碑文与传世文献对勘,细细推敲更准确、更接近初始的版本。他又到房山考察,踏访古老的云居寺、雷音寺藏经洞等。他对学问的投入与痴迷,令人动容。 二三十年后(1956-1958),雷音洞里的藏经洞与云居寺的地宫出土上万块石经,震惊了世人,以至于被誉为“小敦煌”。如果武内义雄有机会再来,不知会怎样激动。
神田喜一郎是历史学家,出于内藤湖南门下。他多次来华考察、访书,还见到了藏书大家傅增湘与张元济,不仅观书,还得以切磋学问,留下难忘的印象。他还有幸在王国维的陪同下,几次参观蒋汝藻的密韵楼,饱览藏书,看了大量宋元刻本,他发自肺腑地告白:“真是感激之至,深慰渴慕。”
二、图书交易
田中庆太郎是日本著名的书商,一度经营着东京甚至是全日本最大的汉籍书店。敦煌文献发现后,他在第一时间著文,将消息传入日本。他的贩书经历,前后跨越了两个时期:清末与民国。清末时他经营古书,为方便收购古籍,曾在北京置业居住多年,将书运回日本出售,以供日本汉学家学习与研究之需。田中经眼与经手的古书与碑帖非常多,练就了高超的鉴别力,与岛田翰、内藤湖南一道,成为最懂中国古籍的几位日本人。进入民国后,中国社会发生变革,学术与文化亦随之巨变。新学兴起,古籍逐渐退出市场,他转而买卖新式图书与刊物,大量从出版重镇上海进货。田中的书店,大量输入汉籍,对日本的汉学与中国学研究,有重要的辅助之功。
说到近代中国古籍流入日本,有一大宗不得不提,即皕宋楼藏书被岩崎家族三菱财团收购。岛田翰出生汉学世家,有神童、天才之誉,精通古籍版本,他用汉语写的《古文旧书考》,在中国知识界享有很高声誉,经学大师俞樾也称赞他为“真读书人”。岛田自称,他1905年末在中国访书时几次登上皕宋楼,对这批藏书的价值以及来源与传承线索了如指掌,就怂恿陆心源后人出售给日本。次年初他回国与田中庆太郎、重野安绎商量,物色到合适的买家岩崎弥之助。另一说,是岩崎氏决定收购皕宋楼后,才委托岛田翰去核查、确认这批藏书的价值,并提交报告《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无论哪种说法,在这一交易中,岛田翰都充当了重要角色。双方讨价还价,最终以十万元的低价成交,皕宋楼藏书遂成为静嘉堂文库的重要收藏。此事,固然令国人伤怀,乃至气愤。但是换个角度看,这批书得到了很好保护,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幸。如今,静嘉堂已将宋元版古籍全部数字化,将高清文件放到网上共享。这又何尝不是当代人之福!
长泽规矩也是近代日本文献学第一人,年轻时多次受托来华采购图书。当他1930年代初再次来北京时,国内最大的古籍市场琉璃厂已经衰落了,不复孙殿起在《琉璃厂小记》中所记的盛况。他以前到过的生意不错的书店,也已日渐凋敝,书架上没有什么书,甚至有些店已停业或倒闭,变化之大,令他唏嘘不已。他随后到访了其他城市,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的书肆也是一片萧条,今非昔比。他用近似素描的笔触,为民国时期的书业留下了照相般的记录。这样详实的资料,在国内几乎是看不到的。借助这些记录,可以局部还原民国时期图书业的真实面貌,进而了解近代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日本自隋唐开始学习中国,尽管在近代明治维新时调转船头学西方,然而一些深受汉学传统熏染的学人,仍然把中国当成文化母体,怀有温情和敬意。我国历经战乱与灾难,很多古书已经在国内失传了,却在日本得以保存,后来辑刻成《佚存丛书》《古逸丛书》等,又传回我国,这是应该感谢邻邦的。中国的文献与文物流传到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反过来,日本文化又影响中国文化,尤其是近代以降。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只有持开放的心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发展和进步。
三、求学访问
日本的汉学家,大多有过在中国求学或访问的经历,从盐谷温到铃木虎雄、羽田亨、和田清、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吉川幸次郎。1923年他初次来华,在江南游历时,去看西湖雷峰塔,到文澜阁访《四库全书》。他为苏杭的富庶陶醉,饱含深情地说:“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1928—1931年,吉川在北京留学,过着中国化的生活,甚至说话都带京腔。他去南方买书,穿长衫戴小帽,当地人都把他当成京城的商人。他去高邮寻访二王故里,还有机会当面向黄侃请益。
吉川在北京上学期间,最喜欢逛书店,甚至与书店老板成为朋友。他说:“这期间的记忆,值得反复回味的美好印象,不在剧场和戏院,不在饭馆和餐厅,而在古书街市。”他深深地认同中国文化,甚至把中国当成他的祖国,回到日本后依然穿长衫,以至于被京大教授桑原隲藏误认为中国的留学生。在大学课堂授课,口口声声称中国为“我国”,称日本为“贵国”。尽管没有变更国籍,但在文化与心理上,他已经成了中国人。正是有如此深情,如此理解,他才开创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日本对中国文化与典籍的崇尚与渴慕,事实上延续了一千多年。《中国访书记》中的访书故实,只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吉光片羽。从这些断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
观察中国文化有多个角度。如果说,西方人看中国,似难免有些云里雾里的隔膜,有时流于隔靴搔痒;日本人看中国,由于切近而更加理解,也更加深刻。我们或可借助这面镜子,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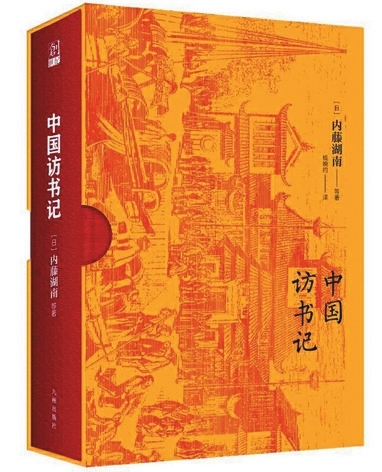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