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旧注辑存》是一份标目相当谦虚内敛的重大科研成果,如果只是狭隘地顾名思义,以为这不过是一部常见的汇编抄撮之书,那就非常外行、离开实际甚远了。
跃进先生在卷首的《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一文中说,他花多年时间做这件工作,“只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文选》提供经过整理的资料”,自己加了种种按语,“目的是为将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线索”(《文选旧注辑存》第1册,卷首第21页)。而事实上,此书乃是“《文选》学”史上继往开来具有总结性的大书,实为古代文学特别是中古一段之从业者案头必备的要籍。
《文选》成书甚早,又曾经与科举考试有关,所以传播甚广,版本非常复杂:有白文本,有带注本;不同的注本不仅注文各异,而其原文也不尽相同,分卷的办法亦复各行其是。《文选》的注本有单独的李善注、单独的五臣注、合编的六家注(先五臣后李善)、六臣注(先李善后五臣);有内容更复杂多样的《文选集注》,又有注者不详的各种手写本。各本之间的关系纷纭纠葛,理董不易,其来龙去脉异同优劣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弄清楚。麻烦还在于其中比较重要的本子散见于国内外各处,有些是不容易见到的,要想看全了尤为困难。
要之,《文选》的旧注意义重大,内容丰富,令人头疼之处在于线索纷乱难明,而且难以读全。可是离开了对于资料的全面掌握,深入的研究便无从谈起。
令人兴奋的是刘跃进的《文选旧注辑存》一书一举帮助读者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该书卷首的《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一文中写道:
解读《文选》,唯一的途径是研读原文,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各家的注释又是不二的选择。从广义上说,所谓“文选学”,主要是《文选》注释学。通常来说,阅读《文选》,大都从李善注开始,因为李善注《文选》,是一次集校集释工作。他汇总了此前有关《文选》研究的成果,择善而从,又补充的大量的资料,因枝振叶,沿波讨源,成为当时的名著。宋代盛行的六臣注《文选》,其实也是一种集成的尝试,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刊,去粗取精,便于阅读。除六臣之外,还有一些古注。清代以来的学者更加系统地整理校订,希望能够对于《文选》文本及其历代注释作系统的集校辑释工作。但总的来看,还留下这样或那样的遗憾。最主要的原因是,《文选》的版本比较复杂,有三十卷本,有六十卷本,还有一百二十卷本,同样是李善注或五臣注本,各本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常常叫人感到无所适从。这就使得集校集注工作充满挑战。还有,新的资料不断出现,尤其是敦煌本和古钞本的面世,不断给《文选》学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长期以来,我在研读《文选》及其各家注的过程中,遇到某一问题,常常要前后披寻,比勘众本,总是感觉到挂一漏万,缺少一种具体而微的整体观照。于是,我很希望能有这样一个辑录旧注排比得宜的读本,一编在手,重要的版本异同可以一目了然,重要的学术见解亦尽收眼底……(第1册卷首第7-8页)
于是,他就亲自动手,来做这种于己于人都非常有用的旧注辑存的工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文选旧注辑存》取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为底本,李善注一般也首先采用此本(如有敦煌本、北宋本则先行列出),而五臣注则以绍兴三十一年(1161)陈八郎本为主要依据,其余各种旧注完全按时间先后排列(例如李善引用的早期注释即列于最前)。元元本本,整整齐齐,一编在手,所有的传世《文选》旧注皆在眼前,读者可以节省许多披寻翻检的时间和精力。
此外,本书还进而博采史书、文集、碑帖中有关《文选》入选作品的材料,加以比勘核校,提供了许多信息,颇有助于人们扩大视野,从而更深入地审视有关学术问题。
《文选旧注辑存》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更在于刘跃进先生不仅逐一辑录了《文选》的全部旧注,而且在仔细研究了《文选》各篇及其注释以后,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写下了大量的精彩按语,形成了一部以传统学术方式呈现的刘氏文选学。
这里有相当长的按语,如卷十九曹植《洛神赋》题下,尤本李善注有引用“《记》曰”的一大段故事,把甄后与曹植的关系引入,说此赋原题《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云。著名的辞赋背后还有这样一段绯闻八卦,古今读者自然大感兴趣。但是胡刻本附录的《文选考异》指出,这一段所谓李善注乃是尤袤误取小说,李善注中原来没有的。查北宋本、奎章阁本也确实没有这样一条李善注。此事后来聚讼纷纭,至今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为此跃进先生写了超过两页的长篇按语(第6册,第3659-3661页),展开深入的讨论,予人有益的启发。
当然,大部分按语没有这么长。除了涉及文献问题者外,也有关于文艺方面之评说的。跃进此书关注的重点固然在文献,而他并不以此自限。例如《文选》卷十八潘岳《笙赋》,在引用过北宋本、尤刻本李善注之后,“跃进按”写道:
奎章阁本李善注与北宋本同。《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嵇(康)之《琴》,潘(岳)之《笙》,二赋发端便是文章,各各排突前人之法。”(第6册,第3659-3661页)
后半引用何焯的意见,评说《琴赋》与《笙赋》的章法,就是讲艺术方面的问题。
将《文选》一书的种种旧注加以汇总并且合理地编排起来,为今后的研究大开方便之门,乃是一件非常复杂繁难的事情,再就其中纠葛纷纭的种种文献问题以及某些艺术问题加以分疏辨析,提出按断,更是十分艰巨的工作。全书平实而求新,谢绝一切花腔,适足以为“《文选》学”的深入发展提供具体的指引。
要做成这样一部“广大教化主”式的大书,至少需要三大条件:一是要能获得资金方面足够的支持(此书列入了三个大项目:2011-2020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是要有一支年轻的精力弥满能做实事的团队(本书后记中列举了一批青年才俊的名单,其中颇有我认识的可畏的后生,相信从这里一定能涌现出未来的学术名家);三是要有一位统领全局的帅才。刘跃进团队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经过八年奋斗,终于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实在可庆可贺。
像《文选旧注辑存》这样高屋建瓴、脚踏实地的好书,现在并不太多见。通过大型项目来奖掖学术后进,培养青年才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跃进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做了很好的工作,这种贡献具有超越具体项目的深远影响。对这样充满热情来组织队伍、身先士卒、带队冲锋的学者,应当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这样一部二十大本、超过一千万字的巨著里,有若干尚可讨论之处自然是难免的,也不足为病,请略述两条商榷意见,一宏观,一微观,聊供认真研读此书的青年同道参考,并望得到跃进先生、徐华女士和大家的指正。
其一,本书对旧注博采旁收,一一予以著录,工作做得相当细致深入,而且优先安排在前面;而对《文选》各篇正文文本校勘的意见,则大抵安排在其后最末的位置。这样的顺序,读起来似乎有点别扭不安。注释是跟着正文来的,正文不同,注释自异。所以关于正文的校勘意见,安排在最前面才好。
试举一个文字甚少、头绪简单的例子以明之。卷四十四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有下列一小段:
夫见机而作,不处凶危,上圣之明也。
【李善注】 尤袤本 《周易》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
【五臣注】 陈八郎本 向曰:几者,事之微。言见事微者,不处凶危之地。
【跃进案】 机,九条本、室町本、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奎章阁本作“几”。奎章阁本注记:善本从木。(第14册,第8709页)
这里最好把【跃进案】安排到【李善注】的前面去,读起来比较顺当。也可以径称【校记】。如果关于正文文字校勘的按语内容比较复杂,则更以安排在最前面为适合。先谈皮,后说毛,而不是倒过来。至于关于注释文字的校勘记,则自然应安排在最后(在上述例子中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既有关于正文的校勘,又有关于注释的校勘,则宜乎分别写出校记和按语,放在所录注释的一前一后。著者关于此段文字的议论,也放在最后的按语里。
这样来排列当然要麻烦一点,但头绪清爽,利大于弊。这个建议涉及全书的编排,不知是否有当,请予考虑。
其二,《文选旧注辑存》书末附录二“参校本提要”之五“其他散见参校本”中第十二项“新疆伊犁《燕然山铭》石刻”条下写道:
新疆伊犁燕然山铭石刻,残,隶书。高二百二十厘米,宽一百二十三厘米。或谓东汉永元元年(89)七月原刻,或谓翻刻者。其拓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时收录该篇。参校时简称“刻石”。(第19册第12061页)
今按新疆伊犁与燕然山(在今蒙古国境内)相去遥远,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当年北伐匈奴为纪功而勒石之地绝无在新疆伊犁的道理。这一石刻绝不可能是所谓原刻,恐怕连翻刻也谈不上——这份石刻拓片完全是做碑刻生意之奸商伪造出来的假古董。这样的文本显然没有条件作为校勘《文选》旧注的参校本。建议将此条删去,同时将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按语中两处提及此一石刻的文字也一并予以删除。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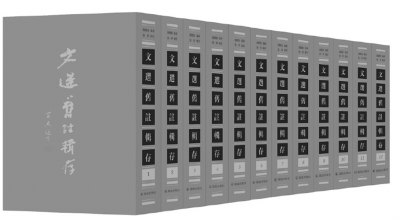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