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见鬼》说起
“海上说鬼人”有鬼君出了一本奇书——《见鬼: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阅读笔记》。这本书打捞了散布在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里各色各样的鬼,把鬼的文献材料视为民族志,用流畅的叙事书写了鬼的日常、鬼的社会、鬼的政治,以及人鬼关系。举凡吃素、约架、全球化、投胎、猪肉自由等时髦话题,均能一一发掘出鬼的视角和故事,而鬼也颇有令人眼前一亮的看法和举动,令人不得不感叹古代志怪的丰富,当然还有鬼君的联想力、叙事才华以及敏锐的现实关怀。
读此书,若能抱持欣赏与玩味的态度,想必是能体会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的话——“能在有鬼的世界中生活是幸福的”。《见鬼》带我们见识了一个以鬼为主、人鬼共存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寻常理解的鬼,已不再是恐惧的代名词,也不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行者,而是一种奇异的存在,它们散发浓厚的烟火气息,透露出活色生香的趣味,令人不得不赞叹:“真是鬼灵精怪!”而重新书写它们的作者,莫非也已到了“鬼才”的境界?若就书中故事而言,直接捧读即能体会趣味。但对于“不接地气”的学者而言,我还想就其中涉及的文化问题做些发微和初探,抛砖引玉,以引起更多学理的争鸣。毕竟,根据《搜神记》,就连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也曾智斗妖怪哩,知识分子岂能不效法先贤。
可惜的是,西方自古有“神学”,日本近世有“妖怪学”,民国始有“仙学”,而鬼却没有相应的“鬼学”——什么是鬼?鬼是如何诞生的?鬼的世界有什么样的运作机制?只有回应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才不至于面对鬼而“疑神疑鬼”,也不怕别人“装神弄鬼”,方能与鬼和好,更整全地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文化系统。
“鬼”的生成
诚如有鬼君所说,幽冥世界是一种累层构建的产物,并非静止不动,它的背后是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既有一些共通的基本规则,也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其实,这接近哈佛大学宗教学家怀菲尔德·史密斯(WilfredC.Smith)的看法,他也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各类“宗教”,无不由“虔信”(Faith)和“积累传统”(CumulativeTradition)所构成,二者缺一不可,互动交织出形形色色的“宗教”。当然,那些佛经、道经里书写的过度繁密又经后世润色的幽冥世界,其实也是一种经千年累积的现象,反映出某种集体实践和“制度化”,并非“虚构”“想象”或“刻意”所能一言蔽之。史密斯就认为传统的宗教学通常会研究某部经典里的教义思想,而他则更注重用千年的尺度,衡量这部经典的作用和角色。这就需要通过跨文化、跨时间、跨文本的比较,来重新建构一个更广阔的的人文世界。
同样,这些学理对“鬼”也是适用的。我对“鬼”的兴趣,更在于想要了解“鬼”这种文化,在长时间尺度里的生成理路,以及它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
“鬼”作为一种文化,并非一次性诞生,而是人类信念和社会实践互相交织、累积生成的产物。从汉字的角度看,“鬼”这个字很古老,甲骨文里的“鬼”字取了人形,不过异于正常的人形,更像是巫师戴着面具装扮成鬼怪的模样。在汉语词汇里,“鬼”的造词很丰富,不下千种,涵盖了正负两极的涵义。比如,说一个人作恶多端、危害他人,那便不能归为人类,而要归为鬼类,举凡“鬼鬼祟祟”“鬼迷心窍”“各怀鬼胎”,无不以鬼贬人。若从正面看,则“鬼斧神工”“机灵鬼”“诗鬼”“惊天地、泣鬼神”,又透露出些许敬爱乃至敬畏。这种现象,除了汉语的博大精深以外,常常也能反映出“鬼”在中国文化里的深厚影响。
的确,“鬼”的涵义多元,内涵与外延交织,早已超越了语言文字,在更基础的社会文化生活里扮演关键角色。《礼记》《论语》郑重教导子孙要祭祀的“鬼”,属于祖先崇拜中的“家鬼”,也是古代中华文化的核心命脉之一。而没有得享后代祭祀的则变为“孤魂野鬼”,有时会扰乱人间生活。当人们遇到无法解释也无以应对的自然事件时,在地震、瘟疫、火灾中惊惧万分时,也会把这些解释为鬼怪作祟。进而,一些宗教节期和仪式,也在应对“鬼”的过程中而日臻完善,比如佛教的盂兰盆节、道教的施食科仪,无不为着救赎这些饿鬼、冤鬼、孤魂野鬼。虽然从“家鬼”到“野鬼”,这些都被称为“鬼”,但他们的文化阶层、道德地位、仪式待遇往往有天壤之别。
“鬼”的学术和文学
不仅宗教和民俗谈鬼,学者和文人也时而谈鬼。一些汉学家、人类学家已有不少对汉人地区“鬼文化”的研究,例如美国汉学家柏华(C.FredBlake)的《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人类学家焦大卫(DavidK.Jordan)的《神·鬼·祖先》,以及林美容的《台湾鬼仔古》等等。近些年来,栾保群的《扪虱谈鬼录》、有鬼君的《见鬼》则是探讨这些问题较多的书。
中国人不仅纸上谈鬼,而且在生活里处处能听到鬼故事,只要你敢提起胆子去打听。《见鬼》涉及的素材,主要源自中国古代志怪小说文献。在历史里,从干宝的《搜神记》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些志怪故事的形成与文本的书写,是“鬼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但这些也并非全部。此外,还有物质、实践、口传、节期等等,均构成“鬼文化”动态演变的内涵。而就物质而言,许多人类学家着墨的“烧纸钱”这种行为和习俗,便对于沟通阴阳、塑造心理起到重要作用。
除了学术研究,中文作家对鬼的严肃文学创作也不是没有。哪怕到了现代,从鲁迅《失掉的好地狱》到钱锺书的《夜访魔鬼》,鬼也依然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当然,这些鬼已经不再有令人恐惧的心理因素,更多的是文学趣味和审美导向。当然,写鬼的文学虽未曾断绝,但也不复见魏晋时期志怪文学的高峰了。
从这些角度来看,“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生成遍及多种文化载体,分布在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鬼”已是人们生活和观念的一部分,也早已确立了它们的文化角色。谈论“鬼”不仅不是“旁门左道”,而且还能从中窥见诸多文化的秘密。
“鬼”消失了吗
扩而言之,“鬼文化”不仅在中国有广泛影响,是亚洲文化的共同特点之一。如果说欧美民族的文化主流是崇拜“神”的文化,那么亚洲文化便是一种敬畏“鬼”的文化。不论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新教,还是伊斯兰教、拜火教,生活于这些文明中的人,往往对“神”的细节了若指掌,他们用大量文本、口传技艺和仪式来描绘、传承“神”的故事,它们中的诸多教派甚至非常忌讳谈鬼,也缺少有关鬼的细节和趣味,更不用说演变出有关鬼的多元文本和祭祀仪式。
相反,在亚洲,不论日本、韩国、中国还是东南亚国家,普遍共享着一种对“鬼”的敬重,其中既包括对祖先的崇奉,也包括对其他各类鬼魂的敬畏。这种现象不仅古已有之,而且于今尤甚,如果看看日本、韩国和泰国的“鬼片”票房,则可以说“鬼文化”是塑造亚洲文化的关键词之一。
其实,在1945年出版的《初访美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区别。不过,他说的是美国人崇拜“超人”,而中国人敬畏“鬼”。即便像费孝通这样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认为童年时对鬼怪和未知世界的敬畏,深远地影响了他的世界观——“我自己早年对于大厨房、后花园的渺茫之感,对于纱窗间的恐惧之感,一直到现在没有消灭,不过是扩大了一些,成为我对宇宙对世界的看法罢了。”
进而,他把童年的恐惧、祖母的影子、房屋的角落,上升到了更高、更悠远广阔的哲学思考——“我们的生命并不只是在时间里穿行,过一刻、丢一刻;过一站、失一站。生命在创造中改变了时间的绝对性:它把过去变成现在,不,是在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成为一串不灭的,层层推出的情景——三度一体,这就是鬼,就是我不但不怕,而且开始渴求的对象。”
他意识到了“鬼”在中国人心理和日常生活中的独特存在,也点出了美国文化中“鬼的消失”。他认为美国人高度流动的都市生活、独立居住的小家庭、联系不密切的血缘关系、千篇一律的住宅形态,让人与人、人与物的联系变淡了,对故人的幽思、对亡物的怀念,也都变淡了。因而,鬼也随之而灭。
当然,费孝通没有看到当代中国已经发生的大流动,那个深宅浓荫、后花园充满传说、一草一木皆有神话、邻里巷陌不缺故事的古老中国,也一样逐渐去魅、消失了。然而,“鬼”真的消失了吗?还是改变了文化形态,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
现代社会的高速流动、个体隐私、人际壁垒,让传统形态的鬼减少乃至消失了,但是现代化的精致的鬼却越来越多。那是香港都市爱情电影中的鬼,是日本电影里的怨鬼,它们多数是独居在公寓里、有各类心理疾病的男女老少,因为家庭、事业、爱情这三座大山而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由人变鬼,演绎起当代都市的幽冥志怪。可以说,从古至今,鬼从未缺席。
幽冥故事不仅仅是对人间生活的反映和投射,它对人们的寻常生活、老百姓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常常有“润物细无声”的深刻影响。在口耳相传中,在好奇和恐惧的情绪之间,它仿佛跨越了代际和地域,告诉一代代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它在人类文化里发挥着深层却又少人留意的巨大影响,需要引起更深的注意。
“见鬼”以后如何
娜拉的出走,让鲁迅追问:“娜拉走后怎样?”而鬼却从未消失,只不过改头换面、如影随形,游荡在人间。前者是一个女性解放的难题,后者却是人们从传统走进现代的难题——“鬼”只是引子,引发人对自身、对传统和现代的思考。启蒙,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终极目标,启蒙从来就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反思过程。
自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科学”和“民主”成了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中心思想,举凡学术研究、政治、经济,皆奉“赛先生”和“德先生”为圭臬。而对于不合于二者的其他社会文化元素,或以“反动”批判,或以“迷信”拒斥,或以“不可知论”漠视,或以“神秘莫测”讳言。总之,百年来的学人学者和社会各界,对“鬼文化”的研究和书写,恐怕是远远不足的。
相较而言,日本学界对“鬼文化”的研究,已有相当客观而且可观的积累,他们对自身传统文化里的鬼魅元素,也有相当早的整理和重新创造。从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到鸟山石燕的浮世绘,从井上圆了到柳田国男,无不展现出他们对日本“鬼文化”的探索。近世日本学人在习得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后,创造性地运用于整理、研究有关鬼魅的文献材料和民俗现象,终成一门特殊的学问——妖怪学。
当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老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翻译了日本妖怪学之父、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后,竟然从中得到启发,抛开了科学与迷信、唯物与唯心、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开始觉得“心境之圆妙活泼,触发自然,不复作人世役役之想”。从前他认为“无稽之谈”的妖怪,在宗教学和人类学的显微镜下,竟然迸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这是一次重新展开的启蒙过程,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见鬼”的经历——“见鬼”是一次震慑,一次提醒,一次让人超脱寻常观念的体验。那么,如果用一双“鬼眼”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亚洲文化乃至西方文化,可能看到的将比以往的更多、更不同。
在此,请允许我以热烈掌声,欢迎“鬼”的到来,不是以魅惑的姿态,而是以反思的、启蒙的、批判的姿态,欢迎“鬼”重归这个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世界。如果人们可以直面鬼提出来的疑难和诘问,或许可以从这个人类永远的“反对派”身上,比从人间事务里学到的多得多。
我与有鬼君素昧平生,也未曾见过鬼,但毕竟写过鬼,还认得书里的鬼,所以不揣冒昧,姑且任笔品评群鬼,有不当处,也请有鬼君和鬼们见谅。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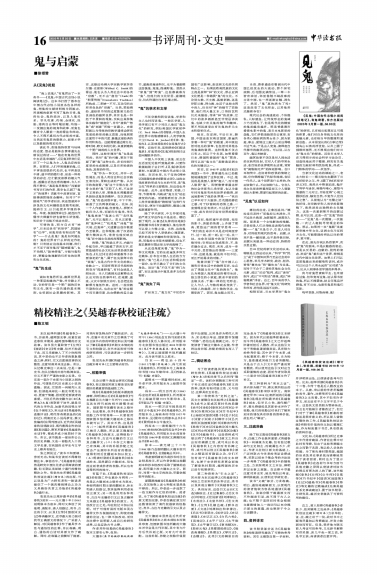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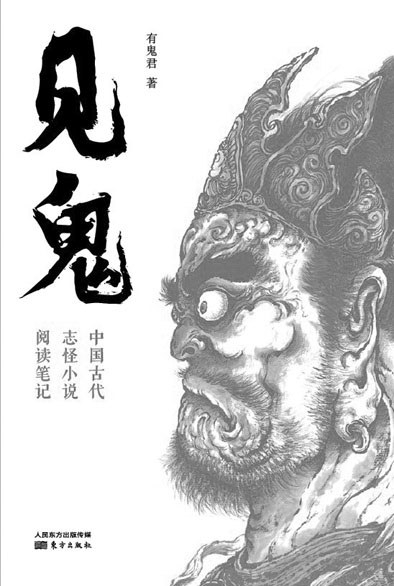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