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轻便型的文体,诗歌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如何赋予芜杂的经验以形式的张力,不仅要求着诗人的真诚,也考验着诗人的技艺。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倾向于哪一方,形成或者“纯诗”、或者“介入”的立场,而是持守一种内在的平衡,既不能在宏阔的经验、题材面前失却了文学的主体性,也不能仅仅将历史转化为语言的风景。在这一点上,查尔斯·西密克,展示了诗人直面历史时的赋形能力。
西密克出生并成长于纳粹阴影中的贝尔格莱德,在经历战乱和目睹种种恐惧之后,移民美国,并再次领受了底层生活的诸多艰辛。正是这样一段成长过程,使得西密克在诗中对战争、政治、创伤记忆和底层经验等等进行了持续的、近于偏执性的书写,无边的苦难景象“魇”住了诗人,而诗歌则是在噩梦中挣扎、保持清醒的唯一抵抗方式。也由于苦难记忆的笼罩性影响,在西密克这里,历史成为诗人必须被动承受的、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历史正犹如“一个拾破烂的老人”,将种种战争与政治的残留物扔进诗人的“麻袋”:
但我什么也没说,一个快要撑破肚皮的/麻袋又能说什么?——《旅行》
或者,历史干脆就是一锅乱炖的“汤”,是诗人必须领受的“圣餐”:
我们会戴上帽子/坐下来咕嘟咕嘟喝:/一种低语的森林般的汤,/一种刺激胃口的屠宰场的汤。——《汤》
无论是“麻袋”,还是“汤”的隐喻,都暗示了西密克诗歌的生成装置:直面历史、接受馈赠。而“直面”和“接受”本身就是一种认知历史的方式,既包含着诗人的历史意识,也内在构成了诗歌的技法。正如“旅行”就是对历史风景的汲取,“喝汤”就是对苦难滋味的品咂,当历史记忆成批量地涌进诗歌的麻袋和诗人的口中,某种新的秩序也在西密克的诗作中被重新确认。
西密克倾心于爵士乐和布鲁斯,认同它们“‘用短短几行承载一部复杂的人类戏剧’的绝技”。而高度凝练简洁的叙事技巧也构成了西密克诗作的张力:
暗地里历史操练它的/剪刀,/结果万物登场,/全都缺了胳臂少了腿。
如果那就是今天你能/玩一玩的仅有的东西……/这玩偶至少有个脑袋,/嘴唇通红!
木板房排列在空荡荡的街上/像恐怖的展览/一个小姑娘坐在台阶上/穿着绣花睡衣,对它说话。/它像个庄重的东西,/连雨水也想听听它说什么,/于是落在她睫毛上,/让它们闪光。——《吓人的玩偶》
历史现场的残酷性在轻与重的辩证演绎中被描述出来。在诗中,“历史”既是一个坏脾气的孩子,又在任性的杀伐中显出它庞然大物的一面,而芸芸众生不过是被任意剪掉的“玩偶”,诗人就如同那个“小姑娘”只能无力地以“说话/诗歌”的方式面对。固然,诗人承载“人类戏剧”的功力体现在上述诸种比喻与关系对照等戏剧化的方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密克诗作真正的张力点似乎在“轻”的那一面,正如《吓人的玩偶》一诗的最后一节,以无声的雨水和哭泣衬托出隆重的画面感,赋予牺牲者和历史场景以特殊的退场仪式。在其中,恐怖与温情交织,颤抖与镇定相融,像那个心无挂碍,即将走向死亡的在“夜间刮脸”的男人:
不管怎样,还没发生,眼下/还有上唇,还有战栗的下巴,长着/亚当那样大喉结的喉咙/可以细心大量。——《夜间刮脸》
正如日常化的“刮脸”所暗含的恐怖一样,西密克处理历史的震惊体验和创伤记忆时,真正的张力被内在化与细节化,有声的“屠宰场”转为无声的画面:
不知不觉,恐惧从一个人跑到/另一个人那里,/当一片叶子将它的战栗/传给另一片。
刹那间整棵树战栗,/而风杳无痕迹。——《恐惧》
西密克有一首诗,题为“拆寂静”,而诗人在处理历史时,并非是将历史拆得七零八落、呻吟不断,而是如《恐惧》一样,重新组接历史的寂静,这一组接过程尽管有超现实主义式的并置,但更重要的,却是一股内在的、像风一般杳无痕迹的力,并通过它,传递着历史给予的战栗。
西密克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也被认为是“新超现实主义”的一员主将。证之于他的诗作,可以看到,一方面,种种肮脏、荒诞、圣洁与高雅的意象和场景压缩在一首诗之内,形成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另一方面,在并置、聚合之外,西密克往往采取寓言化的方式,从日常生活用品中转喻出无所不在的历史暴力,赋予“餐叉”“汤匙”“小刀”等小物件以内在的历史深度。不过,与其说,西密克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点燃了历史的晦暗之处,不如说,历史本身就是超现实的。因此,在“卡戎的宇宙观”也变得混乱颠倒,人间与地狱互换方位之时,成为诗人的最好方式,就是“进入一块石头”:
当两石相击,/我看见火星飞迸,/所以也可能石头里面根本不是一团漆黑;/也可能一轮月亮在某处/照耀,仿佛藏在山背后——/那光亮刚好可以让你/辨认隐秘的墙上/古怪的文字,星星的航海图。——《石头》
“石头”作为诗人的自喻,体现着西密克的抒情姿态——以外冷内热的方式,以“刚好”的光亮照耀历史之墙上的隐秘信息,显得平静,内敛,有温度,并在瞬间的荒诞之中,彰显诗人敏锐的观察力和极佳的文字精准度:
一个很快要被吊死的男人在路上走,/脑袋耷拉,脸色发黑,面孔扭曲,/仿佛死亡意味着用力拉屎。——《行军》
精巧的比喻配合着历史想象力,历史的本来面目也由此呈现为超现实般的悲喜剧。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历史暴力、创伤记忆的不断书写,也使得西密克的诗作在“夜间”显示出“一轮月亮”的光度,正如他描写过的“梦中一只鸟”:“她的鸣叫犹如一根划着的火柴/在昏暗起风的门槛上闪烁”(《鸟》)。
而在上述前提下,按照某些流行的诗学观点,西密克的诗歌创作的确可以归入“见证的诗学”一类,或者以“诗的纠正”的名义为之辩护。然而西密克本人或许会对此持疑,正如他的自述,“查尔斯·西密克是个句子”(《查尔斯·西密克》),而诗人作为一种“词语造成的人”,在西密克那里,却具有相当的限度:“我们只有词语/此外一无所有”(《允诺的怜悯和宽恕》)。诗人以词语的方式见证、介入历史,在一种浪漫主义式的想象中,的确具有创造历史、改变现实的豪情。然而,当诗人的写作脱离了历史与现实中的行动,当诗人只是一个历史的隔岸观火者,尤其是在合理性分化的现代社会,诗人的语言制作行为已经实体化为一种匠人的手艺时,诗歌的介入也只能是一种风格的介入,“写作”本身并不构成“行动”,而毋宁是对行动的悬置,在这一意义上,借用西密克的诗句,历史最多不过是“里边很多拐杖的风景”。西密克曾在早年诗作中“许愿:让一根飞快的针/将这首诗缝成一张毯子”(《一个声音的合唱》),词语的针脚确实可以飞快地缝出历史的挂毯,不过,内在的悖论是,毯子本身既是展演,也是遮蔽,既呈现厚重,也在历史的朔风中显得轻飘,而细密的诗歌针线能否缝出历史阔大的经纬,也是一个值得深思之处。
在时下的诗歌阅读场域中,西密克其人其诗或许也联通着更为广泛的历史记忆。“贝尔格莱德”与“美国桂冠诗人”的并置已经获得了某种超现实意味。西密克的诗作在未被阅读之前或许已经自动打通了某些固化的阅读机制,让西密克顺理成章地进入到某种诗人序列之中。这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西密克的经典化阅读,却也会导致遮蔽诗人的丰富性。也许不妨就以西密克提供的契机为契机,以回到西密克的历史的方式回到我们自身的历史,以反思借鉴西密克的诗学的方法反思我们内在的诗歌方法论,联结现实,打破机制,重新构想新的诗歌可能性。
因此,在诸种现代或后现代风格轮番登场之后,充满喧哗与骚动的诗歌市场如何接受更新的“舶来品”,似乎并不单单是一个翻译与阅读的问题。因为,如果不能从翻译中辨认自身,并在这一辨认中重新认识他者与自我的历史,新的引进或许只不过是新一轮的商品流通,一种无效的、可有可无的诗歌知识的堆积。而这也就意味着,不仅新的诗歌译文必须具有“被辨认”的资格,也必然要求作为接受者的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具备充足的主体性,如此一来,主体与他者才会得以相互生成,新的诗歌乃至历史认知装置才会有效呈现。在这一意义上,查尔斯·西密克,一位“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美国桂冠诗人”,才会在历史的动态关联性中成为我们阅读史的一部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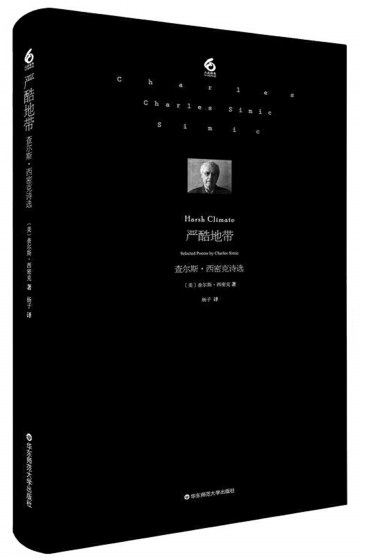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