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先生2004年1月31日逝世于太原,至今已有15年。想起和马烽先生相处的日子,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和马烽先生相识在1975年4月,当时他是山西省文艺工作室的党支部书记,正在为创办一份名叫《汾水》的文学双月刊而做准备工作。我是筹办《汾水》杂志的借调人员,在借调的那段时间,老作家孙谦带我到昔阳县体验生活,把我安排在赵庄大队住了半个多月。回到太原之后,我相继写出报告文学《花儿越开越鲜艳》和短篇小说《评工会上》,先后发表在《汾水》杂志。有一天,在胡同里面碰见马烽,他把我叫住说:“茹志鹃给我来信了,她在信里夸奖了你,说你的《评工会上》写得好。”说这话的时候,马烽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好像比夸奖他本人还高兴。茹志鹃是上海的著名作家,她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我读过不止一次,我很崇拜她。能够得到她的夸奖,我特别高兴。后来《评工会上》被选入《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和马烽茹志鹃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收在一本书里面,马烽又特别把我叫过去说:“趁着年轻,多写些这样的作品。”那种舐犊之情,让我特别感动。
1978年,山西省文联恢复之后,马烽被选举为省文联主席,但他仍然是那副老样子,不许我们叫他马老师,更不许我们叫他马主席,只许我们叫他老马。老马真是一匹好马,他一边主持领导工作,一边奋笔创作。电影《泪痕》《咱们的退伍兵》,小说《结婚现场会》《伍二四十五纪要》等优秀作品相继问世,得到广泛的好评。而我这个后生,则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很长时间没有突破。马烽也为我着急,不断地鼓励我鞭策我,让我向其他的青年作家学习。
有一次,马烽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到太原飞机场去接两位河北作家,一位是《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一位是《代表》的作者张庆田。我当面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却忘得干干净净。那天下午,马烽黑着脸问我:“你接的人呢?”我先是愣住了,接着撒腿就跑,马烽喊了一声:“你给我回来,人家在机场白白等了一个多小时,自己找车过来了。”我垂头丧气站在那里,等待更加严厉的批评。没有想到,马烽放缓了语调:“你是不是有特殊的意外?”那意思我明白,假如我有意外,他会原谅我的。但是我没有意外,我去看电影了,轰动一时的香港电影《三笑》呀!早知道这样,我还能在电影院里面笑起来吗?马烽问我:“老实说,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到处找不到你?”我只好老实交代了去处,心想这下可完蛋了,没有想到,马烽却说:“好吧!看在你诚实的份上,我也就不批评你了。不过你要记住,下不为例。”我频频点头,表示牢牢记住了。
1990年,马烽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那一年我到北京出差,忘带身份证,北京的宾馆招待所没有一家敢让我住宿。眼看天黑了下来,还没有一个睡觉的地方,情急之下就给马烽打了一个电话。马烽说:“没有住处?那就到我这里来吧!”马烽调北京之后,中国作协刚好有了一个新宿舍楼,分配给马烽一套房,马烽没有住,让给了别人,自己仍旧住在鲁迅文学院的招待所。我到了招待所,看见马烽夫妇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根本住不下我。马烽说:“跟招待所打招呼了,你住另外一间。”第二天一早,马烽的妻子段杏绵老师敲门,叫我到他们那里吃早饭。早饭很丰盛,小米粥小笼包子,一盘咸菜还有一盘煎鸡蛋饼。马烽说:“这是沾了你的光,你要是不来,段老师不会给我煎鸡蛋的。”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几乎掉了下来。下午办完事情,回招待所的路上,看见有卖荔枝的,很新鲜,就买了一些给马烽夫妇带回去。段杏绵老师看见荔枝,皱着眉头说:“这样不好吧?”马烽说:“没什么不好,他早饭不也没有给咱们饭钱?”段杏绵笑了,我也笑了。马烽剥着荔枝跟我说:“都说要反腐败,你怎么看?”我说:“腐败的现象肯定有,既然有,那肯定要反。”马烽问我:“当初调你们来作协,我抽过你一支烟没有?”我说没有。“吃过你们一顿饭吗?”我说也没有。马烽说:“这就对了。腐败是有,但你要相信党,相信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时过境迁,想起马烽说过的这些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马烽离休之后,仍旧回到太原市的老房子,他有哮喘病,冬天不能出门。我劝他说,可以到海南去过冬天。他说:“海南我去过,到了那里,我不咳嗽也不气喘。可是那里没有熟人,比在太原更难受。”马烽热爱山西这片土地,热爱南华门东四条(山西省作协驻地)的一草一木。他不愿意离开这里。马烽去世的时候,温家宝总理送了花圈,中国作协送了花圈,国内外的文艺界名人纷纷来函来电,表示沉痛的哀悼。更令人感动的是,马烽的追悼现场,自发赶来许多的普通读者,有工人也有农民,他们像马烽的家属一样痛哭流涕,就像他们自己失去了亲人一样。
马烽先生,您生前不许我们叫您马主席,也不许我们叫您马老师,当我们想念您的时候,就让我们叫您一声马烽先生吧!
马烽先生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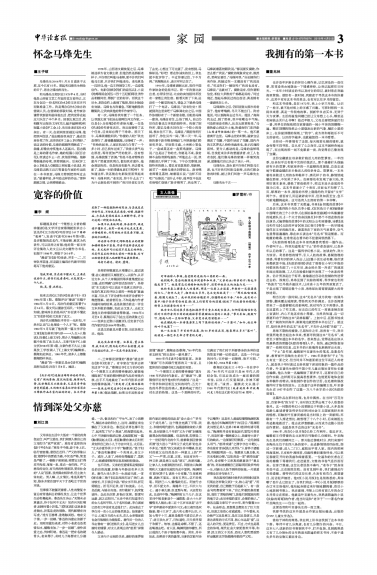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