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家书集,历来是文学著作中颇受读者喜爱的门类之一。家书是作者最近于第一手(稍次于日记)的记载,从家庭琐事、日常见闻,到社会经历、对事物的看法见解,方方面面,包罗繁多,而读者除了欣赏作者的文笔之外,更可以由此了解人物的品格、思想,乃至价值观和人生观。书信中对小辈的教诲,还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意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学术界、出版界对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的研究步步深入,取得了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四十年来,他本人著作和传记、年谱、画传、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可称蔚为壮观。韩芳女士数历寒暑,不仅收集了张元济先生的家书,还对其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了严密的考订,并增加了许多背景材料,使这些一件件看似孤立的信件,构成了一本有一定系统的书籍。它既可以看作是一本家书类的普及读物,也同样应该视为张元济研究有独特视角的一项成果。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譬如我们家人丁稀少,祖父和我的父亲父子两代52年间一直生活在一起,这就很少存在留有家书的空间。书中1931年父亲去美国留学前夕,祖父给他写的《旅学弦韦》,从卫生健康、读书研习,到朋友交往、开支节俭等几乎全方位地做了谆谆教导,既是对儿辈的教诲,也是他本人为人处世方式的写照,是可以和他1948年创作的广为流传的《新治家格言》相并列的一篇佳作。
这部家书集编入祖父致海盐张氏族人的信最多。祖父14岁时,随同曾祖母从他的出生地广州返回故里,苦读诗书。彼时,我国古代传承下来的“聚族而居”的社会形态在家乡并未有所改变,因此,在他年轻的心灵中,“敬宗睦族”始终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待成名之后,便约集族中长辈和堂兄弟辈,编辑宗谱、修缮宗祠,还出资创建了海盐张氏公墓,力图改变落后的丧葬习俗。这些工作在书信中有不少记载。抗战八年,带来了社会生态很大变化,胜利后,祖父与族中亲戚仍有往来。记得我幼年时,见过其中辈分最高的长者幼仪太太(张德培),他是祖父的叔辈,我自然应该称他为“太太”(海盐人用语习惯,即“太公”之意)。幼仪太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尽管那时他年事已高,但步履矫健,话音响亮。他是一个办实事之人,在海盐有实业,与人合伙开办轮船公司,所以常说他“有半条船”,我当时一直不理解这“半条船”怎么能在水上行驶呢?
本书还收集到80多件祖父给他堂侄张家昌的信。家昌伯父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专科,在商务印书馆任庶务,商务老人说凡是他经手的基建或设备项目质量都属上乘,经久耐用。这批信大部分书于1950年代初祖父患中风以后,因家昌伯父任庶务,与水电维修商家熟识,家里凡有这类事情,祖父就去信找他。其中1951年9月21日至28日四信提到的电钟,是祖父病后特地买来挂在他病床对面,目的是使他能看清钟点,下午让他的护理工按时到我上学的小学把我接回家。本世纪初,家昌伯父的长子声远堂兄,得知我在编《张元济全集》,就把这些信件带来给我看,我如获至宝,抄录下来,对其中一部分作了书写年份的考订后编入了《全集》。后来声远、声荣堂兄决定将这批信件捐赠给家乡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该馆设有张元济著作和研究资料的专柜,但今天要收集到张元济先生的手迹,谈何容易!他们为此专门举行了捐赠仪式,并予以珍藏。
本书信集的第三部分为致姻亲,“姻亲”,顾名思义,是由婚姻关系结成的亲戚。其中很珍贵的一件,是吾鸿墀太老伯1937年给祖父的信及祖父在信上的批注。这封信包含了许多历史信息。吾太老伯是祖父原配吾氏祖母之弟,吾氏祖母早年难产亡故,但张吾两家的戚谊继续保持,抗战前夕,吾太老伯的夫人病重,祖父从上海去海盐探望,特地请了医师同往诊治。信中“小孙用福”系吾太老伯的长孙,后来在商务谋职事未果,便由我父亲介绍他去银行工作。用福表兄为人厚道、勤奋,工作上进步很快,却不幸英年早逝,我听父母多次说起此事,他们都为之扼腕。“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炮火毁去海盐县城大半,祖父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与吾家的交往也中止了。半个世纪之后,海盐县人民政府在上海举行海盐籍人士联谊座谈会,父亲在签到时听见一旁有人叫他“树年叔”,问询之下,原来是用福的二弟鼎新表兄,从此两家世谊又得接续。又得悉用福的三弟用明表兄主持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工作,我有幸与他在同一个系统工作,联系更多。在家乡海盐前后举办过五次纪念张元济先生的学术研讨会,用明表兄都应邀参加,带去了论文,发表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上。
《张元济家书》即将付梓,韩芳女士嘱为之序,谨书数行,以抒感怀,也希望我中华文化中,名人家书结集出版,既记载历史,又示谕后人的优良传统得以持续。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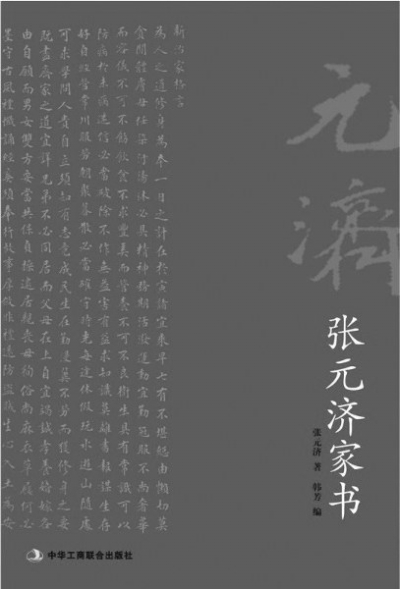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