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中国》(全九卷),薛保勤、李浩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年1月出版,定价552.00元
我们不但要生存,而且要诗意地生存,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创造诗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创造出诗。诗意是生活的一个要素,诗是生活的重要维度。中国是诗的国度,几千年的文明贯穿着诗的脉络,《诗经》《楚辞》、汉魏古诗、唐诗、宋词、元曲,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实则是一代有一代之诗。因此,用诗意的眼睛打量历史、用诗的目光看待中国则顺理成章,这正是薛保勤、李浩主编《诗说中国》的根本情由。薛保勤先生是著名诗人、优秀报人,李浩先生是唐诗研究的著名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时写一手好散文,两位都是诗歌的会心人、诗意的创造者,由他们组织策划这套《诗说中国》正得其人。
《诗说中国》一套九卷,九卷所涉,又无一不与今天大部分中国人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如《耕读卷:耕读传家》即暗含着巨大的困惑:在工业化、后工业化或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我们应如何对待我们曾经辉煌的农业文明,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到底应该怎样“改造”曾经的农业大国?《民俗卷:诗语年节》则促使着读者思考:我们现在的节日越来越多,泛节日化是当代文化的一大特征,但同时现在的节日又越来越无味,人们往往在商场血拼、扎堆旅游、胡吃海喝的虚假亢奋后产生巨大的空虚和厌倦。节日原可构造人类共同体,给人归属感、充实感、幸福感,但是现在却是更多的虚无感和逃离感。而读完《家国卷:家国情怀》,我不禁想问,对于生活在现代主权国家的公民来说,到底应该怎样摆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都具或隐或显的当代意识。
经纬既成,《诗说中国》每卷著者自出机杼,缀文成书。每卷虽纲目不同,但设计原则一致,即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由点入手、因点成线、以线带面。每卷的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皆是社会生活某一侧面的要素;从文学的角度说,所选诗歌要么出自名家、要么是为名作、要么间有名句。著者以此勾画一条诗学社会学的线索,进而呈现古代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即如刘炜评教授所著《战争卷:铁马冰河》,是以诗语述说古代战争,全书分四个部分,“情怀篇”“人物篇”“风物篇”“事件篇”,抓住了战争(诗)的基本要素。“情怀篇”分述“战争诗中的士人襟抱”“战争诗中的灾难控诉”“战争诗中的乡愁”“战争诗中的哀悼”,“人物篇”分述战争诗中的“将帅”“士卒”“百姓”“女性”和“胡人”,“风物篇”分述战争诗中的“军阵沙场”“边塞风光”“名关要地”“兵器与军制”,“事件篇”诗说“楚汉之争”“安史之乱”“宋金对峙”“抗倭战争”“明清易代”“近代中外战争”,其中隐约贯穿着时间顺序,把古代战争诗中的关键点提炼出来,加以阐述,足见用心之良苦和细致。
在具体的阐述解说中,《诗说中国》做到了文学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结合。《诗说中国》,原是从诗歌入手、以“诗”来解说中国,故文学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此只一端。除此之外,《诗说中国》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其解说文字上。笔者随手翻读《行旅卷:行吟天下》一页,读到诗说“岳阳楼”一段,著者因杜甫的《登岳阳楼》说到:
诗圣的孤舟漂在湖上,恐怕一辈子都不能摆脱孤独和忧愤,然而如果把我们的视角放大一些,就会发现他并不孤单,四百年后,他的知己出现了,这个人就是陈与义。同样的忧国忧民,同样的忧身忧命,也同样在岳阳楼上留下了沉郁壮阔的诗篇:“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陈与义《登岳阳楼》)不知是陈与义有意模仿,还是他们本就性情相同,只是不同的时空造就了不同的命运,我们无从知晓。
人到中年的陈与义,诗文中都难掩风霜,字里行间除了悲壮之外,更有刀刻般的坚毅。这种老而弥坚,除了岁月之外,再也没有另外一件东西能将其给予一个男人……(《行旅卷:行吟天下》第66页)
这样的文字充满了文学的灵性,直可当美文来读。而在整套《诗说中国》里,这样的文字虽非触目皆是,但亦不在少数。
《诗说中国》是以诗来说“中国”,说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因此,历史性、文化性也是其行文要求的目标。虽然是“诗”说,但是诗只是进入中国的切口,诗是中国文化最绚烂的色彩之一,但是并非全部,好诗往往是超越历史的,但是每一首诗又都有历史性,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诞生的,它总是天然地携带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诗且如此,何况中国。因此每卷著者,总是从诗的起点出发,左顾右盼,牵合经史,联通古今,举凡儒释道各家经典、文人别集、史志文献、小说笔记、民谣民谚等等,能为其所用者,务尽其用。所以,通过《诗说中国》,著者为我们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审美化的中国,而且是一个有着特定历史体温的、浑融整一的中国。因此,我认为《诗说中国》具有一种文化诗学的审美取向。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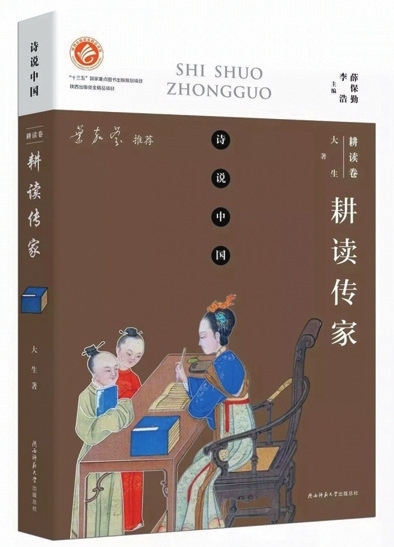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