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时间纷至沓来》,我们会遇见一个“有主见”、有定力的人,她沾染书和植物的美好气息,从亲切的汉字中向我们走来,她的“气质是清朗的,就像冬季雪晴后的空气”。这本书,疏朗静美处,有繁盛清劲;时显炫然,然而更多的,又是心性里的寂然。
陆梅的散文新著《时间纷至沓来》中,充满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美好的植物和书。
熟悉陆梅的人很容易发现,她的身上,有着很深的植物情结。她的诸多书名,像《生如夏花》《当着落叶纷飞》《辛夷花在摇晃》等,即可证此。现在回想起来,和陆梅初识,就在浙东某处溪滩的古树林边。还记得,初见那片清新蓊郁的溪林时,人群中的陆梅,有顿然发亮的眼神。
读完这本最新出版的《时间纷至沓来》,让我进一步认定,陆梅前世,就是一株植物——在那个时空中,雏菊、桔梗或辛夷,应该就是她的姐妹。她这样自述:“我的每一次出行,总忘不了对一朵花、一株草、一棵树的投注。我对某个地方的回忆,也常常是融入了某种植物的回忆。”确实,对于故乡松江,她记住的,是华长路的水杉,是老家门前那棵初春灿烂绽放的紫玉兰;对于新疆,她倾情的,是维吾尔女子用来描眉生眉的“奥斯曼草”;还有浙江的香榧、丹东的橡树、东京的银杏、西班牙的橄榄树,往往,“站在树下看天,恍惚自己也成了树的一部分,美得舍生忘死”。她“发愿想写一本我的《植物记》”,她承认,“……我和树的感情,早已融进了心灵。我的成长,我看世界的眼光,我性格里那一部分神往自然的因子,肯定和树有关。”
除了植物,书,是陆梅的特殊亲人。她的同事、青年作家张滢莹曾描述过陆梅的工作环境:“走过她书的‘围城’,恍惚觉得这大概就是她的桃源,也是她的驿站,帮助她隔绝于一切繁琐,也令她在人生的旅行中暂时歇脚。”这本《时间纷至沓来》当中,包含了那么多陆梅与之交流过的书,古今中外的书。读完全书,你会意外发现,原来书中还潜藏有一张如此高质量的书单。
陆梅看书,有着属于女性的独特习惯:“总是以‘发现的目光’,在文字里寻找会心的细节。”她读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留心的是三岛对屋顶那只“神秘的金鸟”的描绘;读沈从文,她注意的是,“沈从文表达喜欢的心情时,不说‘喜欢’,说‘欢喜’”;读法国作家彭塔力斯,她看见这位萨特的学生是这样描写水仙的:“一种近水而生的忧郁的花,垂向自己,长在春天”。
陆梅写书,读书,向热爱文学的人们推介书评论书,“而书,我把它视作我的另一个故乡,纸上的故乡”。
植物与书,是陆梅的慰藉和热爱。然而,让这本新著特立于书林,真正具有打动人心力量的,是书中深刻存在的对时间、对人生、对生命的哲学式的悲感和痛感。
“时间纷至沓来”,这个书名所呈现的意象,在书中至少有四次近乎重复地提到。时间如电移去。陆梅是疼痛的、异于常人的时间敏感者。
她这样理解日常:“所谓日常,既是日日之有常,亦是每日之无常。”
她内心时时响起的,是顾随先生的这句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
这种哲学式的悲感和痛感,不仅让她与一般的美文制造者区别开来,亦使她那些“闪耀着温暖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芒”的文字(作家徐鲁语),有了深扎的根系和生命的表情。
也许是气息相契的缘故,在陆梅新书中,还意外相遇到多年的友人和曾让我动心的熟悉风景。
譬如,她说到云南的好友叶多多:“素未谋面,竟一见如故”,“叶多多身上有种奇异的多民族气息……和她聊天,感觉身上有种边地山林的神秘气质,呼应着土地、星空、深山、溪流……的万物有灵和宽阔纵深”。譬如,她在书中记叙某年春节一家三人登桐君山,而我,也曾在过去的某个时刻,独自坐在有白塔的桐君山顶,透过枝杈,看了很久富春江。
散布书中的众多只言片语,也令我印象深刻:让我认同,给我启示,或瞬间产生莫名的共鸣。
如她的日常,2012年的大年初一:“日常里的一天。黄昏时刻,下楼透气,自觉意志消沉,书写的心情散淡。”真实感。
如论写作,她同意马尔克斯:“事实无须证明,只要落笔,即为真实发生。”这是对写作者的极大解放。
读陆梅文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汉语字词、文法和意境的美”。她的这本书,疏朗静美处,有繁盛清劲;时显炫然,然而更多的,又是心性里的寂然(不过,这种“寂然”并非没有能量,而是“寂然光动大千”)。读《时间纷至沓来》,我们会遇见一个“有主见”、有定力的人,她沾染书和植物的美好气息,从亲切的汉字中向我们走来,她的“气质是清朗的,就像冬季雪晴后的空气”。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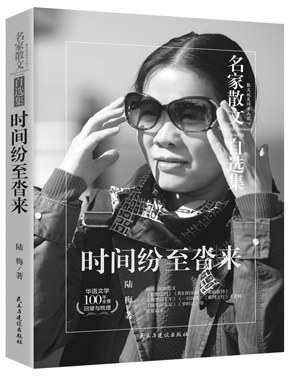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