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星空灿烂的“大家”,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暗淡了星光而隐进了历史的星河。吴泰昌本人就是一位置身于这条星系中的陪伴者。
纯粹的历史写作其实大多是一种应用文体的写作,其叙事方法是从史实的本身去着墨的。文学史也不例外,因为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特殊门类,专门的“中国文学史”以及现、当代文学史的版本不下数十种,但当然是通识的文学史家眼光对历史的断代等作出自己智慧的见解,除了语言风格的不同,在叙事上大多强调实证性。新近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亲历文坛五十年》一书,则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以朴实的纪实风格和非虚构的叙事行文,娓娓道来五十年中国文坛的“人”和“事”。作者吴泰昌先生是蜚声文坛五十年的编辑家、散文家,也是一位卓著的文学史家。
与“亲历大家”系列一人一本不同,这本《亲历文坛五十年》是从吴泰昌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见诸报端的文章中精心选辑出版的。从选编的数量上看,尤以作者写于本世纪头十年的数量为重,记述的频次为高。可见,那些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星空灿烂的“大家”,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暗淡了星光而隐进了历史的星河。吴泰昌本人就是一位置身于这条星系中的陪伴者,他见证过星星的运行并努力地记载着星星的轨迹,像一个文坛的值勤哨兵,更是一位星空的仰望者。所以,流淌于他笔端的言语,总是那样的真诚温情而又凝神聚气,有时候捧书读着、读着就随着文中的意象而如同一起走进了现场,仿佛读者自己正在与某一位“大家”的亲切会面。全书由39篇记述作者自大学时代始,见识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30位人物往事,就如同30个人物的小传,多数篇章则是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无从见到的珍贵史料。吴泰昌不愧为一个文艺编辑大家,他善于将散帙的素材或者是不为人们关注的小事,通过记忆这把金梳理出一出出精彩的头绪,在文学史的开掘中,做着既拾趣又拾零的精巧又精细的工作,为丰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了有益的贡献。不过,如果我们说《亲历文坛五十年》具有史学的价值,那么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意识的史学写作,作者在结合自己置身于一种特别的历史情境时,其写作时对传统的延续以及方式方法,或多或少地产生可能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延续中会保留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但是它是合理而有情趣的,这些都需要读者在阅读中去感悟。
吴泰昌不乏史学写作的功夫,就像书中他自己述说的一样:“1958年,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在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同时,又着手编写《中国小说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几项活动我都参加了。”近百年前,北京大学校史上著名的“文科教授案”就曾倡导:习文学史者,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从游国恩、林庚、王瑶到朱光潜、钟敬文等北大中文系的魁星,在史实的演进上赓续着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的传统。这一文脉至少影响了在北大浸濡长达约九年时光的吴泰昌,比如,我们读他的散文,时常能触摸到史实的温存。他在写往事时,或者是对历史的钩沉中,时常从一个特定的历史线索切入,但是他从不像史家们那样纠结在史实中反复地梳篦,也就是说他不拘泥在某时某刻发生的某件事上,但清晰而跳跃着任由自己的思维去发掘、联想、展开,抒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抒发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汪洋恣意而收放自如。譬如,书中选定的关于巴金先生几个篇章就是这样,写作者自己与巴金本人及一家结下的友谊,过程是平铺直叙的,甚至是一次散步路上的偶遇,但其中透出的情感则是细腻的;写巴金与冰心之间的交往,则更是具象化的白描,没有一丝的修饰。在题为“巴金这个人……”中,两位“平时以姊弟相称”的文学大师既散发着长者的智慧,又充满童稚一般的可爱。我们在认真地阅读之后,感到吴泰昌先生的有心与细致,他总是随身记着笔记、随身带着相机,这样他写下的文字以及作为一种印证的影像,从来不是靠虚构获得的,相反是一种朴素的真实感打动读者。入选书中的这些文学大家生前都对吴泰昌如此自觉的史料意识和文化责任感极为赞赏,难怪有人写道:“钱锺书称举其‘兼有史料价值和轶事笔记的趣味’,吴组缃看重其‘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的描述’,孙犁推许其‘文字流畅,考订详明’。”所以,这本《亲历文坛五十年》的价值贵在“亲历”,带着鲜明的个性色彩,为我国文学史留下了大师们一个又一个真切精彩的瞬间,殷鉴了让人回味遐思的历史畅响。相得益彰的,则是吴泰昌的这些具有文学史家的笔法和体验,又总让我们在阅读时饱览着散文的色彩。
吴泰昌是散文作家,他最早闻名于文坛的是那本散文集《艺文轶话》,1989年获中国作协举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后来在他各个时期的散文写作以及他的“亲历大家”系列丛书中,他的文字朴实而凝炼,不尚语言的华丽,继承着“五四”以来的优秀传统。在《亲历文坛五十年》中,通过感受作者由于对人物的熟识,由于对散文创作的驾轻就熟,无论是前辈大师的精彩谈话和点点滴滴的待人处事,还是对相关图片、信件、资料中,都能触摸到不同人物的个性,其人格的张力潜在于吴泰昌的随意、恬淡的语言叙述中。对每一个人物的叙述,虽然都在一个一个的故事中展开,细节极其丰富,但从不会因为着力于那些生动的细节而游离于主题之外,往往他用冷静、简练的语言,有时候则用朗朗上口的生活化语言,写出大家们内在的深刻,写出这些有着不同常人阅历人物的个性。他们中随便一个人的一个细节往往曾影响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进程。咸宁干校的往事,是印在那一代文学大师们脑海中的集体苦难记忆,吴泰昌也不例外。所以,这段时光也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在“走进叶家大院”一文中,除了对这个坐落在北京东四八条幽深的四合院,行文不繁,简明扼要,像一幅老北京的民俗画,自然、素净,对叶圣陶老人的起居习惯、为人为文等都作了惟妙惟肖的叙述,令人亲切甚笃。作者本人曾长期在《文艺报》社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对该报的过往与今生都了然于心。此次选辑这本《亲历文坛五十年》,一方面在布局时将“忆茅公”一文列为全书的开篇,一方面在结构文章时倾注了对茅盾先生的全部热爱。当我们徜徉在这些鲜活、具体、生动的故事中,我们不仅领略到一位文学史家的举重若轻,而且还能品味到一位散文家建构历史的语言魅力,全书显现着文学史的散文化叙述,让读者完成一次史实审读与语言审美并行的阅读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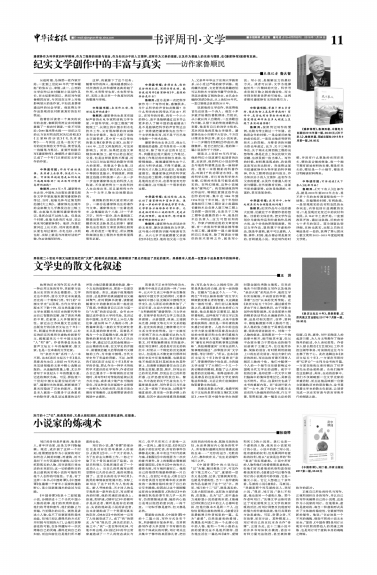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