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3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和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文学苏军新方阵”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并在会上向文学界整体性推出了朱文颖、王一梅、戴来、韩青辰、李凤群、黄孝阳、曹寇、育邦、张羊羊、孙频等10位70后、80后江苏新一代作家,这是继2016年在北京推出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周梅森、储福金、毕飞宇、鲁敏、叶弥等10位江苏文学领军人物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江苏文学将以强大的领军人物、新方阵和新秀阵容,构建一支可持续发展的、充满活力的文学苏军队伍,为江苏文学、中国文学的发展担起更多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
省作协党组书记韩松林在研讨会上说,推出“文学苏军新方阵”的目的,一是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培养高水平创作人才,进一步锻造文学骨干;二是集中展示文学苏军新阵容、新力量、新实力,扩大江苏优秀作家的知名度、认可度;三是更好地推动优秀青年作家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勇于担当时代使命,更多创作文学精品,攀登文学高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好的精神产品。
朱文颖:希望从形式上做减法
近二十年前,朱文颖已经作为“文学新人”为文坛瞩目。她的第一本书是评论家谢有顺主编的“文学新人类”丛书,一起收入丛书的一共有四位作家,分别是卫慧、周洁茹、金仁顺和朱文颖。也是近二十年以前,作为当时的热点新闻事件,在《作家》杂志,70后作家第一次集体登上中国文坛……严格意义上,朱文颖算不上“新”。但是这次入选文学苏军新方阵作家,其实有另外层面上的意义。朱文颖的理解是,首先,如同今年第七届江苏书展的主题是“文脉”——江苏有很多著名作家,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范小青、苏童、叶兆言、毕飞宇等,而这次被选入“苏军新方阵”的,基本都是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这就有着某种文脉的传承与延续的意味。而“新”在汉语里的另一层意味,则是生命力、旺盛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
与早年的写作不同,现在朱文颖会关注一些更本质的东西,回到“这篇小说是关于什么?要说什么?”的基本概念上。“这就意味着我希望从形式上做减法,从一种外在的小说美学转换成一种更为内在的小说美学。小说,作为与结构主义特质最为亲密的艺术形式,一定存在着更多的隐秘通道。在我现在这个年龄,阅历、思想、见识以及视野会比文本本身更为重要。”朱文颖说。
每个人都有他在生活以及艺术上的天性。朱文颖的天性可能更接近一种纯粹的诗性,或者一种纯粹的理性。有时候她甚至开玩笑地觉得,自己其实更应该成为一个诗人,或者一个理论工作者。近几年,朱文颖介入了一些艺术策展和艺术批评。“它让我思维更加活跃,视野更为宽广。这对于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比什么都要重要。”
目前,朱文颖正在写几个中短篇小说,以及一个长篇。“如果人的本身没有成长,重复写作其实毫无意义。我有很多想法,我的问题在于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容器,把我的那些想法用小说的形式装入那个容器。或者说,那个容器就是小说形式本身。”朱文颖曾经还对非虚构作品相当感兴趣过。甚至有一个自以为很牛的题材,太有意思和挑战性了,因此不敢轻易去动它。但她想,总有一天,她会把它写出来的。
王一梅:归零心态会让自己轻松前行
从为幼儿写短篇到为小学生写长篇,从写童话到写儿童小说和纪实儿童小说,王一梅的写作一直在寻求变化。她认为自己比之前多了对生活的思考,转身再写童话的时候,会有新的面貌。
王一梅曾经担任幼儿园教师13年,特别体会到和孩子们珍贵的相处就是自己写作的宝库。孩子要听故事,她就讲故事,一个讲故事的老师变成了写故事的老师似乎很自然。每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一把通往童年大门的钥匙。从事儿童文学多年,王一梅越来越感觉童年的纯粹和珍贵。很多年之后,读着儿童文学长大的孩子变成大人的时候,想起童年阅读过的儿童文学,他们也许会觉得那是生命中的亮光,对人生真善美熏陶最好的方式。
王一梅的儿童文学创作一开始是凭借兴趣做出的选择,现在看来,是她重要的人生选择。如今,儿童文学创作对于王一梅仍然是快乐而美好的,是她梳理、反省、思考的一种方式。
长期儿童文学的写作更让王一梅看见了童年的内心柔软、想象丰富、勇敢……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有时候,觉得信心百倍,有时候怀疑自己。每当这时候,她总是对自己说,一开始就是什么都不会的,一字一行都没有发表过,那个时候,都没有退缩,如今总算有点经验了,应该会好。王一梅说:“我想,阅读学习、归零心态会让自己轻松前行。”
戴来:写自己想写的愿意写的
年过不惑,戴来从河南回到苏州父母的身边。
回到写作的话题,戴来觉得都“不好意思多谈”,因为写得实在太少了。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说“狼来了”的孩子,说了很多次要好好写东西,但一直写得很少。
对戴来而言,写作是一件自己一个人就能玩起来的游戏。二十年前,完全是凭着一股子热情,带着游戏的心态开始写作的。但在写了百八十万字后,她突然觉得写作已经“不那么好玩了”。正如一件手艺,不小心掌握了一点门道,完全放下是不可能的,也许这个比喻不恰当,也不够冠冕堂皇。换个说法,二十年,写东西完全是因为好玩,现在还是下意识地会在有意思之外寻找一点意义。“写作上我没有太长远的计划,不出意外的话都会一直写下去吧。将来对我而言,其实就是眼下,至多是明天,眼下正在写的那个就是我对写作的全部想法。至于写出来会怎么样,将来会怎样,顺其自然吧。”戴来说,这么多年,自己一直是一边懒散着一边自责太过懒散一边为自己的懒散寻找借口。写自己想写的愿意写的,是她一直没有改变过的写作的初衷。
韩青辰:写作重建了自己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时间是什么呢?假如别人没问我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不过如果有人问我时间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韩青辰对写作就是这种感觉。写作犹如她的呼吸,她会呼吸,可是她对写作恐怕永远也不能说“我会我懂我知道”。
作为警察,韩青辰经常被问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写儿童文学?她说:“因为我是警察我才写儿童文学。多年警营采访,让我发现每个问题人生都有一个问题童年,如果他们的童年及时阅读所需的儿童文学,伤痛被医治了,那么他们的生命也许就不会失丧。”她是穿警服的儿童文学作家,她知道多一个失丧的童心,社会就可能多一个罪犯,国家安全就会多一份威胁,人民警察就可能多一份危险与牺牲。
她愿意在纸上执行使命。所以她写《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希望每个生命百折不挠;她写《小证人》,希望所有人都有坚持真的勇气;她写《因为爸爸》,希望那些读过英雄故事的孩子,长大成为捍卫美好与和平的人。
在她心里,儿童文学是鲁迅先生的《药》,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等等,是关乎个人兴亡、民族盛衰、国家安危的文学。
韩青辰一直忠于自己“成长是历险与挑战”的生命经验,儿童文学是穿越幽暗成长隧道需要的一道光,她愿用生命传递成长之光。“假如我是灯盏,那么生活是油,写作就是燃烧的灯芯。没有写作我就没有生命。”韩青辰说,写作重建了自己,写着写着警察与作家的使命暗合了。她终是觉得,儿童文学要有与孩子们的心灵疾苦与成长危机在一起的使命与担当,其实也是家国之担当。
李凤群:以全新的视角开始
眼下,李凤群生活在波士顿边上一个人口密度很低的小镇。这里一年中有半年是冬天。她的屋后是湖泊和湿地,可能离梭罗生活过的瓦尔登湖太近,环境也极其相像,她渐渐沉迷于这种静止的生活。只要她愿意,可以一整天不用说话。每天上午十点,她喜欢站在窗口等着看邮差的车开过去,就像一个仪式。陪伴她的也多是久远安静作家的作品,比如,最近她读加贺乙彦、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王阳明和圣经。去年,当她开始创作新长篇的时候,明显感受到自己的性格和写作受到了陌生地带的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滋养,在陌生环境之下,作为一个外来者,李凤群得到了全新的视角。
“我享受这个状态。我不确定手头的这部作品一定多么受欢迎,但它对于我来说是向下行的一个开端。下行即上行,底部即深处。这个过程妙不可言。”李凤群说。有时,小说是看似软绵的,但是,小说可以传递小人物的自由意志,小说既是现世的安顿,也是精神的图存。小说是一条征途,期间有绝望有反省也能获得解放。严肃而有责任感的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会插手现世的困境,理解其中的甘苦,与之碰撞或和解,这暗藏的能量,一直在推动社会进程,这是每个作家的目标,李凤群也不例外。
黄孝阳:“我是一小团荧火”
“从攀援树上,学会了直立行走,学会了钻木取火。新时代澎湃而来。这是一个类似奇点爆炸的事实,正在构建起我们今天的现实。它渴望着新逻辑,新发现,新思想。我渴望着这种‘渴望’,渴望我对这个‘新’字有点滴拾掇。”黄孝阳如此理解“文学苏军新方阵”之“新”。
黄孝阳尊重文学传统,可心里老觉得“传统虽好,已然匮乏”。他对现实主义推崇备至,可今天的现实是怎么形成的,其力量与根源何在,他渴望找到它们,并对未来抱以相对乐观的遥想。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发现当代中国人的特质与经验(基本是一个城市文明的范畴),能看见未来人类的足履。
碎片化的今天,写作很难保持注意力。如何把这些不同属性的碎片(有的是金属,有的是河水,有的是木),按照某种有机结构加工制造出一个可以测量时间的钟表,不容易。仅对这些碎片的打磨与再加工,就很耗时伤神;更毋论后面千百道的工序。
过去黄孝阳的写作,大致是一个河流叙事,让小说中的人物主宰情节走向;现在更多的是先画好设计草图,他觉得得做这样一个东西出来,就像一个手艺人做一块表,专心致志,舍此更无它物。“作为写作者的我与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次要的;而表是第一位的。”黄孝阳说。
育邦:小说因自然而生
年轻时,育邦希望作品传达尽量多的认识、感官、洞见,希望它们是棱角分明的,甚至是剑拔弩张的;随着时光的推移,对于世界与自身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察,表达的欲望却越来越小。
既写小说,又写诗歌、随笔,育邦觉得这只是自己写作中三件不同的外套而已。“小说像一件正装,我希望它浑然严谨,细微阔大而具有张力,全面深刻地展示一个创造性的自我姿态,对于这个广阔世界的深度介入;诗歌像是内衣,柔软贴心,与自己的肌肤与血肉相连,甚至隐秘地包涵这个人内心的晦暗部分,它真切,不容半点表演,是我那颗弱小心灵的外在显影;随笔像一件休闲外套,是张家长李家短,是与艺术的对话,是与古今中外作家的聊斋……”他的小说《身份证》《恐龙先生》等,有很多探索和实践,试图写一种没有明确指向的小说。比如《身份证》本身就没有什么指向,我们看着它试图将要有所指向,但马上又消失了,它拉开弓箭只是虚假的一个动作而已。
这样的小说有意义吗?育邦肯定地回答:有。它回到了艺术本身,回到了小说它本来的面目。假如小说像人一样也有生命的话,他想,我们必须赋予它人性,甚至还要讲人权,不要对它进行没完没了的说教,不要给它穿各式各样可笑的花衣裳,给它自由,给它空间,而不是强行地让它干这干那。它因自然而生,它因呼吸自由的空气而成长,它就叫小说,一种唯一的本体意义上的小说。 他认为自己理想中的语言风格是简洁而深往:“我以陶渊明、孟浩然为标准,看起来通俗简洁,读起来却又韵味无穷,留有巨大张力。”
曹寇:精准是第一法则
很多人认为,曹寇“风格化”很明显,辨识度较高。“我手写我心,我就是这么个人,我希望我能和自己无限接近、无比相像。”曹寇说,自己的追求,或者说理想状态是:“我的作品能够体现我的‘问道之心’。”
在曹寇看来,自己的小说是太“热”、太温顺了。“他总觉得自己的语言还不够精准。精准应该是所有写作在技术层面的第一法则。以前当教师时,曹寇经常闲得无聊只好看教室里的文字。黑板报上的学生作文不行,挂在墙上的名人名言也不行,怎么看都透着假,最后他发现粉笔盒上几十个字的产品说明还有点意思,精准无比。
已经写了十多年小说,却觉得自己完全不会写小说,“我希望自己写得更好,在够更好的过程中,我的姿态应该是垫着脚尖的,与‘会’相距甚远。”曹寇认为自己不具备或还没有体现出像样的创造性,但这不影响他对创造性的景仰和追求。他所理解的,创造性就是最大限度并诚实地描绘出这个世界这个人间的真相,并自然地呈现出接近“真理”的光亮。
正是因此,他才有写下去的动力。“写作于我只是一项技能,一个目前还能驾驭的生活方式,一个某种追求的途径。如果我感到自己写不下去写不动了,我就会放弃写作,我反对‘坚持写作’这个说法。”曹寇说。
张羊羊:把自己重复彻底
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中对汉语的简洁精神彻底改变了张羊羊的写作观念。面对万事万物,永怀敬畏之心。他开始坚信,只有在大自然里才能寻找到最朴素、最美好的情感,他也愿意用尽一生,以汉语呵护好“大地道德”里古老的人与动物、植物相互宽容的生存秩序。
他是一个想把自己重复彻底的人。“文字随缘。它们遇见我,就长成了我的样子。也有时候,老长一阵子不写,一时进不了状态,会看着空白文档发呆半天。有一个方法对我很有效,摊开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读上几页,心就平静下来了,我就听到了万物在我身边呼吸的声音。”目前,张羊羊只想把十几年来写的植物系列《草木来信》、动物系列《大地公民》、人物系列《乡村肖像》尽快地结个集子,算是一种告别。还想写个《二十四节气》,向没有写完《二十四节气》、过世近20年的苇岸致敬。
孙频:把写作当成艺术来打磨
在评论家何平看来,孙频的小说在中国年轻的作家,年轻的女作家中是一个异数。这种“异”是她下笔的“狠”、“拼命”和不拖泥带水;她对人性之恶之猥琐穷追猛打;她对世界呈现出来的,我们看得见的部分有异乎寻常地不信任,孙频要写那些隐匿的,遮蔽的,看不见的部分。所以,孙频在键盘上敲下一个个字,用的工具是刀子——各种样式,各种型号的刀子,这些刀子用来是精微地解剖世界和世界中的人和人性。
2016年,青年作家孙频自山西调至江苏作协。近两年,孙频的几个中篇《我看过草叶葳蕤》《光辉岁月》《松林夜宴图》,相比以前的小说她付出了更大的心力和更多的时间,把写作当成艺术来打磨的。
过去,孙频的写作总担心瓶颈,现在反倒觉得正常。“关键是你对写作的最终态度,以及你心里是否有真正的热爱和虔诚。”孙频最切实的想法,是想写一篇是一篇,尽量能有一些新的思考,有更多的艺术含量,有更多真正的领悟。“至于长篇,我觉得不应该好大喜功,到功力够的时候自然就写出来了,功力不够时就不要好高骛远,还是修炼自己最重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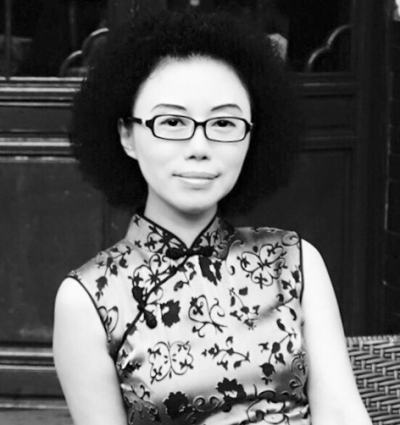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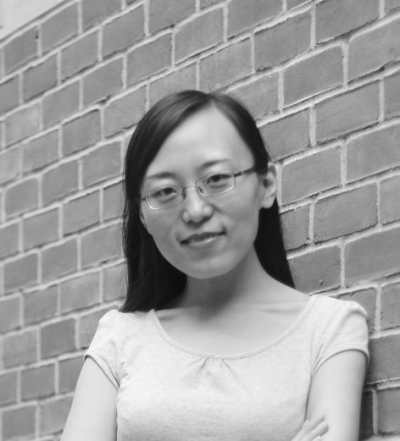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