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中,吴稚晖提出了“欢迎穆姑娘”的口号。他认为“赛先生”代表智识,“德先生”代表公德,二位“先生”之外,中国还需要一位“穆姑娘”(moral)来“主中馈以治内”,以私德来补智识与公德的不足。谁想这位上个世纪好出惊人之语的无锡老头简直宛若先知——因为,在今天的科学史研究中,我们居然真的迎来了一位“穆姑娘”。
科学史研究的传统向度
多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今天已经淡忘了,但犹记中间一幕:一个瘦瘦弱弱的姑娘,向大家介绍了一篇开普勒的“科幻小说”,内容是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托梦大谈月亮上居民的生活。这是多么八卦的研究啊!紧张严肃的会场突然就活泼起来,我等听众在台下被撩拨得不能自已,台上的来宾却开始不那么团结了——科幻小说也能进入科学史研究范畴?在座的大佬不答应。
这个作报告的姑娘就是穆蕴秋。在那次会议的茶歇我调侃她:“谁让你的论文不在人家的科学史研究向度里呢?”这句话据说后来成了一句“名言”。我猜想,大家之所以这么咀嚼这句话,大概是因为都熟读过当时影响很大的几篇科学编史学文章。
这几篇文章的主题都是呼吁科学史研究要走向“新的综合”。其中一篇援用“向度”概念,认为在不同信念和动机的牵引下,科学史研究指向不同的认知目标,从中便可以归纳、辨别出具有指向性的四种维度:其一是历史向度,代表人物是霍尔,同萨顿、柯瓦雷本质上一样,他坚信要将科学史当作历史来研究;其二是科学哲学向度,指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影响下兴起的“科学史-科学哲学”个案研究;其三是社
会学向度,前期是盖森、默顿的工作,之后是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全面崛起,再往后又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重要参与;其四是科学向度,研究指向当前科学或为当前科学服务,霍尔顿的工作被认为是很好的典范。
穆蕴秋的科幻小说研究——这种研究后来被导师江晓原教授老于世故地定名为“对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当然不在这四个向度中。那时在几乎所有人的观念里,文学和科学就像磁铁的两极,怎么都凑不到一块儿;在科学史领域里的文学研究?怎么看都格格不入。几年后有一次我向她推荐研究生,她还很认真地告诉我:做科幻研究是不容易发文章的。
然而,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之后,她还是把科幻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方向,欢欢喜喜地开始了研究。一晃又是几年,她不仅已在各种CSSCI刊物上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还有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本《地外文明探索研究》——这让人不禁感慨这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小撮人,哪怕“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也能“一念便入世”,让人礼敬赞叹。
翻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时常会想起当年的调侃。我甚至觉得它已经成了一种隐喻,恰好反衬出当下科学史研究领域包括我本人在观念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何时发生的我不得而知,但就我个人而言,自那次会议之后,想法便和之前有了不同。至于本书,参照上述变化,我感觉也有几种不同的读法。
科幻研究可以不是文学研究而是科学史研究
一种读法是看对科幻小说如何进行学术研究。什么是科幻小说?
在《科幻小说史》中,作者罗伯茨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但我认为他是缺乏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的,因为一上来他就用达科·苏文的定义打掉了我的求解欲望:
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类型或者说语言组织,其充要条件在于疏离和认知之间的在场与互动,其主要策略是代替作者经验环境的想象框架。
天地良心,这个定义就像科幻小说本身一样不接地气,而且还富含学术黑话。好在穆蕴秋的《地外文明探索研究》从书名开始就毅然采用了更为明确的关键词,这显然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以“包含了幻想和猜测的科学文本”替代“科幻小说”,不仅避开了对“科幻小说”定义的纠缠,也让更多的文本得以进入研究视野。
然而作者所图并不止于此。书中依时间顺序,以五个主题涵盖了研究内容:17世纪对月亮存在生命可能性的探索和想象;天文学史上“适宜居住的太阳”思想源流和影响;19世纪火星运河的争论以及与想象中火星文明交流的探索;科幻作品中时空旅行的物理学理论背景;当下寻找地外文明所引发的争议。
对照罗伯茨对科幻小说的“粗略”分类:空间旅行故事、时间旅行故事、想象性技术故事和乌托邦小说,这五个主题恰能一一整理入册。这分明是在说,“包含了幻想和猜测的科学文本”同样能够完成“科幻小说”的叙事功能,甚至还可以理解为,“科幻小说”只是“包含了幻想和猜测的科学文本”的一个子集。而科学文本与文学之间也根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两者之间的边界也很模糊!
科学在谬误中成长:看到被屏蔽的科学史
另一种读法是看科学如何在谬误和失败中成长。其实,依我的个人经验,在我从大部头的流行通史阅读转向更细致的专门研究后,各类科学史上的谬误和失败就已然司空见惯,然而本书中的丰富案例还是再次刷新了我的认知:
查尔斯·莫顿在一篇阐释鸟类迁徙理论的论文里,试图通过严谨的说理来论证,冬天鸟儿都飞到月亮上过冬;威廉·赫歇尔先后在皇家学会的会刊上发表文章,对太阳本质结构进行探讨,提出太阳对人类来说可以是宜居的……
此外,那些科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大人物们,诸如马可尼、高斯、洛韦尔、弗拉马利翁,都曾经非常认真地讨论过月亮上、火星上甚至太阳上的智慧生命,设计过与这些智慧生命进行通信的种种方案,并且,这些设想、方案和讨论,当年还都曾以学术文本的形式发表在最严肃、最高端的科学刊物上!
尽管这一系列事件已然在我们的教科书和各种通史读物中被“屏蔽”掉了,但对于它们的钩沉与索隐,无疑展示了一种全新面目的科学史:科学其实是在无数幻想、猜测、弯路甚至骗局中成长起来的,科学的胜利也并非全是理性的胜利。
科学幻想是发表科学成果的另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读法,是看科幻小说如何成为科学家们的思想实验场。将科幻小说视为“思想实验场”不是我的发明,它来自前面提到的罗伯茨:
确实有这么一个地方,存在着费耶阿本德所提倡的科学类型(怎么都行),在那里,卓越的非正统思想家自由发挥他们的观点,无论这些观点初看起来有多么怪异;在那里,可以进行天马行空的实验研究。这个地方叫做科幻小说。
对于很多著名科学家都热衷于写科幻这个事实,我并不赞同那种因为科学家们旺盛的想象力无处安放的说辞。我有一个发现,正如伽利略时代的学者有一种把自己没有把握的发现“加密”后再发表的习气,幻想小说其实是另一种“发表成果”的方式。你可以把它看成拉卡托斯研究纲领式的保护带,或是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式的研究方法。其结果就是,幻想小说直接参与了对某些科学问题的讨论,或是直接影响了某类科学问题的探讨。
例如萨根的小说《接触》就在理论物理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虫洞研究;“稳恒态理论”的提出者霍伊尔也喜欢通过小说来设想人类与地外文明接触的后果,其基调与霍金一样灰暗和悲观;而业余天文学家马克·威克斯,甚至用一部小说来支持洛韦尔“火星运河”的观测结果。当然,最典型的还是对“费米佯谬”的求解,书中足足列出了50种解决方案,论文与小说参半——科学探讨与科学幻想的分界,在这里其实已经消失了。
开拓科学史研究的新边疆
在书的最后,作者总结道:科学拥有开放的边界,科学幻想应当被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同意将科学幻想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那么至少在编史学的意义上,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性就浮出水面了”。
这段话俨然是全书的压卷,我当然不敢简单地将它视为对当年会议的回应。
科幻小说当然能够理直气壮地进入科学史的研究,文学显然也应该构成科学史研究的向度,但仅限于此的话,未免又落入了布鲁克的老套路——在2000年当选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他已经将“科学史”解析为“科学+X”的“历史”,关于X,他列举了宗教、文学、艺术甚至女性主义。在我看来,这种“新科学史”还进一步提示了一种新的科学和科学史观念,这种观念不仅仅是非辉格的、带有历史和社会等多向度属性的,也不仅仅向我们表明甚至文学创造都可能是科学活动的一种模式,它还启示我们:对科学史的理解既不应是一种史学旨趣,也非一种哲学阐释,更不是一种社会建构和文学创造,我们或许也不能把科学仅仅看成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和知识体系——说到底,套用时下“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时髦说法:科学就是科学史,科学是在认知中被把握的它的时代。
如果仅仅把《地外文明探索研究》的工作理解为替科学史扩展了一点研究范畴,我觉得很可能还是将事情想简单了。事实上,扩展研究范畴的努力,在当代国外的科学史研究相关成果中并不罕见,在国内,这样的努力虽然不多,但对于扩展研究范畴的想法还是容易理解的。忝为师兄,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穆姑娘这个师妹,我发现她的一系列研究,至少是为科学史开拓了一段新边疆。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站在这段新边疆上,放眼前方,江山万里,她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前进阵地。
举例来说,她因为研究科幻作品,开始注意到《自然》杂志(Na⁃ture),遂有“Nature实证研究系列”之作,而这个研究系列简直就是“科学史=科学+X之历史”的示例之作:
在热身阶段已经有《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Nature与科幻百年》(海豚出版社)这样的奇妙书籍问世。而为了突显这些受到媒体“宠爱”的成果背后有着强大的学术支撑,又有《新科学史:科幻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这样“高冷”的学术文集出版。然而她的“炮火”不久又从《自然》杂志延伸到了“影响因子”(因为《自然》杂志是“影响因子”游戏的顶级玩家之一),近年她一系列关于“影响因子”的重磅文章,让她俨然成了“影响因子”问题的大权威。
如果我们将上面说的“新边疆”比喻为一片猎场,这片猎场中人们原先只用长矛和弓箭狩猎,那么穆姑娘就像一个高调的闯入者,她近战有冲锋枪,远袭有狙击步枪,几乎颠覆了这片猎场中的游戏规则。重要的是,她使用的这些枪械,全都是“科学史牌”的——她在进入这个前进阵地的过程中得到了这些武器,并学会了熟练使用它们。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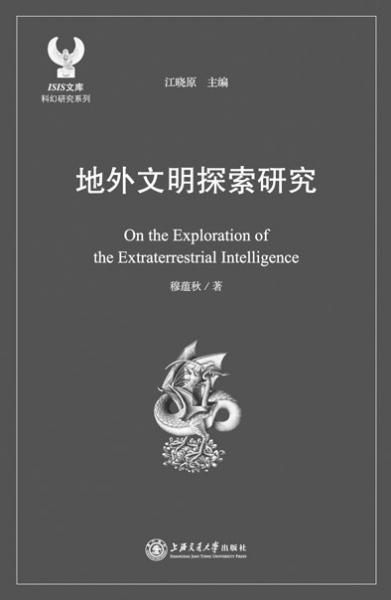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