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国学很热,却是虚热。热的主要是小术、小道、小学。小术方面,如算命打卦、中医中药、古乐古戏、书法国画等;小道方面,如修佛、学道等;小学方面,如一些机构教人读三字经、弟子规等。
大家当然知道国学的核心是儒学,许多人主张读经,但他们有种奇怪的观点,认为读经就应该读纯正的先秦原典,回到孔子那里。
其实,这是一种误判。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打“孔家店”,实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他们按理当时应该直接打“朱家店”,因为孔子毕竟远了,当时笼罩神州大地的思想学术,是经过朱熹、王阳明等人改造过的新儒学——理学。
理学自南宋理宗时代入官学,经元、明、清三代,至民国已历近七百年。期间,有约六百年的时间,朱熹注的经书,是朝廷科考指定的唯一教材,其受崇奉及影响社会的程度可想而知。
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不直接拉朱夫子出来批,反而去找两千年前的孔夫子的晦气,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他们认为,“孔家店”是理学的总后台,拆了总后台,朱熹的前门店自然也会跟着倒塌。
另一方面,直接提打倒理学他们底气不足。
他们否定儒学的缘由,是判定儒学已经腐朽了、僵死了,成为了中国社会拿来西方科学与民主制度的障碍。但是,这种话他们不敢公开说出口。
当时他们不能不顾虑这样两个事实。
一是清末曾国藩、左宗棠等一班理学家,不仅奋起镇压太平天国,中兴了清朝;而且还积极发起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他们虽然最终没能挽救清朝的败亡,却足以证明理学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相互排斥,理学家并非都是冬烘先生。
二是在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王阳明的格心派理学发挥了极重大的作用,陈独秀、鲁迅等人在日本留学,是亲眼目睹了的。日本人的成功,足以说明,理学既可与科学兼容,也可与现代的政治社会制度相兼容。
因此,民国初期的激进派人士便达成了一种默契,彻底批判传统文化,却不公开点名批判理学。
新中国建立后,理学虽被定位为唯心主义,却很少被大张旗鼓公开批判。因为假如要公开批判某种学说,就必须研究它,而只要有人肯用心去研究理学,就难免会上朱熹、王阳明的当。所以,对付理学的最高明办法,是先将之歪曲,然后“默杀”之。事实证明,这种先歪曲后“默杀”的策略极为成功。
先秦儒学不很完善,也可以说比较原始。儒学讲究内圣外王,先秦儒学着力解决外王问题,内圣部分虽做了不少努力,却没有形成闭环。
宋明理学是对先秦儒学的完善与补充,到朱熹手里,儒学才真正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论体系,且将内圣与外王有效贯通了起来。
因此,现代人假如不懂宋明理学,而只读先秦儒家的原典,根本不可能全面领会孔、孟的微言大义,或者说很难读懂。
许多研习者有这样的体验:一本《论语》《尚书》精读下来,揣摩很长时间,不过得些片言只语的启示,整体上却一片混沌。
什么原因呢?一是因为现代人普遍欠缺小学功夫,对古文有些隔膜,且与古人的思维方式不对接;而最重要的是,经书的内容本身有些杂乱,缺乏逻辑性,因此找不到头绪,感觉就像面对一筐散乱的珍珠。
另一个方面,孔、孟、荀当时言及政治及社会礼法制度的言论较多,谈论人生的学问虽然也不少,且基本具备了理论体系的雏形,却仍相当隐晦不明。因此我们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上,听孔夫子等人站在封建宗法社会的立场上讲话,难免会被儒家的外壳所眩,而忽略了它内里的真精神,从而满腹疑虑,产生出许多疑问。
所以,将先秦儒学与理学撕裂开来,只重视先秦儒学,而忽略宋明理学,是我们现代对待儒学的一大误区。没有理学,儒学是原始而残缺不全的。也就是说,理学包含了先秦儒学;而先秦儒学不完全包含理学。
读西方的学术著作,大致总能找到它们的思想线索,把握其脉络,甚至能看出一个清晰的思想理论体系;可是读儒家经典,却找不到这种感觉。据此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圣人不善于线性的逻辑化思维,他们受《周易》的影响过重,习惯于用“类比”的风格说话;因此,儒家的思想是散乱的、涩晦的,不可从整体框架处理解,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次序构造。
这种看法纯属一种偏见。
儒学从一开始发展,就有一定的次序与线索,只是因为它过于精深博大,中途遇到困难,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线索隐断,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到宋朝时,儒学发展到了理学阶段,那条中断的线索又被重新寻出,发扬接续,终于在朱熹那里贯通内圣与外王,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
这个庞大而细致的儒学思想框架虽然尚不够完善,但它隐然有明晰的逻辑次序;相较而言,它可能比康德、黑格尔等西哲们的思想还易理解。
有一些人虔诚地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抱怨说读不懂。我告诉他们读不懂就对了,瞎子摸象怎可知道什么是象?因为读王阳明不能不读陆九渊,读陆九渊不能不读朱熹,读朱熹不能不了解北宋五子,了解北宋五子不能不读孟子,读孟子不能不读《大学》、《中庸》与《论语》。
王阳明处在儒家学术的下游,他的许多话都是针对上游而说的;所以关起门来读《传习录》,读不懂正常,即便宣称自己读懂了,一般也是假懂。
同样,《论语》也是一本被热读的儒家经典。《论语》表面文辞简浅,实则几乎每个字都有深意,所以从中读出点“心灵鸡汤”类的感悟容易,而要读懂其大义则难。
如果单纯读《论语》,只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要想深一步,达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需要下很大的工夫。当然捷径也有,那便是从理学入手,只要理学熟了,就能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而如果再进一步,理学通了,就能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王阳明当年龙场悟道成功,自言回味圣人的言论,与自己的体认无不契合,便是达到了这种境界。
《理学的脉络》,安鲁东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定价45.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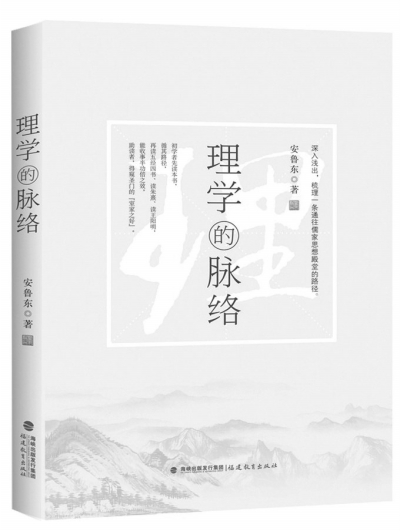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