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十八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不仅发生了两次震撼世界历史的大革命,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理论上经历了人类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脱胎换骨,使西方的人性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而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层次。直到今天,这一层次还是西方人日常政治和伦理生活中所奉行的公认的价值基础,不论他们如何对这一启蒙立场进行反思、纠正甚至批判,都只不过是这一立场的精致化,也是这一立场本身内核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传来的这种思潮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习惯于零星地撷取其中的个别命题和口号来为我所用,而很少去系统地追溯其中的来龙去脉,去关心这些思想在理论和现实的方方面面的矛盾冲突中是如何艰难地成形,以及在运用于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时所带来的成功或失败的后果。在一个全球化日益深入影响到每个文化的内在原则的时代,我们实在应该对西方文化的根基来一个正本清源的追溯,否则很可能当我们对西方文化自以为耳熟能详的时候,恰好隐含着根本性的误解。
现在,因应这一需要,由英国学者马克·戈尔迪和罗伯特·沃克勒主编、刘北成等人翻译的《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分为24章,每章一个主题,分别由24位欧美名牌大学的学有专攻的学者撰写,并按照每四章一个板块的比例整合成六大部分,即“旧制度及其批评者”“新的理性之光”“自然法学与立法科学”“商业、奢侈和政治经济学”“促进公共幸福”“启蒙与革命”。书后按照西方学术规范附有大量的参考文献和40多页的人名索引,更为特别的是有一个80多页的“人物传略”,几乎相当于一个18世纪风云人物的小辞典,全书总字数接近100万字。通观全书,可强调五大看点。
看点一
本书非常看重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纵深的历史感,这和孟德斯鸠的罗马情结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有关。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等著作中处处都穿越到古代的政治经验中去寻求一般政治体制的运行法则,但这和英国人对待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习惯还不太一样,而是具有某种世所公认的启蒙意义,这种意义在《法的精神》中得到了体系化的表达。英国人向来对法国人不大瞧得起,对伏尔泰的无条件的恭维还颇为享受,但在孟德斯鸠那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水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获得了一种跨文化跨历史的视野(参看第319-322页)。这一视野正好为后来的美国脱离英国独立以及立宪建国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参看第76页)。本书对这一思想传承关系揭示得非常详细,很值得读者玩味。
看点二
本书并非抽象的政治理论的梳理,而是与十八世纪的政治事件和经济活动紧密相联,并考察了在这些事件和活动中思想者们的思想动态和思想冲突,以及这些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来源和所造成的结果。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的政治体制还非常粗糙,除了对王权的根本性的限制外,其余一切都处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中,洛克的《政府论》是直到18世纪才得到广泛的宣传和认同。而最终确立的英国体制实际上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并带有习惯法的那种不自觉,虽然在理论上并不能自圆其说,甚至遭到一些理论家的批评和嘲笑,但它确实行之有效地保证了英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参看第330-331页)。相比之下,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背景要比英国革命浓厚得多,以百科全书派、自然法学派以及社会契约论为旗帜的启蒙运动为这场政治革命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法国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中止理论的探讨,而是在康德开创的德国古典哲学中为法权哲学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但本书第12章的作者认为在黑格尔以后,社会契约论走向了“衰落”(第359页),这就未免太忽视了理论的生命力。作者在宣布了“契约论的死期”之后,把美国革命的成功归之于“一种相当守旧的洛克主义”,并对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契约论的复兴感到意外(第361页)。其实,对于卢梭的“公意”学说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正是在美国革命的“摸石头过河”的尝试中得到了最好的实践和运用,按照本书第21章的说法:“美国人的宪法观念已经变得与英国人大不相同。宪法不再被视为政府的一部分。宪法是一个不同于并先于全部政府运作的书面文件。”如托马斯·潘恩所说,它如同《圣经》一样,是“一个先于政府的事物,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第585页)。这应当视为社会契约论的升级版,它构成了罗尔斯《正义论》的出发点。
看点三
本书在讨论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时,还广泛涉及了当时的宗教思想、文艺作品和大量的时文,因为在作者们看来,“18世纪政治思想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话题,有一些是需要在那些或许更具历史重要性而非哲学重要性的作品中加以探究”(第7页)。天主教和新教、英国国教和非国教、耶稣会士与詹森派、正统路德派与虔敬派的冲突时时伴随着政治主张的风起云涌(第109页以下),甚至教士们也来宣扬社会契约和人权了(所谓“天主教启蒙运动”和“虔诚的启蒙运动”,见第125、130页);反之,廷德尔等人和卢梭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提出了建立“公民宗教”的设想(第55、87页)。本书的一个假设是,情感的上帝使得英格兰倾向保守,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乱局,而推理的上帝则导致了政治激进主义(第141页),假设是否恰当,还有待考证;但文学、戏剧、诗歌、漫画、音乐等等都成为了政治斗争的手段(参看第72-73页),这似乎的确构成英国十八世纪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
看点四
本书虽然主要由英国学者所撰写,但仍然努力扩展自己的视野,除了英国(包括苏格兰)外,还广泛涉及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甚至俄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反复提及并论述的又主要是法国思想家的观点,特别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观点。在比较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时,作者指出前者是文化一元论者,认为所有民族都应该向英国的政治形式看齐;后者是文化多元论者,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与自己相适合的政治形式,没有什么好坏之别,如“日本由法律统治,斯巴达由风俗统治,中国由礼仪统治”,而“英国最擅长如何将宗教、商业和自由结合在一起”(第154页)。休谟则认为,正是因为“在商业和制造业使人类理性变得优雅精致之前,法律、秩序、治安和纪律不可能得到完善”(第162页),所以英国和法国是最文明最优雅的社会。但本书(本章)的作者似乎更倾向于孟德斯鸠的多元论,并针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指责为孟德斯鸠辩护,认为他“拒绝了环境决定论。他认为道德原因比自然原因重要”(第155页)。作者还以赞赏的口气说,孟德斯鸠在一些关键之处“就英国社会和中国社会进行持续的对比。一个欧洲政治哲学家在其主要论著中如此行事,这是前所未有的”(第156页)。一个几百年来都以最好的社会制度和天然的殖民者自居的国家的学者,能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并将“历史进步论”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第194页以下),这种风度本身就值得敬佩,虽然理论上并不一定站得住脚。
看点五
本书对西方近代政治理论中一些最重要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里且举几个例子。首先是“自然法”的概念。书中对自然法的起源未作过多追溯,但强调近代自然法观念起于新教以自然的信仰代替天启的信仰(第241页),而自然的信仰则基于人的自由意志。这就带来了自然法的一个矛盾,即一方面,“意志的运用乃是人的自然特性”,自然法就是自由意志的法;另一方面,自然法被看作有意志的人类在历史中通过传统习俗发展出来的产物,因而是个人意志必须服从的上帝意志或历史规律。(第242-243页、253页)这一矛盾又发展为权利与义务、法学和伦理学、法律与道德、正义和善、理性与情感的分离。自然法究竟是一种伦理规范还是一种因果关系?这一矛盾直到康德才有了一个解决。“康德学派对自然法的占领,可以说是本章一直在说的两个‘学派’或直接或间接的遗产继承者之间长期斗争的结果。……其中核心的变革是把关于‘自然法’的形而上学转变为关于‘自然权利’的形而上学”(第269页)。或者说,明确地从“自然权利”来理解“自然法”就是从康德开始的,这也就一劳永逸地把自然法与上帝的意志区别开来了。而这一点是苏格兰的那些学者(卡迈克尔、哈奇森、休谟、凯姆斯、斯密等)单从自然感觉和感情出发所不能理解的,斯图尔特甚至最终觉得有理由宣布自然法的死刑(参看第10章)。
另一个概念是所谓“三权分立”或权力制衡的概念。这是从上述自然法概念中推导出来的一个相关概念。孟德斯鸠通过对英国宪制的分析发现,所谓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体”,表面上是脱胎于罗马共和国及英国“大宪章”以来的习惯法,实质上却体现了近代分权制衡的政治理念,即君主的行政权、两级议会互相制约的立法权,加上陪审团和巡回法庭所体现的审判权(司法权),三权分立,这正是自然法的因果律所要求的技术性设计。这一解释得到了英国人的热情拥护和普遍接受,并在英国后来的政治体制的运作中得到了自觉的运用。(参看第322-325页)
再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的概念。通常认为,孟德斯鸠不谈社会契约,而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反对三权分立,认为这就像把一个人的肢体大卸八块,是对国家理念的误解。但本书第20章却指出:卢梭“与孟德斯鸠一样,认为国家必须实行分权,主权者永远不能拥有实施自己制定的法律的权力,而政府也永远不能拥有立法的权力”(第554页),这是很有眼光的。实际上,卢梭只是在“公意”的层次上反对主权的分割,而在“众意”的层次上则主张分权制衡,因而与孟德斯鸠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他对孟德斯鸠不满的只是“把仅仅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以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同样,卢梭所谓公民权利“不可代表”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因此该章作者也指出,卢梭实际上并不反对“那种委任性的、可任意解职的代表体制”(第555页),正如康德表明的,既然承认了分权,那“就要求政府必须是代议制的”(第568页)。这些说法有根有据,颠覆了一般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表面看法。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可能把书中的看点全部列出来,最后只想告诉读者,谈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第21、22两章太精彩了,不可不读,最好对照着来读,你就会知道法国革命的失败和美国革命的成功(这本质上是一回事)在哪里。
本书不太令人满意的是,对康德的政治哲学的介绍显得简单了些,而且不是很准确,对贝卡利亚的刑罚理论的分析也比较表面(可对照一下黑格尔的分析)。作者们(除个别外)似乎更倾向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缺少哲学家的思辨性。不过本书能够做到这样,已属不易了,不必过于苛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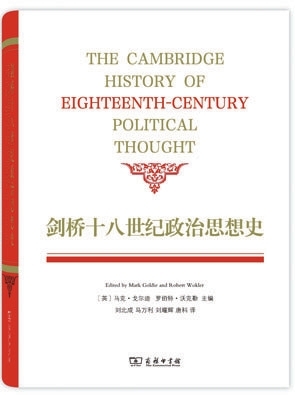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