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闻先生幼时师从前清遗老、书法家李健(1881—1956,前清两江师范总督李瑞清之侄),少年时代就举办个人书法展览,已经是海上声名斐然的艺术才子,翻看1948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年鉴》就会读到有关他的记载。上世纪40年代末他负笈赴美留学,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乔治·罗利。从1958年至2000年,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桃李满天下。期间一度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的主任,70年代起兼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部特别顾问部长,始终协助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和大都会博物馆,致力于系统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展览和研究,成果斐然。自他荣休以后,一直表示要使中国艺术史这门学科在国内生下根来,便相继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筹建中国艺术史研究所和考古艺术博物馆,从设计馆址、网罗人才、安排课目,到捐助资金,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他提出“中国书法与绘画史研究,能够为中国文化思想史提供更有深度的洞悟,并可以使得传统西方艺术史学得到一种多元性艺术史的借鉴”。而且,“不同的视觉语言拥有不同的民族文化意义,为获得一个可以观照不同艺术史的公共视野,我们因此需要一套共同、适时的现代分析和诠释工具。这些方法或许最初形成于西方艺术史,然而,随着当前非西方视觉作品的研究,它们已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补充”。也就是说,要摒弃西方中心的逻辑,从具体的历史遗存的艺术作品入手,通过分析比较的方法,讲述中国艺术本身的故事,重建一门中华文化史论说。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兼备了中国国学与西洋艺术史方面的深厚底蕴,方闻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著述,先后荣膺美国哲学院院士(1992)和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1993)称号。二十年前我曾在翻译《心印》时介绍说,方先生的这部著作,就是围绕“视象结构分析”的基本思路,“来鉴定古代书画作品的真伪、断代定位与艺术风格分析……同时又密切联系与作品相关的社会背景,由浅入深、博引旁征地从当时政治、哲学、文学等思潮中寻绎艺术风格演变的历史依据”。因为书中的字里行间,都是具体艺术作品的解析,从笔墨、布局到空间、图式,简直须臾不离开实际的历史文本——具体书画作品本身,而根本读不到抽象的方法演绎。联想方闻先生那一句口头禅:“作品不会讲假话”,充分显示出他从事这份专业研究的自信心。
鉴于方闻先生的师承以及研究特色,加之普林斯顿大学的地理位置,习惯上常被称为美国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的东部学派,以风格分析著称,而与偏重于社会学方法做艺术史的加州伯克利大学高居翰教授为代表的西部学派相对。有关与高居翰先生的关系,方闻先生说他们从50年代初相识以来,两人一直是最好的朋友,“更贴切地说,应该是战友——共同让西方学术界及一般大众有了更多接触中国画的机会”。他佩服高居翰的美文,称赞那是善于将目之所见转为文字的写作天才,作文雄辩滔滔,洞见层出,甚至“天生是个文字导向的人而不是影像导向的人”。他们两位连续不断“公开讨论”的有关中国艺术史的学术问题,从早期中国山水画的特征到中国诗、书、画的相互关系;从董其昌的画史意义一直到《溪岸图》的真伪……事实上,只要认真阅读方闻先生的著作,就会发觉上述那种笼统的“两分法”的弊端所在。
在通常人们认为的人文学科当中,艺术史研究如何才能作出它特有的成果来?换而言之,在学术研究的普遍规律中,如何使我们的工作更能凸显艺术史学科的独特性?这里面,要注意的可能有许多,但有一点大概是基本的:即它必须与历史上的物质文化、视觉资源密切结合。同样属于人文学科,艺术史研究与通常思想史、历史学不同,它往往不是从纯粹观念的、文献的条条框框出发,而应从具体积淀着不同时代人们思绪、意识或者理念的人造加工制品(无论是一件书画、陶艺或者一幢建筑)入手,寻绎其中相关联的征象、因素及背景,探究其形成、演变与融合的诸多要素或机制,最终重建起自身艺术发展的历史故事。所以,方闻先生经常提起,他写那些文章,就是用不同的图片述说同一个故事:讲述中国艺术史发展的一套叙述方式,由再现客体至表现自我。所着眼的是中国书画对于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所提供的视觉证据。
因此,这种对于视觉图像资源的敏锐感觉,这样一种做视觉历史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学术基因,来自于方先生本人的大学基本训练。方闻先生回忆自己在普大时,学校正是欧美中世纪艺术史学的中心,他受教于著名西方中古艺术史专家克特·魏兹曼教授,后来到艺术考古研究所当研究生时,他的导师乔治·罗利首先也是此中的专家,写过有关14世纪锡耶纳画家A·洛伦采蒂的专著。罗利收购保存了大批中国汉代至18世纪的石刻拓片、照片及参考资料,并建有远东艺术专题研究室。后来撰写过《中国画的原理》(1958)。他“是第一位教我用现代观念来理解‘风格分析’的老师”,方闻先生意味深长地说道,“这种风格分析是反映个人‘观看’的方法,是一种生理结合心理的视象化活动。成功的风格分析必须注重‘视觉历史’与‘时代分期’”。基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经验,方闻先生提出:要充分运用存世的艺术品和考古发掘的文物,来支持文献学,作为现代艺术史研究的双重证明,才能完成重建中国古代艺术史的重任;而且要从具体的语汇诸如线条、笔墨、块面等物质性图像入手,分析每件书画作品视觉上的机制、结构,才能做好鉴真伪、辨优劣的基础性工作。他本人如此重视历史上视觉图像的资料、数据库积累,重视大学美术馆建设类似理工科“实验室”的功用,其意义皆不外乎此。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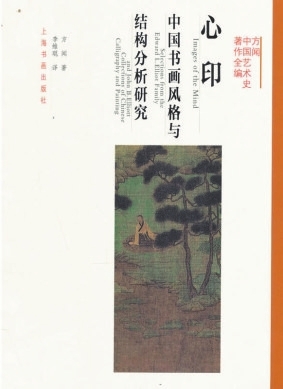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