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的书有点门槛,读进去却非常有意思。譬如他这本小说,叙事速度非常快,几个动作,或者只是一个照面,内心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
大约十四五年前,我住在大学的宿舍里,有个朋友常在下班后找我玩。说是玩,其实他来了便往我的铺位上一躺,一言不发,直到夜深了他回自己的住处睡觉。我则在电脑桌上继续看自己的书,不用因为自己的怠慢而感到愧疚。有一天晚上,他来到宿舍,在照例躺下之前,丢给我一本皱皱巴巴的杂志,跟我说,你读读上面的《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那天晚上破例,我跟这个从来不谈文学的朋友谈到很晚,从理想主义谈到虚无,以致要到室友出言提醒,才知道我们已经聊到很晚很晚了。
那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薛忆沩是谁。在那次谈话之后,我也只在阅览室的往期杂志上,找到他零零星星的几个短篇,《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首战告捷》《出租车司机》。后来,忘记从哪里获知他有一个长篇《遗弃》,便到处寻找。学校图书馆遍寻不获,后来是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不知是不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反正那一版《遗弃》,留在我脑海中的印数是两百册。
回想起来有些奇怪,那个跟我聊薛忆沩的朋友,很少关注虚构作品,他更关心的是时政和经济,满心揣着的,是家国的大事,不知怎么就跟我谈起了薛忆沩。照理,薛忆沩的小说是属于最本质上的虚构一类,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乔伊斯的传承,跟所谓的家国之事好像没什么直接的关系。长篇《遗弃》则更是一个玄思式的作品,除了能从中看出作者的思辨深度,实在读不出跟时事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是什么吸引了那个朋友呢?
我毕业之后,又过了六七年,到了一家文学批评杂志工作,想起了朋友对薛忆沩的推崇,就让他写一篇评论文章来。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文章终于来了,在关于薛忆沩不多的评论文章中,显得非常突出,我也由此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喜欢《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他关心的现实和家国之事,与薛忆沩虚构指向的某些东西,居然内在有密切的关联。从这里大概也不难推测,薛忆沩居然用虚构的形式,对准或者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核心秘密,从而在远较小说技艺广泛的领域,产生了独特的共鸣。
仍然是在杂志工作的时候(我现在还是在这里工作),忽然收到了薛忆沩一组题为“与马可·波罗同行”的文章,解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文章发表不久,就有师友赞叹,说文章写得好,其间思维之复杂、构想之精妙,对一些问题的洞见,几乎构成了思想的多维景象,显示其绝非凡品。因为这批文章,我把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找出来对照着看,并没有从原作中获得太多高于解读文章的东西。我因此得以推断,薛忆沩应该是极为杰出的阅读者——如果《看不见的城市》是个起点,薛忆沩是个高点,说明薛忆沩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卡尔维诺;如果《看不见的城市》隐含更加高明的东西,普通人很难识别出来,那薛忆沩就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引路人。
薛忆沩喜欢重写自己的作品,不管是前面提到的《遗弃》《与马可·波罗同行》,结集为《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的随笔,还包括为数不算少的中短篇,无论是结集还是未结集的,几乎都经历了被他自己重写的命运,有些作品甚至就此从中篇变为了长篇。或许对薛忆沩来说,对作品一字一句的改动,都牵连着他对整个世界的认识,那热病发作式的、洁癖重症患者似的对文字的改动,都是他在调准自己对时代的认识,仿佛错下了一个字,瞄准的箭矢就会失控,有了脱靶的危险。
当然,薛忆沩绝不只是在重写旧文,否则他就有蹈袭自我的嫌疑不是吗?2014年,薛忆沩出版了长篇新作《空巢》、随笔集《献给孤独的挽歌》,2016年,则有《希拉里、密和、我》问世。如果说《空巢》显示了薛忆沩对题材的敏感,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回应了时代的某些问题,《希拉里、密和、我》则充分展示了薛忆沩在虚构上的出色才华。
从《希拉里、密和、我》的开篇,你能闻到熟悉的卓越虚构作品的气息。一个移民加拿大的中年男性,老婆刚刚去世,女儿搬离了他,并不再跟他联系。韩国女孩出现,把他带到溜冰场,并就此结识了两个行为独异的女性,她们各有着自己深受的伤害和无法言明的心事。小说开始的时候,叙事腾挪的空间很小,但小说对叙事者自身之外的人的想象,丰富,复杂,细微,精确,充满狂想意味。我很久没有看到过了,一个写作者在这么小的可能里把细节填充得这么饱满,类似于秘密空间游戏,对方的心思不打开,你只能去猜想,把每一个心灵角落都尝试着探索一下,看看能出现什么。有时对方只是一个无意的动作,却会引出一段长长的想象。
薛忆沩的书有点门槛,读进去却非常有意思。譬如他这本小说,叙事速度非常快,几个动作,或者只是一个照面,内心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薛忆沩对叙事节奏的把控,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是用过心思的,可以仔细琢磨。或许正因如此,薛忆沩的写作具有典型的节制特征。他的文字从不铺张扬厉,而是把情感和行为都控制在含蓄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因此叙事上少见有溢出的部分,虽然每个细节都充分伸展,有着狂乱意味,总体却细腻,紧致,密不透风,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楔进叙事的缝隙。不难看出,这些叙事既有现实的蛛丝马迹,却早就经过了薛忆沩机械般精准的虚构加工。
有些写作者会到一定时候放弃对人物的管控,任他们按自己的性格逻辑发展下去,看看他们会走到什么地方。另外一些写作者,如纳博科夫,则决不允许人物失控,每一个细节都须经过精密的设置。薛忆沩无疑是纳博科夫序列的作家,在阅读时就几乎可以断定,《希拉里、密和、我》的整个流程,都是在他心里细细密密走过一遍的。即使人物共读莎士比亚十四行部分,本可以展示他自身杰出阅读才华,薛忆沩也让它完全符合人物自身的逻辑,这部分就不仅是知识传授,也传达着人物的性格,推动着故事的进展。
在薛忆沩身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生于湖南的他,似乎回到故乡和曾经居留的深圳,就是地方作家;一旦到了北京或上海,人们谈论他的时候,他就是全国性作家;等他去到蒙特利尔,接受各路国外媒体的采访,就又成了世界性作家。这原因,或许就跟他上述的虚构方式有关。相对于虚构传统悠久复杂的欧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虚构充满误解,不是认同为胡编乱造,就是只认可放手让人物自己活动的那种。其实,虚构是对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无论怎样的虚构,都得是一个完整的自洽世界,运行逻辑出错是绝不允许的。薛忆沩的虚构方式和对文字的克制,让他在很多时候不容易辨认。他严密的虚构世界运行逻辑,要求这一种极为细微的鉴赏力,这对很多人来说太过严厉了,得不到更为广泛的认可,本就应该是他写作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为这严密的掌控,我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偶尔会为薛忆沩担心,觉得如此多的细致心思和细微心事,像是充分燃烧的火球,不小心就会耗尽人的耐心和体能。好在,我在《希拉里、密和、我》的后半部分,看到了放松的可能。小说开头的时候,“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完全绝望,完全孤绝地立在尘世上。偶然出现的女孩带来另外的偶然,已绝望至将死的世界复活,“我”又开始慢慢打开了自己,并有了结尾处的新生活。就这样,薛忆沩用一本小说,既完成了对希拉里与密和的安慰,也完成了对“我”自身的治疗——没错,好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就是这样,既是对外在世界的治疗,又是自我的治疗。我相信,薛忆沩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慢慢放松下来,完成了他的自我治疗。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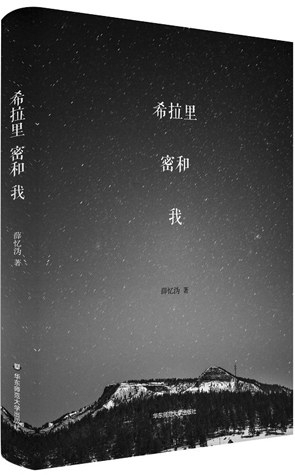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