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商务印书馆百年资源部编印的《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上纪念吴泽炎、高崧等老领导的文章,我深受触动;又忽发现《馆史资料》的“顾问”名单中居然有我,更感到惭愧和激动。余何人斯,敢承此任!作为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读者,我不过对商务的历史和历史上的若干著名人物略有一点研究而已。但我有幸也可算是商务的一位作者,因为曾在商务出过一本不薄的书,而且还出了两次,从而与商务的几位老领导、老编辑有过接触。这些老领导、老编辑是我的恩人,而且他们也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了,我非常怀念他们!
最早认识老编辑唐锦泉先生
我最早认识的商务老编辑是唐锦泉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唐先生好像已到退休年龄,但被返聘做馆史资料工作,编辑《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记得当时还是打字油印的。那时唐先生与我都在上海的《出版史料》杂志上发表文章,大概是由《出版史料》主编宋原放先生的介绍,我也收到了油印的《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还为它写过稿。1985年我去北京读博士研究生前,赴京出差时就曾拜访过唐先生,1985年后在北京师大读书三年期间更是常去拜访他。唐先生非常热情,曾提供馆藏的一些珍贵史料给我看。
吴泽炎先生支持拙作在商务出版
我最早认识的商务老领导是吴泽炎先生,当然是由唐先生介绍的。查自己当年的笔记:1986年5月6日,我收到唐先生的信,通知我说吴先生想见我。我知道,吴先生是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记得当时商务没有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而且还是我平时请益最多的《辞源》的主编。他老人家怎么想要见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呢?
第二天,我赶去商务,由唐先生带去拜见。吴先生应该比唐先生年纪还大一点,平易近人,和蔼慈祥。原来,吴先生不仅注意到我在《馆史资料》上发表的小文,而且在报刊上也看到几篇不足道的拙文,所以就向唐先生打听我,并招我去面谈。当时吴先生好像已退居二线,馆史研究一块正是归他负责的。他认为我这样的博士生,对商务馆史又有所了解,是商务所需要的。他找我去谈话,就是想请我毕业后去商务工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也曾在上海的出版社干过,也很喜欢编辑工作,但说实话,我更想去大学做研究工作。而且,我父母年纪大了,都在上海,也盼望我回去。我吞吞吐吐说了这些,等于谢绝了老人的好意,但看他并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我又说了一个相当粗鄙的理由:回上海去大学工作的话,可以优先分配住房(当时的博士还是比较“稀有”和“值钱”的)。吴老同情地说,这点对年轻人来讲,的确很要紧啊。在我们商务,这方面比较难解决。吴老和唐老都讲上海话,我真感到一种父辈的温情,初次见面也没有什么拘束感,倒是唐先生,在吴老面前始终毕恭毕敬。
吴老又关切地问起我毕业论文写的什么题目,我说是郑振铎研究,并介绍了在撰写中的毕业论文的内容。不料吴老特别感兴趣,高兴地说,你写好后可以在我们商务出书啊,并当场就指示唐老,这本书就由你来做责编吧。唐老则连连称是。这更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郑振铎先生曾在商务工作过十年,拙书稿中也涉及不少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内容,但吴老肯定拙书稿的价值,显然绝不仅仅因为这些。他对郑振铎研究的意义的高度认可,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我的惊喜和激动可想而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写好,就如此“得来全不费工夫”地有了出路,而且还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国际第一流的出版社。
回到学校,我也不敢对老师和同学说。一是因为其他同学还没有开始撰写论文呢(我写得比他们快);二是我曾在出版社干过,知道出一本书要经过许多关口,吴老虽是副总编,但毕竟已退居二线,不知道他这样当场做的决定最后当不当真。
吴老当时已70多岁了,不是每天到馆,因此我与他老人家见面次数并不多。据自己的笔记,这年12月22日,我去商务又见到吴老,谈到我的毕业论文事,他再次肯定商务可以出。1987年5月18日,我在商务第三次见吴老。最后一次见到吴老是1988年12月中旬我赴京参加筹备“全国首届郑振铎学术研讨会”时。16日我去商务印书馆时见到了吴老和唐老。此时,我在吴老的激励下已将博士论文认真地做了修改,最后成稿字数扩增至48万字,取书名《郑振铎论》,于是年4月即托朋友带到北京,交给了唐老。这次见面,唐老告诉我,拙书稿正由吴老在审读。我人生的路走得很不顺,但蹉跎中偶尔也遇到过好人拉我一把,吴泽炎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好人,而且,还是在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之后。我将永远怀念他!
拙书的责任编辑唐老,是非常朴实、非常认真的一位老编辑。他看稿子非常仔细,加上年纪大了,当然看得很慢。唐老又非常谦虚,认为自己在古典文学方面不精通,所以又将拙书稿寄到上海,分出商务给他的不多的审稿费的一部分,以个人名义再请另一位早年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后调到中华书局工作),比他还年长的退休在上海家里的金云峰先生审读把关。金老也非常认真,又看了很长时间。我那时心里其实很焦急,总有点担心“夜长梦多”,但也不好去催。最后,两位老编辑都给予拙书稿以好评,我感到极大的欣慰。由于两位商务老编辑的认真把关,使我避免了不少差错。
后来有一件小事还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拙书稿中引用了郭沫若早年一句话:“我常想天才底发展有两种Typus:一种是直线形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唐先生来信问我,应该是Types(类型的意思)吧。可见他连一个字母都不轻易放过。我没学过英文,查了词典,确实是Types,也就照改了。但后来,我才知道郭沫若没写错,那是德文。可惜我得知这一点时,唐老已经逝世,我已无法告诉他了。拙书是在交稿三年多后才出版的。
高崧先生审读我的书稿
拙书稿不仅经过吴老和两位老编辑的审读,而且其间还有另一位商务副总编也审读过全稿,那就是高崧先生。高先生任副总编时,商务仍然未设总编辑,而他其实是主持全馆工作的领导。他竟亲自审读拙书稿,那是我在很偶然的情况下知道的。
1988年底,为纪念郑振铎诞辰九十周年殉难三十周年,“全国首届郑振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高崧先生也在百忙中代表郑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商务印书馆赶来出席。那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找到他的房间,不料他连这样的点滴时间都在抓紧看书稿。再一瞥,我更吃惊了,那厚厚的一叠不正是我的那部书稿吗(是他从吴老那里拿来的吧)!我很感动,请他注意休息。而他只是笑笑说,工作太多。看到他那么忙,样子也很严肃认真,我只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而关于拙书稿写得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出版,他一句也没说,我当然也不敢问。后来,我在看校样和修订后记时,也是写上感谢高崧先生认真审读的,但最后出书时却没有了,肯定是高崧先生把提到他的文字删去了。
而就在拙书出版的时候,1991年6月,高崧同志因积劳成疾,67岁就离开了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我的痛心可想而知!
杨德炎先生帮我圆修订《郑振铎论》之梦
因为我从事的研究工作涉及商务馆史和张元济先生等,又在商务出了一本书,所以后来我好几次应邀参加过在上海、海盐等地举办的商务印书馆的馆庆活动和纪念张元济的学术会等。在这些会上又认识了商务的林尔蔚、杨德炎等领导。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特别是杨德炎先生,又帮我圆了一个梦。那就是过了近20年,2010年12月,商务印书馆又替我出版了修订版《郑振铎论》。我在后记中写道:
本书一九九一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仅两千册,后未重印,早已售罄。我很希望再版,除了想作些增补和修订外,主要更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觉得,至今文学研究界有些人对郑振铎的无知或偏见,仍远未消除。随便举些例子吧,如曾有几个单位召开过专门研究“文学研究会”的大型学术会议,会议总结中却连郑振铎的名字也不提;曾有国家级博物馆专门集中树立“现代文学大师”的塑像,多达十几人(包括有当时还活着的人),但却没有郑振铎的影子;曾有专门称为民国时期文学“研究史纲”的书,举出的作家多至半百(包括一些成就不大或不全面的作家),竟然也没有郑振铎;等等。有一位以前从事鲁迅研究,后在国家文物局党史办工作的老同志给我写信,激愤地说:“郑先生为国家和文化事业做了那么多贡献,这样对待他太不公正了!”我也深为文坛上某些莫名其妙的成见、势力之强而感到可悲可气。无奈人微言轻,惟有希望通过拙书再版来表述管见,以引起一切有实事求是之心的人的思考。
二是十多年来,学术界有过一些热点话题,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撰著史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以及一些专题讨论,如一九二〇年代初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小说月报》的改革、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关于“整理国故”等。有的高谈阔论,令人畏敬;但我常发现,有些问题或史料在拙书中也曾写到,那些论者却似乎都没有看过,因而以重复为新见,谈不上超越,或者还不如拙书,甚至还发现连一些早已弄清的史实也还会搞错。这时,我便会想起明清之际张宗子《夜航船序》中“僧人伸脚”的故事。我希望再版拙书,也就是“且待小僧伸伸脚”的意思。
如今,商务印书馆再次帮我圆了这个梦。我对商务印书馆充满了无可言喻的感激之情!
为修订本的出版,我曾给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写过信,诉说自己希望重版的原因。我工作的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正是杨总的母校;我当时的邻居潘先生还是杨总的老师。潘老师说杨先生为人非常好,是他鼓励我直接给杨总写信的。这个我当然也知道。因为我在开会和会后参观时与杨总说过很多话,杨总也就比我大了五岁,圆圆的脸上老是笑容,那样的和蔼可亲。
我去信后,杨总因为极忙没有回信,但将此事交代给了总经理助理常绍民先生。2010年6月,我听说杨总生病了,正在上海治疗。我有他的手机号码,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中他的声音显得悲伤,说病情严重,并谢绝我去探望。不久,我从报纸上惊愕地得知,他不幸因肝癌而病逝,年仅65周岁!约半年后,拙书修订版在商务出版了。该书的后记是在杨总逝世前写的,我虽然在后记中感谢了杨总,但未能表达我的悲哀!
以上几位先生均已作古多年,写上这些,以代生刍一束,表达我的怀念之意。我在拙书修订本后记临末写道:
不知为何,忽然有一丝怆然的感觉袭来。人生蹉跎逾半百,不如意事常八九;但能在商务印书馆出这么一本书,我也知足了!
如今我已年逾花甲,感慨就更多了!
最后,我还想略微写写我认识的几位比我年轻的商务新一代编辑。首先当然是常绍民了。人家出书,都是作者请编辑吃饭;我倒好,每次都是他请我吃饭,还送很多好书给我。他老兄现在调离商务去别的出版社当领导了,虽然与他“失联”,但我很想念他。还有张稷、陈洁等编辑,都非常勤谨认真,我在她们身上都看到了商务老一辈编辑的精神的传承。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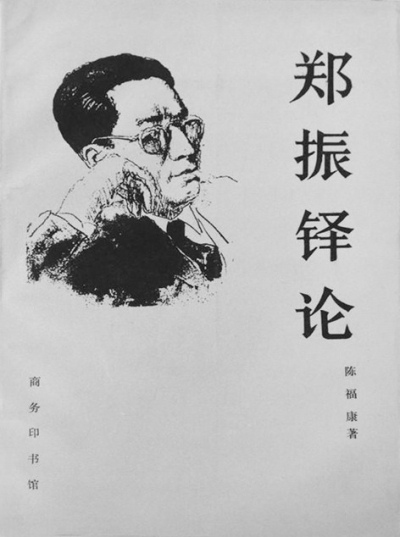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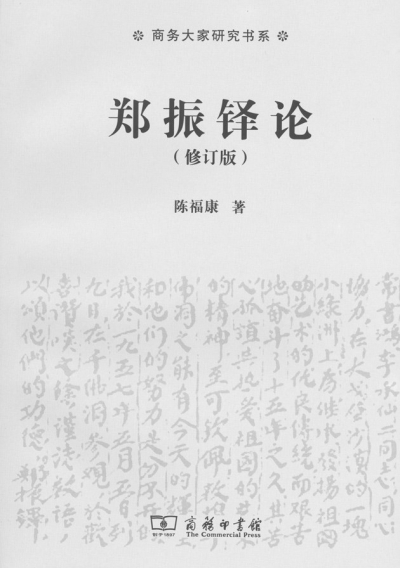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