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第十五辑出版了,其中包括我翻译的《沙乡年鉴》(下简称《沙乡》)。手握新书,不禁思绪翩翩。联想到《沙乡》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感慨亦多。
1988年,我将《沙乡年鉴》(以下简称《沙乡》)的译稿交与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先生——他曾编辑过我的第一部译作《现代美国妇女》,帮助颇大。邓先生看了书稿后将它推荐给了三联,因为他认为此书的风格与三联更为相宜。在三联,先因编辑出国而无故地被压了一年,接着又逢出版低谷,终因资助未能落实而被迫抽回。随后我又将此书交给了商务的一位资深编辑,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他觉得此书似乎更接近科学,因此将它推荐给了科学出版社。不想在审稿中,某位专家断言,本书原著出版年代过早(1949年),因此不宜出版!译稿被退了回来。我被这荒唐的结论弄得哭笑不得,却又无计可施。其实,也难怪,直至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利奥波德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
1990年冬,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年会上,我认识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的范国鹰先生,说起本书稿的遭遇,他当即答应协助,但同时又言,孔方兄亦不可缺。最终,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利奥波德研究专家苏珊·福莱德(SusanFlader)母亲的赞助下,此书才于1992年问世。
此书的难产甚至使我对它出世后的前途也充满了疑虑。在初版的后记中,我曾写道:“利奥波德的这本饮誉四域的名著终于要和我国读者见面了。奇怪的是,我却失掉了那应有的喜悦和激动。……好似一个难产后的母亲,我现在所感到的只是在听到婴儿啼声时的那种疲惫的欣慰,还有微带颤抖的忧虑。”谁能预测它未来的命运?我只得安慰自己,原著等了八年才得以出版(1941-1949)——比我等的时间还长!而且,它的价值是在十多年后——在美国环境保护运动兴起之后才真正被认识到的。我暗自希望,我的译著也会碰到原著那样的机遇——有朝一日,中国也将掀起一个波澜壮阔的环境保护运动。
我没有等到这样的时刻。不过,随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的召开以及我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我国国民的环境意识也在发生变化,尽管没有像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轰轰烈烈。1994年,中国的第一个非政府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成立,即是我国普通公民主动参与和关注环境事务的标志。在此期间,我还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都是谈他们读了《沙乡》之后的感想的。一位来自科学院自然史所的年轻人写道:“侯老师,你相信吗,正是在《沙乡》的感召下,我才变成了环境保护的‘发烧友’,并且加入了‘自然之友’”。他告诉我,《沙乡》已成为他的枕边书,如果几天不读它,就觉得自己变庸俗了。很快,我又听说,原来出版社担心积压的库存竟也告罄。于是,原在怅惘中的我,此时又窃生了某种期望。
1997年,《沙乡年鉴》被收入吴国盛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有了那种在初版时未曾有过的喜悦和激动”。(见吉林版后记)。这一版的社会影响显然大大超过了初版。尤其令人兴奋的是,本书的多篇文章都被选入了大学人文读本和中学语文教材。由此,在中国,利奥波德的名字已不再如初版时那样“鲜为人知”了。2009年,在九九读书公司的策划下,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沙乡》的插图本;现在,商务印书馆又将它列入到了汉译名著系列。这说明,利奥波德的这本书已在中国出版界得到了普遍认可;而商务印书馆将《沙乡》列入汉译学术名著系列的举措,又具有另种特殊的意义。
奥尔多·利奥波德(1887-1948),出生于美国衣阿华州伯灵顿市一个德裔移民的家庭。1909年,在获取林业硕士学位后,利奥波德成为联邦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并被派往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做林业官,在那里工作到1924年。
利奥波德在耶鲁读书和在西南部工作的时期,正值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兴起之时。这个运动的根本宗旨是,从长远的经济利益考虑,对资源要进行“聪明的利用和科学的管理”,以限制个人对国家资源的滥用和掠夺,使其在良好的管理下为全民所用。它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经济。因此,根据人的需要,所有的资源都被分为有用和无用、有利和无利的两大类别。这是保护主义的原则。这一运动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并得到了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广泛支持。
早年的利奥波德是资源保护运动的热情追随者,但是,在西南部的工作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1928年,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利奥波德脱离了林业局,转而从事他特别感兴趣的野生动物管理研究。1933年8月,他成为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一直到1948年4月逝世。
其间,1935年4月,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河畔购买了一个荒弃了的农场。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这个地方和它上面的一所破旧的木屋便成了利奥波德和他的一家——妻子和五个孩子在周末和假期可暂时逃避那“过分”现代化了的城市的“净土”。然而,利奥波德购买这片农场的动机,是想要了解为什么尽管政府提供着可观的贷款,而这一带的农民还要迁往他乡。他决意在这里进行重建的试验。
木屋经验对于利奥波德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正是在这里,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终于认识到生命与死亡、发展和停滞上的种种深不可测的因素,并形成了一种高尚的对待土地的谦恭态度。他深切地感到改变人们关于土地的概念的必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的大部分学生被动员上了前线时,利奥波德专心著述。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文学和哲学方面的文章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他力图在这些文章中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寻求树立人们对土地的责任感的方式,并欲通过它来影响政府关于土地和野生动物的管理方针。他的基本观点—土地伦理观业已形成。他渴望公众能接受它们,也渴望他的这些文章能以书的形式与公众见面。然而,直到1948年,在去世之前,他都未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1948年4月17日,利奥波德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他从1941年就开始寻求出版的书终于被牛津大学出版社接受了。他非常兴奋。两天后,他带着妻子和最小的一个女儿来到他的乡间“别墅”。这是他每年春天都要进行的旅行。农场里洋溢着春意:白头翁花在开放,红柳在抽芽,山雀在求偶,即使在朦胧的月夜里,从沼泽地里不时传来大雁的咕咕声,也能使人感到生命的存在。利奥波德在这里种树、观察、读书,人和大自然都是生气勃勃的。4月21日上午10点,邻居农场起了大火,利奥波德去救火……。当天晚上,麦迪逊的报纸上登出了头条消息:“奥尔多·利奥波德教授在扑救草场大火中去世了。”实际上,他是在奔赴火场的途中,因心脏病猝发而突然死去的。
一位科学家的离世,似乎并未引起多大波澜,曾因大火引起喧闹的农场早已沉寂下来,搏斗后的大自然又在繁息着。这是自然的辩证法。
一年以后,一本薄薄的书《沙乡年鉴》(ASand CountyAlmanac)问世了,它是利奥波德思想的结晶。
《沙乡》自出版以来,不论是原著或是译著,在很长时期里都只被看做是一部自然文学(naturewrit⁃ing)。据美国著名的利奥波德研究专家苏珊·福莱德教授讲,她初次闻听利奥波德,就是在大学本科的英文阅读课上。在中国,《沙乡》也多被置于美文之列,很多读者都是首先因其文采而受到吸引。实际上,就利奥波德本人而言,似乎也没有否认过自己作品的自然文学属性。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忽略,从一开始,利奥波德就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前人和当代人已经开创的事业中“增添某种东西”。这“某种东西”,实际上就是他曾暗示过的那种蕴含在自然文学形式下的“哲学内涵”。(见《沙乡》附录:未发表的序)
利奥波德的这一追求,在《沙乡》之中得到了真正体现。他将三个概念——土地是一个共同体的生态学概念,土地应该被热爱和尊敬的伦理观念和土地产生了文化结果的事实,通过生动的文学描述和敏锐深邃的审美眼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从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概括,进而对人和土地(自然)的关系提出了新的伦理标准。他通过自己毕生对土地的认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概念——土地伦理。他认为,土地并不只是土壤,它是一个包括气候、水、植物和动物的共同体,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和公民”。这便是土地伦理观,“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的尊敬”。
利奥波德曾说,他的土地伦理观只是生活旅程的一个最终成果。在《沙乡》中,利奥波德曾记述了这个旅途中的许多插曲。其中,最动人心弦的,是他在《像山那样思考》中的那段描述:
峭壁下面,一条湍急的河蜿蜒而过。我们看见一只雌鹿——当时我们是这样认为——正在涉过这条激流……,我们错了:这是一只狼,另外还有六只显然正在发育的小狼也从柳树丛中跑了出来……
“在一秒钟之内,我们就把枪弹上了膛,而且兴奋的程度高于准确……。那只狼已经倒了下来。”他写道。当时的利奥波德,作为一个坚定的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他坚信,狼越少,鹿就越多,因此,没有狼的世界,就是猎人的天堂。但是,这次的狩猎经历,让他有了新的认识。
当他们到达那只老狼的所在时,正好看见在它眼中闪烁着的令人战栗的“绿光”。“这时,”利奥波德写道,“我察觉到,而且以后一直是这样想,在这双眼睛里,有某种对我来说是新的东西,是某种只有它和这座山才了解的东西。”自那以后,他亲眼看到一个州接一个州地消灭了所有的狼,也看见失去了狼的山被过多的鹿拖疲惫的状态。而最终,则是大批失去天敌的饥饿的鹿的死亡。那个原本紧扣的狼-鹿-森林的食物链被人破坏了。
利奥波德深切地感到,人为的变化,与生态学上的变化相比,是一种不同序列的变化,其具有的影响要比意愿中的,或意料中的要广阔得多。因此,在自然面前,人类必须小心谨慎,谦卑有礼,因为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破坏它的生态完整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他告诫道,只有“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他呼吁人们以新的意识对待土地,不再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自然面前。
利奥波德的这种将人和土地看做一个整体的论点,虽与西方传统的“万物为我,我为上帝”的天人相分观有悖,却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尤其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的“人与天地一物也”的论点相合。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中国古代精英们修身养性的最高追求,它并不涉及任何自然的各种物种的关系。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则不仅是一种伦理学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通过实践得来的生态学上的科学结论。
利奥波德一生出版了三本书,五百多篇文章。他的关于土地伦理的论述,奠定了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并由此获得了生态伦理学之父的美誉。如今,《沙乡》被纳入汉译学术名著系列,更明确了它在中国的学术经典地位,可谓实至名归。
实际上,从频频被拒到普遍接受,《沙乡》在中国的经历也折射了一种意识的转变。曾几何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当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时,许多在西方已经习以为常的概念,在我们国家,还只是一些只见于媒体和专业书刊的名词,诸如生态学、生物圈、生物多样化等。而今天,仅过了二十余年,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已经成了人们挂在嘴边上的常用词,不再专属于媒体和专业人士了。但是,语言并不代替行动,实际的环境状况仍不容乐观。正如利奥波德所言:“如果我们在理智的着重点上,在忠诚感情以及信心上,缺乏一个来自内部的变化,在伦理上就永远不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我想,这正是需要我们阅读利奥波德的症结所在。
自1992年起,至今,《沙乡》已出版了四次。初版时的书名为《沙乡的沉思》,是为意译;第二版时改为《沙乡年鉴》,是为直译。三版时与初版同名,此次又与二版时相同。实际上,直译或意译,向来在译界都有不同看法。“沉思”耶?“年鉴”耶?也总是仁智之见,各持一端。作为译者,我一般都是尊重编辑的取舍的。反复易名,无非是一个目的,即便于读者接受。据说,根据市场调查,似乎《年鉴》更被认可(近几年来,国内又出现了《沙乡》的另外几种译本,似乎都使用了《年鉴》之名)。对此,作为译者,难置可否。
时过二十余年,人世沧桑,不尽细说。如今,当年曾经为《沙乡》的出版倾注过心血的朋友,有的已不在世间,如苏珊的母亲——多洛雷斯·福莱德夫人,尼娜·利奥波德·布拉德利——利奥波德的大女儿。而曾与我为《沙乡》在中国的出版分享忧乐的苏珊,亦与我同步越过古稀之年,令人感叹。毋庸说,四时万物,皆有盛衰,然唯有精神之光芒无极永远。“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我们似又听见利奥波德在《沙乡》中多次借鹤发出的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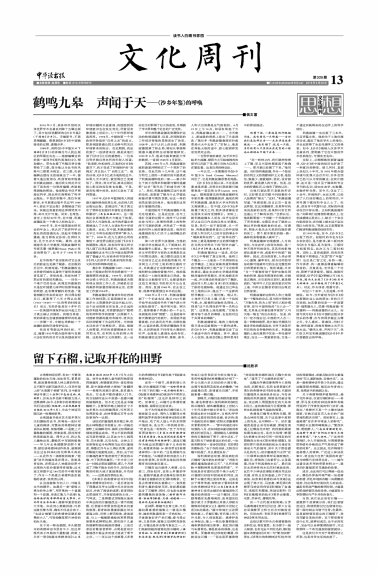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