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介徐梵澄先生的文字是很难的工作,更遑论评说。
《孔学古微》1966年序定于印度琫地舍里,今由青年学者李文彬译就。应该肯定译者和校者的用心与学力,庶几将梵澄的謦欬与气息传映于字里行间了。不过,也正因着简明而亲切,读者在从容愉心的阅读中,或有可能忽略内里的深邃识见和普遍理念。而发觉这些思想“宝什”且表述全面,实为不易。这里只能依拙力所及,概述一二。
很显然,梵澄诠解“孔学”,亦是贯穿着他“一生所治”的精神哲学。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认知,认为儒学的本质是“世俗”的,抑或仅为一些“道德训诫或行为原则”。对于这种肤浅的误解,梵澄告知,“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而且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量测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与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孔学古微》之《序》6页,后下简称《孔学》)。——这段文字极为关键,它几乎浓缩了精神哲学视域内之儒学的所有根本要件。
梵澄语境中的“精神性”,并非悬浮空挂的孤立概念,而是诸要点彼此发明的思想有体或曰理脉网络(这是阅读时特需注意的)。就基点而言,则在形上与历史,而历史又是理论的出发点。故此,他以“极具精神性”来确定儒学本质时,首先对传统的或曰前现代的中国历史,下了一个似乎绝对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孔学》之《序》3页)
这论断放置今日,定会招来各样异见。然而,梵澄自有一番理路。他认为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充满着接连不断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其共通特征则是,在最艰难无助的时刻,会有希望之“光”的出现。印度称之为“降世应身(Ava⁃tar)”,中国称之为应天命而生的“圣人”。这当然不可用“英雄史观”或“轻视人民”之类做浅表的理解,因为它内涵一深刻的看法:历史是人的创造,何样之人书写何样历史;无论民族或个体皆不脱此律。其实,康德所言的“理想的哲学家”,弗洛伊德将犹太民族先知摩西称为“表现人之本质的类型”的“同命运搏斗的英雄”,都近似于这样的历史观。梵澄将此种史观视为“古老的理论”,不过,就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这“古老”何尝不是恒久“常新”的真理!“圣人”的重要作用,就是范导历史。梵澄引用“神圣母亲”的话说:“在永恒的变是之中,每一位降世应身都是未来更加完美之实现的宣告者和前行者”(《孔学》之《序》7页)。
那么,圣人以何者来范导历史呢?答曰:以“精神性”。梵澄认为室利·阿罗频多的定义值得体味:“神圣圆成永远在我们之上;但是精神性的含义是要人在知觉性中和行为中具有神圣性,并于内中和外部都生活在神圣生命之中;赋予这个词的所有次要含义都是拙劣和不实的。”(《孔学》之《序》7页)这里核心概念是“神圣性”。明确说,“神圣性”即“精神性”。毋庸置疑,梵澄对阿氏有着深度的理解。“神圣性”在梵澄的语境中,被诠释为动词性的“文化”。在将宇宙视为一有机大生命体的意义上,“神”(divini⁃ty)就成为有着“天道”源头的“人性中的菁华”,而“精神性”的人不过是将这“菁华”圆成完善而已。从这个视角来说,“精神”又是“文化了”的过程。因此,梵澄说,关于“精神”的物理或人文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那是高度发展和文化了的生命,也可视为文化本身”(作为动词性的“文化”,《孔学》多处涉及,如76页、172页)。又说,“文化”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依照人性中的菁华而使人转化和完善”,正是在个层面,“文化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具神性”(《孔学》之《序》11页)。
这个论说触涉到“存在意义”的深层问题。为此,梵澄特别对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仁”作出具有形上高度的诠释。经过比勘梳理,他认为将“仁”描述为“神圣之爱”或“精神之爱”非常接近原意。就价值源头而言,它表示“天地之心”,意味“宇宙的大和谐以之显现和遍漫”;从人的“存在”而论,它包含着各种善,“如平和,非暴力,慈爱,善行,同情,博爱”等许多美德。总之,“仁”在上,亦在内,“是宇宙存在的根柢”。由此可见“仁”的神圣义和庄严义。(《孔学》48页,49页)
“存在”意义上的“仁”,乃为人以及人类“须臾不可离”的生命原则。故而梵澄举史料,言明儒家文化之精神,如“一日不可离之稻谷”那样重要,且简易可行,因为“作为宇宙原则,仁离我们不远。人在转念之间,就可以拒绝冷漠枯燥的生活,付出并得到爱,只要人觉醒于仁,仁便就在眼前了”(《孔学》49页)。
还需作一提问:儒家的理想如何可能实现于现实之中呢?梵澄认为儒家的思路有着极大的历史合理性,即居于最上层的主政者必须是“在知觉性和行为中具有神圣性”或曰“精神性”的君子,“从最上层开始,直接在皇室中产生影响,然后如旱季的雨云,笼罩整个国家,将甘露洒满大地。面对数量巨大的人口,这可能是最直接和最简易的方法”。据此,他借“球形”之喻,说明主政者居于“球心”,他们的任何决策作为,发到“球面”,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参见《孔学》十二章)
对具有历史可能性的儒家理想,梵澄绝不将其降低层次。因为在他看来,“精神之爱并非指向一两个人,而是指向宇宙中的所有人和所有事物”,如果放弃“大同”理想,那么,“福祉”就会成为少数人群或权贵阶层的特权,“而人类的救赎或社会的进步就只能是空谈了”(《孔学》176页)。指向“所有的人和事物”,意味着必须尊重每一生命个体之特有的存在及成长的权利,即所谓“道并行而不悖,万物育而不相害”;任何人都没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所有人的特权,梵澄谓之:“黄金法则”就是“没有黄金法则”,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大道”。(《孔学》之《序》10页)
当今,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大端有两说,一是“复兴”,二是“制度化”。如果静心读进去,《孔学》或许会颠覆这些外在的想法:不是儒学需要我们“复兴”,而是我们需要从儒学中汲取解决困境的智慧;并非儒学需要“制度化”,而是我们必须首先成为“精神化”的人,现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才有希望。
徐梵澄先生的《孔学古微》内涵丰富而深邃,有限的篇幅,只能挂一漏万。然而,我毕竟在他的娓娓道来之中,听到了久违的古典“乡音”。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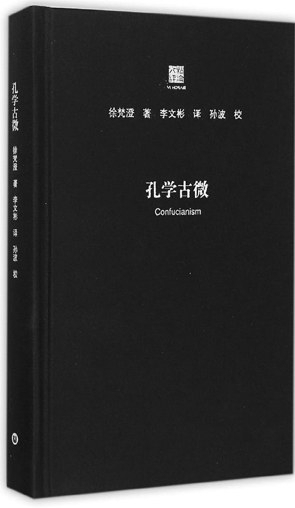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