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这个名字在中国学界并不算陌生,至少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可算是“如雷贯耳”。他曾担任过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主席,并且很早就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院士。此外,还有三个原因使得他在中国学界如此名声大振:其一,他本人确实在美国属于主流人文学者,单从他的一系列经历我们就不难发现他在美国学术界所处于的领军地位。他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长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前者使他一度介入现象学批评日内瓦学派的著述活动,后者又使他与德里达及其他三位耶鲁同事结盟并一度形成所谓的“四人帮”。其实这四位批评家的学术生涯有着不小的差异,而他们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四人帮”或“耶鲁学派”,其原因不外乎这样三点:第一,他们四人都著述甚丰,而且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批评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对美国文学批评的冲击力如同“黑手党”一般;第二,是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解构主义的鼻祖德里达的影响,在其批评实践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解构倾向;第三,他们四人都曾同在耶鲁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任教,属于学者型的理论批评家。因此把他们放在一起统称为“耶鲁学派”是一个十分便当的办法,甚至有人把曾在耶鲁大学客座的德里达也归为“耶鲁学派”的一个编外成员。实际上,仔细阅读这四位学者的著作后,我们便不难发现,所谓“耶鲁学派”并不是一个有着相同批评原则或倾向的批评流派,而是一个松散的、各自为阵但却有着大体一致的解构倾向的批评群体。由于他们都曾经或仍在耶鲁大学任教,并且时常彼此之间进行批评性讨论和切磋甚至争论,此外,他们的组合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德里达的进入美国批评界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把他们统称为“耶鲁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米勒在中国学界的名气之所以如此之大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他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美国的最重要的代表和实践者介绍给中国学界的,他的一些著作也早在80、90年代就开始被陆续译成中文,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和比较文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两年在国内文学理论界讨论得很热火的那本《小说与重复》虽然迟至2008年才有完整的中译本,但在此之前关于这本书的评介性文章就已经不少了。由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也确实需要像米勒这样的既有理论又擅长细读的批评大家,同时对中国学界来说,我们也确实需要像米勒这样的主流人文学者为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推波助澜,因而米勒的批评著述便引起中国学界的特别关注。这一关注在本世纪甚至发展到了几所名牌大学的多位博士生以他的学术思想和批评理论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而这即使在他的祖国美国也不多见。难怪他不无调侃地说,“我在中国的知名度大大超过了我在美国的知名度”。
其三则是米勒与一些非常神秘的西方理论大家均不同,他为人十分和善和亲民。无论是蜚声学界的大教授还是初出茅庐的博士生,只要给他写信请教学术问题,他总会在第一时间亲自回复。要知道,对于这位只用一只手写作的八十多岁的老人,亲自操作电脑是多么的不易。不少年纪小于他的中国学者也许早就不上电脑了,所有的信件均由家人或学生代为回复,或根本不予回复。而米勒则亲自回复来自各方面的来信,这样便使他在中国学界有着广泛的人缘和很好的口碑。接踵而来的就是不少大学邀请他前往演讲,不少国际会议邀请他作主题发言,而他一般没有其他允诺大多会满足中国学者的要求。因此我们就有了这本《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AnInno⁃cent Abroad: LecturesinChina,2015),这是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中国十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所作的三十场演讲的精选文萃。作为学者型批评家的米勒从不满足为了演讲而撰写的稿子,他总是反复地在吸取听众所提问题的基础上修改扩充原稿,使之成为能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单篇论文。现在年逾古稀的米勒应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邀请,又按照这些演讲的内容选出十五篇编成本书,从而使其有着内在的整体性,读来不禁令人颇为亲切,同时又不无启发。
我和米勒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相识,当时他第二次应邀来北京大学演讲,而我作为一位青年教授并没有机会与他进行深度交流。我和他真正开始比较频繁地交往则始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创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其后又在清华大学创立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米勒被我们聘为客座教授。我们每隔一两年都要举行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米勒便当之无愧地作为我们首先邀请的美国学者,而且他每次几乎都有求必应。于是我们就成了很好的学术同行和朋友,并保持较为频繁的邮件往来。几年前,当我从米勒的来信中得知美国的一家大学出版社将出版他在中国的演讲集时,我立即感到这本书应该同时在中国出版,便鼓励我的两位学生尽力促成此事:我先前在北京语言大学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国荣承担了本书的大部分翻译和校订工作,在我的指导下以米勒的文学思想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郭艳娟正好担任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她也表现出对这本书的极大兴趣,并得到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这两位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本书马上就要在中文世界出版了。我想这不仅是因为书中的不少篇章最初是米勒教授在我安排的学术讲座或国际会议上的演讲,而且还因为这一篇篇闪烁着批评睿智和思想火花的论文正是中国当代十分需要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各种高科技数码技术的发展,人文学科被放逐到了边缘,更不用说印刷在书本中的文学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将向何处发展”成了每一个致力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毕生致力于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米勒对此尤为关注,并不断地在各种场合为文学的幸存而做“最后的一搏”。但他同时也提请人们注意:既不要对文学的衰落感到沮丧,也不必与文化全球化的大潮逆流而动,正确的选择是在全球化高科技的大潮面前表现出冷静的态度,安心地从事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这应该是对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的一种告慰:文学是不会消亡的,但它再也不会像以往那样处于“黄金时代”了。由此看来,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毕生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老学者为了捍卫文学的合法地位而做的最后一搏,饱含着深刻的人文情怀。所以,当米勒再三嘱托我为该书中文版撰写一篇序言时,我不禁倍感荣幸,但同时又不免诚惶诚恐,因为为这本书英文原版作序的正是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和米勒早年在耶鲁就是同事,之后几十年里一直和我们有着往来。
也许读者们要问,在这样一个文学不景气的全球化的数码科技时代,出版米勒的这本纸质的演讲集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想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启示外,本书对中国的文学批评界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其两篇附录,因为如果前面的十五篇演讲是米勒的独白的话,那么作为附录的一部分,本书还收录了中国学者张江近年来和米勒进行的两轮对话。我认为,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近年来在国际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我们过去总是不惜代价地将西方文学理论大家请来中国演讲,却很少推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大家,即使偶尔推荐出去了,也很少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这样看来,米勒率先与小他一辈的中国学者张江平等对话便有着明显的表率作用。尤其令我感到自豪和宽慰的是,在我的编辑和推动下,张江和米勒往来的四封信将发表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和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权威刊物《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ies)第52卷(2016)第2期和第3期上,这也是该刊自创立以来首次连续发表一位中国文论家与西方文论家的通信式对话。这一事件将在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鉴于国内学界对此尚未有足够的认识,我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人们也许会问,张江与米勒的对话之意义具体体现在何处呢?我想在此先略述一二。首先,这分别是两位中国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著名文学理论家之间的两轮通信,这些通信将告诉我们的西方以及国际同行和广大读者,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即使在理论衰落之后的“后理论时代”仍然对西方文论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仍在认真地研读其代表性著作,但是这种兴趣不仅体现于虔诚的学习,更在于对之的讨论和质疑;其次,这两封信也表明,中国的文论家并非那种大而化之地仅通过译著来阅读西方文论家的著作,而是仔细对照原文认真研读,而且并没有远离文学文本。他们在仔细研读西方文论著作时,不时地就一些疑惑和不解之处提出一些相关的甚或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通过与原作者的直接讨论和对话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识;再者,两位批评大家在仔细阅读了对方的通信后,深深地感到中西方学者和理论家就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误解和分歧,因此迫切地需要进一步沟通和对话,只有通过这样的对话才能取得相对的共识,并且推进国际文学理论批评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确实,正如我在其他场合已经提及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大量的西方学术理论著作,尤其是文学理论著作被译介到了中国,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的批评思想和研究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诺斯洛普·弗莱、罗兰·巴特、埃莱娜·西苏、米歇尔·福柯、爱德华·赛义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哈罗德·布鲁姆、特里·伊格尔顿、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乔纳森·卡勒、朱迪斯·巴特勒以及米勒本人,高视阔步,频繁地出没于中国文论家和研究者的著述中。假如有哪位文学研究者或批评家不知道上述西方文论大家的名字,便会感到羞耻和被人认为是不学无术。甚至那些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学者,也至少对上述文论大家的名字有所耳闻。中国学者不仅对他们的著作十分熟悉,而且还认真地将其运用于中文语境中的文学作品阅读和文学现象的解释。一些对西方现当代文论情有独钟的青年学者还以上述文论大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当然,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了解西方乃至国际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成就及当下的前沿热点话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这只是实现中国文论国际化进程所走过的第一步,我们切不可仅仅满足于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和“封闭式”讨论。就这一点而言,张江的尝试可以说跨出了新的扎实的一步,而米勒的回应则体现出一位西方学者对来自中国的声音的重视和认真态度。这应该是促成这两位文论大家进行对话的一个基础。
(本文为作者为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萌在他乡:米勒中国演讲集》中译本所作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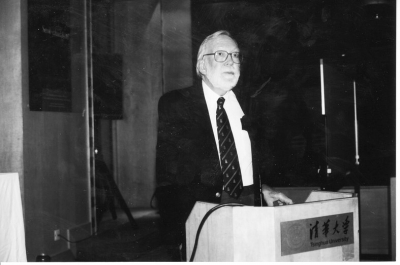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