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看是不错的。但向后看也同样重要,或者说,只有时时向后看看,不规避失误,不掩饰缺陷,才能使向前的步伐更为稳妥,更为坚实。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到北京不久,就听说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喜欢骑自行车逛北京,感到非常新奇。因为那样大的官儿,在敝国也早已是“红旗”“上海”“伏尔加”——“屁股后头冒烟儿了”。何况是美国,何况是代表美国官家体面的“联络处主任”。所以,新闻媒体曾对此细加介绍,还配有图片。
随着这些报道,报章上开始大量刊登国外对中国这个“自行车王国”的美评,也有我们自己以此为豪的文字。大意是说骑自行车如何节约能源,如何避免环境污染,如何有益健康,欧美等国的幡然悔悟,似乎恰证明了中国人的环保意识如何先进。如此等等,曾让我颇感自豪。那年头,北京雨天骑车,雨披七彩,堪称一景,故我有诗赞道:
青绿橙黄蓝紫红,单车百万雨帘中。诸君试上天桥望,一道湍流化彩虹。
但是,事有不可预料者。没过几年,报刊上对“自行车王国”的礼赞,变成了关于“轿车进入家庭”的讨论。起初还有两种意见,其中主张根据中国的现实与国情,应继续鼓励自行车出行并加快发展公共交通的占着上风。又过了一两年,舆情大变,轿车进入家庭,渐次成了强势的呼声。又渐次,大力发展轿车,成了政府的既定政策。
到底那时出于什么考虑?是认为要走世界诸国共同走过的道路?是因为发展轿车生产能够发展经济,销售能源,增加税收,还是以为轿车的普及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说不清,总之一年一年,引进的,自主的,高档的,低档的,各式各样的轿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随之而来的则是能源的过度消耗,大气的严重污染,道路的异常拥堵——首都北京被称为“首堵”。大都会上海被叫做“大堵”,南国的广州则成了“广堵”。总之,当年我们指责、批评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在我国都一一重现,而我们曾引为骄傲的自行车,则被汽车挤得连行驶之路也危乎殆哉了!
于是,人们开始抱怨,开始大谈雾霾,开始口罩风行、见霾关窗,但就是无人讨论当初大力发展轿车,推动轿车进入家庭的利弊权衡,究竟应当接受什么教训?或许还是“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一致“向前看”的老传统吧。只是,一项决策在实施之后如果没有对效果的评估,没有对引发问题的深入解析,没有对当初决策的的认真检讨,在处理其他问题时,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举一反三的长进。
还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采访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采访另有主题,我竟记不得了,倒是采访之外的闲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那天忽然离开了访谈的内容,问我:为什么我们北方地区也种起了水稻?我说,大概因为水稻比麦子产量高吧。一九五七年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对粮食产量的增长有明确的指标:黄河以北十二年内亩产要从一百五十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要从二百零八斤提高到五百斤。在“以粮为纲”的时代,这个指标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各省、各县官员们的政绩,当然也关系到他们的晋升与罢黜。种植水稻可以明显地提高产量,自然成了首选之策。何况《发展纲要》还有水稻种植面积要从四亿三千万亩增加到七亿四千万亿亩,不从北方打主意,哪能增加这三亿多亩稻田?
“可是,从老祖宗起,北方都是种旱作作物啊。为什么?”光召先生苦笑地摇了摇头,好像只是提示,并不是提问。
他的提示,引发了我关注此事的兴趣。种水稻要水,北方水少,所以历来都种旱作作物。但是,指标既高,就要完成。我们又处在鼓吹“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的狂热时代。于是华北平原开始了向地下要水的高潮。作为典型的石家庄地区,每平方公里打了十口机井,还在不停地打。水资源严重匮乏的河北,一度总计打了八十多万眼机井,每年抽取一百二十多亿立方地下水。
后来我到甘肃采访,据介绍也在为人均一亩水浇地而大搞黄河提灌工程。我问,黄河本已缺水,每年都发生断流。这样提灌,中下游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上游宁夏就在提水灌溉,山西在“引黄入晋”,黄河水我们不用,人家也在用。“那么,下游断流咋办?”回答:“那是黄委会(黄河水利委员会)管的事。”
这样,我才渐渐感到,周光召作为中科院院长,他一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一定对大量开采地下水和黄河的处处截流等相关决策有着更深的忧虑。
地下水超采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过了几年我到河北,省委书记别的采访可以推脱,唯独一谈水资源的问题,再忙也愿意接待采访——因为这时超采地下水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
南水北调,恐怕就是因水资源的滥用,不得已而为之,是对以往掠夺性使用水资源的惩罚。
但是,水资源的涵养与利用,我们认真回头看过吗?对以往的失策,我们认真总结过吗?或许有吧——但人们听到的只是对南水北调工程的赞美与欢呼。
但是,在同一些专家的接触中,我听到的却不乏各种忧虑。这样大规模改变自然生态,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很难预估的。盲目相信“人定胜天”,带来的或将是天之惩罚。苏联,不,更早的俄国,就不断有过这种大规模调水的设想,想用北水南调来解决南部荒漠地区的农业生产。但是,上百年研究下来,终因可能的后果难以预估而作罢。这情形是水利部一位高工同我谈的。他还谈到一种担心:如果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北京的饮水问题,那么似乎还有更为便捷的方法。如果想用调水来解决农业用水,那么,农民是否用得起这调来的水,大可讨论,除非国家大量投钱来填补这个黑洞。至于大量调水会带来什么环境的改变,这些改变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想来应当有详尽的研究吧?但结论如何,一般人是不知道的。或许,俄国北水南调可能出现的问题,中国并不存在?只是以往的经验表明,许多庞大工程,决策之际的拍手派、举手派,乐观派,到得出了不曾预料或曾经有人预料而未予置理的问题,照例都推卸责任隐匿不见了。三门峡的前车之覆,就是个例证。决策而不承担责任,使参与决策者颂词多而诤言少,而事后的评估,照例也是走过场或秘而不宣的。
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高楼林立,叹为观止。一位俄罗斯小姑娘随父来到上海,看到到处都在建高楼,不禁大为惊奇: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钱造大楼啊?陪同的人颇为骄傲地告诉小姑娘,因为我们努力劳动,所以就能盖很多高楼。这事曾见诸报道。我那时觉得这回答颇有点忽悠之意,但要回答一个小姑娘的这个问题,讲得太详尽似也未必能够理解。
不过,当时内地各处并不曾有沿海这样规模的建设。我想,这是缺少资金的缘故吧。但不久我就发现,原来他们是不曾开窍,还不懂得土地可以换钱。及至一旦恍然有悟,在“招商引资”的口号下,到处都在卖地,都在拆迁,都在盖楼,而首先盖起来的大抵是那里的政府大楼。“土地财政”这词儿就是那时开始听说的。这样的“土地财政”造成了几多虚假繁荣,带来了哪些政事腐败,已有一些报道,但未闻当年的决策者有什么反思,有什么处置,按照老规矩,大概又是一句“付点学费难免”吧。
还有一项担忧,是我当时听过未曾留心,直到近来才觉得是不是真的“来了”。
我说的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好像是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是世界诸国,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建造的楼房,最容易草率从事,隐患多多,以致寿命不长,屡有坍塌。就此事好像又有人写文章提醒越是在快速发展期,越是要注意建筑质量,即所谓前车之覆应当引为后车之鉴。
大概因为这些文章的影响,每见到一座座大楼像搭积木一样拔地而起时,我心里总想,但愿这些楼不是豆腐渣。后来听说一些工程的招标猫腻重重,施工队伍资质可疑,心想,这样建造的楼房,将来如果出了问题,恐怕根本无法追究责任,尤其是一些民用建筑,竞标到手的并不就是实际施工的,往往夺标者只是把工程再分包出去,从中渔利而已。而许多实际施工的“建筑队伍”又都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完成建造后便各自分散,哪里去找!
再后来,关于楼倒倒,阳台坍塌,窗户飞落,擅自改建,种种异事渐渐多了起来,不由又令我想起那篇提示“前车之覆”的文章。
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一个能将自己的、他人的失误化为财富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一直在讲要善于学习。向成功处学,也向失败处学。成功之际,不陷于沾沾自喜,而能思考其不足;失败之时,不汲汲于弥缝、掩饰甚至封锁消息,而能坦承失误之由,总结避免之策,以使失败化为教训,这才是为人之道,治学之道,建国之道,成功之道。
向前看是不错的。但向后看也同样重要,或者说,只有时时向后看看,不规避失误,不掩饰缺陷,才能使向前的步伐更为稳妥,更为坚实。而一味以向前看为由,拒绝对失误的研讨,倒是未必能有效地前行的。
(本文摘自《悦读MOOK》第44期,2016年1月第一版,定价:20.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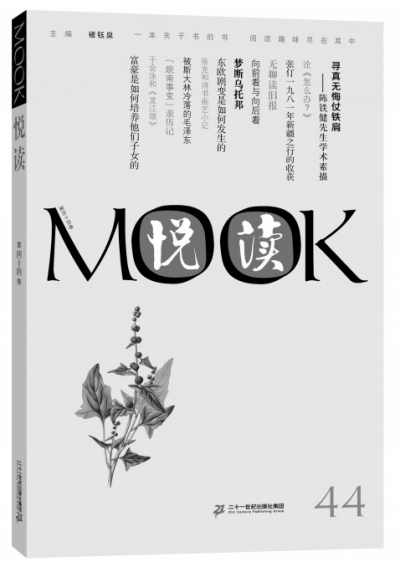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