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实无法给予孩子希望和温暖时,孩子就靠记忆和幻想为自己构建一种精神的乌托邦,在虚幻的世界中获得自我存在的确认。
《逃逃》是秦文君创作于2003年的儿童小说,今天读来,题材、故事依然鲜活如初,人物、蕴涵也更显丰赡、深厚。
小说讲述了五年级男生逃逃和大大大因生活不如意离家出走,经受挫折后幡然醒悟的故事。单看内容,小说很容易被贴上“问题小说”的标签。但细加品读后,不难发现,其实,作家寄寓在“离家—返回”情节模式背后的情感、意蕴远没那么简单,它关涉到家庭教育、亲子关系、爱与责任、梦想和现实等诸多儿童成长命题。
具体说来,小说呈示了两方面的题旨:其一,亲情渴望与心灵补偿;其二,自我确证和尊严维护。这样的主题、蕴含既是作品中小主人公心灵诉求的真实表达,也是作家童年关怀和价值考量的趋向所在。
这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儿童形象塑造上。故事里,作家刻画了两类孩子形象。一类是以小小小、黄美、毕晓宇、“小疙瘩”、小陶金等为代表的“好学生”“幸福孩子”;另一类则是以逃逃、大大大、小瘪三龙龙、小山东、小四川为代表的“弱势儿童”“问题少年”。如果说,前者体现的是现实童年的主流样态,那么后者则代表了童年生态的边际面貌。这恰恰是小说形象塑造的焦点所在。
主人公逃逃是个单纯、善良、自尊、诚实、敏感、细腻的孩子。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后,逃逃最需要的是母爱,是生活上的关怀和精神上的理解。可是,年轻的后母王阿姨却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让逃逃更为惶惑的是,在自己家里,他成为“外人”。他不仅体味不到母爱,甚至连爱的权利也被无情剥夺。此时,唯一的安慰是小弟弟陶金稚拙而真实的依恋。至此,家已经由温馨乐园异化成了笼罩着漠然、无奈、委屈、怨愤的心灵孤岛。
正因如此,当从大大大口里听到“迷人巷”时,他立刻被迷住了。想象中,那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世界。故事的最后,当逃逃带着小弟弟陶金安然回到家的时候,作家这样写道:“那已是深夜,在路边灯下看自己所熟悉的弄堂,逃逃发现这里的一切依旧是老样子,只是好像所有的东西都缩小了一丁点儿。”
显然,经过“离家”后一系列的生活砥砺,逃逃已经不是懵懂、冲动的小男孩了。他懂得了爱与被爱,理解和信任。他已经长大了。
相比逃逃,大大大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家庭破碎的同时,亲情也离他而去。爸爸沉溺于“眼泪水”,整天醉生梦死,大大大完全处于父爱的失重状态。面对肮脏、破败、毫无生气的家和迷茫、消极不知所终的前途、命运,大大大一方面靠恶作剧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以油嘴滑舌、嘻嘻哈哈掩饰内心的失落,另一方面也不断通过对阔姑婆慷慨施予的炫耀,以及信口开河的幻境描述表达情感诉求、心灵渴念。唯其如此,他才能够获得面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小说里,大大大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缺少家庭温暖、成长关爱的孩子,其生命如同荒原上的一株野草,显示了怎样一种坚韧和顽强。
小说中,男孩“小疙瘩”的出场,也是作家有意为之的点睛之笔。作家借助这个孩子写出了儿童和成人世界矛盾的普遍性。这让逃逃和大大大的“离家”具有了更为深广而典型的意义。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曾指出:“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
也就是说,当现实无法给予孩子希望和温暖时,孩子就靠记忆和幻想为自己构建一种精神的乌托邦。小说中,逃逃和大大大一直津津乐道的“迷人巷”实际上就是孩子们的“白日梦”。这让人想起巴里笔下带着一代一代孩子逃离家园的神秘男孩彼得·潘。不同的是,彼得·潘通过永远不长大来抗拒成人社会强加给儿童的社会形象,其“离家”行为本质上是价值观的冲突和精神的反叛;而逃逃和大大大则试图将家庭环境中的屈辱、无奈、漠然、伤感置之脑后,在虚幻的世界中获得自我存在的确认,其“离家”选择所标示的更多是自我精神救赎与家庭亲情补偿。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迷人巷”具有深厚的象征意味。这个虚拟世界如同《彼得·潘》中的“永无乡”一样,是所有孩子共同的秘密,共同的心灵镜像、精神家园。
除此之外,小说还写出了童心的朴实、真诚、磊落、自然。无论是小小小不计前嫌的临别祝福;还是黄美细心、体贴的礼物赠送;无论是小瘪三龙龙初次见面的慷慨仗义,还是大大大投桃报李的真诚允诺;无论偶遇时,“小疙瘩”急中生智的信任挽留;还是困境中,难兄难弟的不离不弃……都显示出儿童世界单纯、善良、诚挚、信义、朴实、热忱、乐观、宽容的纯良底色。这也是整部作品略显沉重的情节氛围里最摄人心魄的亮色。
在小说的审美倾向上,秦文君则表达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故事中,她以举重若轻的情节结构,轻捷、幽默的语言叙述,适时揭开了生活温情脉脉的面纱,让小读者瞥见了现实背后斑驳、迷离的童年世相。与此同时,还将笔触深深嵌入边缘孩子的内心深处,将他们内心的隐痛、情感的渴望、自我的寻找,以及卑微中的渴念,清冷中的美丽等等精神诉求表达得令人唏嘘不已,而又感慨万千。
秦文君同时也是一个温情的理想主义者。尽管现实的童年生态阴翳密布、病象连连,但她依然深信生活中真与善的存在,依然相信爱能给予童年信心和希望。基于此,故事里,她不愿孩子彻底坠入生活的危境、苦难的渊薮。于是,情节推演中,作家让逃逃和大大大困厄中清醒自救,并安排老奶奶雪中送炭伸出援手……所有这些,不仅仅是爱心的守护,更是精神的引领。
对儿童读者来说,文学所能给予他们的不止是启迪与警醒,更有信心和期冀。显然,秦文君深谙此道。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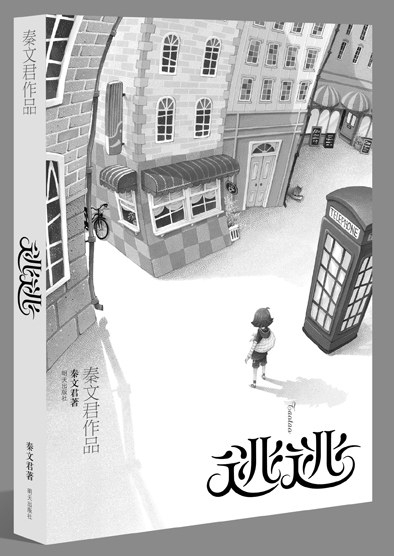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