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鲁迅日记中被先生提及了114次。张友松——这位民国老人,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人生惨剧,却依然刚直不阿、顽强地独自支撑,在陋室寒屋中借助放大镜依旧笔耕不辍,翻译着他钟爱的马克·吐温作品。直到1995年,92岁的他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
中国翻译界有一位专门翻译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作品的“专业户”,翻译了几代读者耳熟能详的名著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王子与贫儿》《镀金时代》《密西西比河上》《傻瓜威尔逊》《赤道环游记》等,其中著名的《竞选州长》多年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这位老翻译家叫张友松,民国时期他曾经是鲁迅的学生,鲁迅文集里一百多处提到与张友松的交往。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与大译家曹靖华、傅雷、汝龙齐名,但他就如同中国文坛上划过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流星,因为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作品改用“常健”笔名出版,从此张友松这个名字就从著名译家的行列里消失了。“文革”中受尽迫害,到“文革”结束,得到平反,这位一九○三年出生的民国老人年事已高,又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无单位、无工资、无养老金,仅靠北京政协资助少量生活费,与同样无工作的老伴偏居成都陋巷,远离中国的文化中心,因此没能像一些错划为“右派”的文化老人(如当年的同事冯亦代、荒芜、符家钦等,他们比他年轻、身居京城)那样平反后再度崛起,重享盛名。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追访译界老人,甚至像李景端先生告诫我的那样“你要进行抢救式采访”,写了几十位老译家,可竟然对张友松这位曾经如此耀眼的译界巨星一无所知,估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吧。这是历史的误会和耻辱,是该让广大读者重新认识和了解张友松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国文人了。
因为被埋没得太久,想在网上查找张友松的资料基本属于大海中捞针,但我还是很幸运地通过各种关键词搜索到了一些零星的资料,这其中老诗人和翻译家、张友松当年的同事荒芜先生的女儿林玉的博客进入了我的视野,里面有她回忆“张友松伯伯”的散论,我就冒昧给她留言请求帮助,后来得到了她的一些对历史的解读高论。仝保民先生为我提供了《新文学史料》一九九六年第二期上张老的女儿张立莲撰写的《怀念我的父亲张友松》一文,这是唯一一篇张老亲人的回忆文字,情理交融,十分宝贵。我在微博上谈论起张友松时,素昧平生的康拉德作品译者赵挺为我复印了老翻译家符家钦的散文集,其中一篇就是回忆老师张友松的文章。我还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任吉生找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人文社工作、后任该社外国文学副总编的秦顺新老人,电话采访了他,耄耋之年的秦老是健在的唯一一位在人文社与张友松有过书稿和日常来往的老一辈了,但他还是告诉我当时他太年轻,没有与张友松有深入的接触,那些对张了解更多的人都不在了!
所有这些网络搜索和电话采访都让我感到是在浩瀚的夜空中穿越历史,在脑海里借助一两张老照片重构张友松的形象,这种重构是与历史的雾霾和血泪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民国老人、曾为鲁迅鞍前马后奔走效力,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人间惨剧,依然刚直不阿,顽强地独自支撑,贫病交加,在陋室寒屋里借助放大镜依旧辛勤笔耕不辍,翻译着他钟爱的马克·吐温的作品,他是用生命在翻译,直到九十二岁在贫病中撒手人寰。
他的一位当年的学生在一九九八年曾写了《翻译家穷死成都》一文,描述他所居住的陋巷穷屋,经常忍饥挨饿。有人对“穷死”一说表示质疑。严格说,那是一条普通劳动者居住的陋巷,他下岗的女儿只能居住在那样的地方。城市低收入者在此生老病死,似乎也平常,但人们并不知道同他们住在一起的这个同样普通的风烛残年的老人竟然是著名翻译家,在那样的环境下还带病苦苦地进行着文学翻译这样似乎是十分风雅的高尚工作,他曾经锦衣玉食,西装革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月入三百元的大文学家,享受预支固定额度版税的待遇,这样的待遇曾仅次于周作人。似乎是缘于这种“落差”和历史悲剧,才说他是“穷死”的。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张友松生于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三石塘,自幼家境贫寒。十二岁随大姐到北京半工半读求学,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学,课余翻译英文小说。受大姐影响,张友松在北京读书期间,先后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除李大钊外,他当时还与邹韬奋、冯雪峰、柔石、邓颖超等人有过许多接触。其间,他还跟随大姐去当时荷属苏门答腊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试图能以此挣一笔较大的收入奉养母亲和弟妹,但不仅没挣到钱,连回国的船票都是同胞们给凑的。后来,张友松同大姐继续回北大半工半读。不得不说的是,这位具有先进思想的大姐就是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张挹兰。军阀张作霖入京后,拘捕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家,与李大钊同时遇难的唯一一位女性就是张挹兰。
大姐张挹兰牺牲后,他的家庭负担加重,无法继续在北大的学业。鉴于他勤奋好学,读书期间已发表过不少英文翻译小说,鲁迅便推荐他去了北新书局做编辑。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张友松仗义执言为鲁迅追讨出版社所欠的稿费,因此失去了自己在北新书局的工作。“别看鲁迅的文章写得泼辣不留情面,可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却在版税这类问题上往往抹不开情面,所以被人欺负。”张友松回忆说。
鲁迅的日记里一百一十四次提到张友松,说明他很器重这个年轻人。甚至在一次聚会中,林语堂先生因不知情提到张友松,语气可能略带调侃,引起鲁迅反感,两位文学大家当场反目。
失去工作后,鲁迅先生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垫付五百元帮助张友松开办春潮书局,还帮他组稿,策划出版文艺丛书。但张友松是一介书生,并不善于经营,书局很快倒闭。为此张友松很内疚,认为这是他“毕生莫大的憾事”。
春潮书局倒闭后张友松陆续在青岛、济南、衡阳、长沙、醴陵和重庆等地做过近十年的中学教员,并在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过晨光书局。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仍然勤于笔耕,翻译了很多文学作品包括契诃夫、屠格涅夫、普列沃、歌德的许多名著。
重庆解放后张友松先生正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积极参与重庆市文联和西南文联的筹备工作。本来有关领导要安排他当一个出版社的社长,几所大学也请他去任教,但他谢绝了这些出人头地的机会,一心留恋文学翻译事业。最终是在一九五一年,他应邀到北京参加宋庆龄女士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的编辑工作。
这个时候张友松已经是年过半百之人,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翻译经验和大量的作品,还是想全副身心投入翻译工作,而新杂志的编辑工作是忙乱的,他一时难以适应。恰好当时的文化部一位领导金灿然同志是他的老朋友,对他很了解,就安排他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上了“特约编译员”。这个职位其实是业余的专业翻译,人不属于出版社的编制,没有八小时坐班的时间约束,但事实上出版社包了他的所有翻译作品的出版,给予其很高的稿酬标准待遇,按月预付每月三百元的稿酬,预付费从未来出版的稿酬中扣除。这样的安排其实是极少数德高望重的文化人的待遇。据说周作人先生的月预支稿酬是四百元。所以说张友松先生当年的待遇是很高的。但这种安排也埋下了一个不幸的伏笔,那就是张友松等于辞去了一个“铁饭碗”,一旦有不测,他的日常生活就会受到难以预料的影响。但这位民国文人以前也没端过“铁饭碗”,对辞去一份工作毫无感觉,对专业翻译的向往令他对未来充满信心,一派憧憬和幸福。同一个时代在上海,也有一位热爱德国文学翻译的医生钱春绮,他因为一本德国诗集挣到了八千多元的高稿酬,从而相信自己可以靠翻译过上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于是辞去了医生的职位,变成了自由翻译者。后来稿酬标准远远低于工资的上涨速度,他的生活陷入困境,对自己辞去公职大为后悔。
张友松先生对这样的安排是非常满意的,感到了党和国家对他的器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工作热情高涨,新作迭出。当时是他的好友萧乾先生提出建议,希望他专心翻译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的作品。他接受了萧乾的建议,埋头苦干,成了马克·吐温“专业户”。他应该是继朱生豪之后第一个以“一对一“的方式翻译一个外国作家的专门翻译家。这个模式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得到了一些人的继承和发扬,成为一个优良的传统。
这段时间里张友松不仅翻译了八部马克·吐温的作品,还翻译了几十万字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可谓译著等身。
那些年里张友松如鱼得水,心旷神怡,不仅购置了几套新的西服和呢大衣,还在兵马司胡同租了一套别墅式院落,在此安居乐业。他应该说是在文学界出人头地,声名显赫。优厚的稿酬待遇下,那个年代著名的文化人甚至流行用一两本书的稿酬在京城置办一个四合院,成为风气,也成为当今看来的传说和神话。但这都是真实的情况。
但一九五七年风云突变,“反右”运动开始。作为文学家,张友松是被组织上派来的小汽车接进中南海去聆听毛泽东的报告的。出自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他积极建言献策,发表意见,根本不懂什么叫“阳谋”和“引蛇出洞”,天真的他就这样因言获罪,被打成了“右派”,从人民艺术家一落千丈,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袁木的文章,把张友松划入“右派集团”,说这个集团有一个“大阴谋”,其实这个“集团”的定性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不过是因为张友松以自己的名人身份替山东的两个老友打抱不平,结果就被诬陷为“右派集团”了。
从此张友松漫长的炼狱生涯开始了。他没有工作单位,就回街道接受监督改造,定期写思想汇报检讨。不能再以张友松的名字出版作品,起用了“常健”的笔名,但至少还是有工作可以做的。但他的稿酬待遇大大下降了,每月发给一小笔“生活费”算稿费,日子还算过得去。但他的子女却因为他的“右派”身份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一儿二女大学毕业都不能留在北京,都分到外地,一个女儿还分到了遥远的牡丹江教中学,三十年中不断受到批判。最小的女儿甚至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而不被允许考大学。
但更为悲惨的遭遇发生在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此时他没有任何工作可做,一分钱生活费都没有了,全靠儿女接济。在街道上惨遭批斗,批斗中还被“革命群众”打伤了眼睛,由于医院不积极给他这样的“坏人”治疗,耽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摘除一只眼球。他的住房也越来越逼仄,甚至被迫住进与人合住的一套两居室房屋,他只能住阴面十二平米的一小间,还是五楼。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了。老两口就在那间小阴面的屋子里生活了多年。
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他才得到了“摘帽”,不再是“右派”,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可是他已经年逾古稀。他一直误以为自己是有单位的,直到这个时候才弄明白,当年的安排其实是让他成为一个“自由翻译家”,不必坐班,享受优厚的稿酬待遇的方式是按月预支稿酬,但并非是单位的正式职工。多年后他成了一个“无单位”“无工资”的人。他要完全靠“文革”后大幅下降的稿酬标准生活了。
由于他不明白先前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约定关系的性质,他把本来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权的马克·吐温作品转到了别的出版社再版,导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了给他的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这些都是历史的误会,但这样的误会也是令人痛心的。如果没有“反右”和“文革”,他就不会有这些厄运加身。
即使是在诸事不利的古稀高龄上,张友松还是借助放大镜的帮助,翻译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直到八十一岁,与老伴离开了居之不易的京城,迁居成都陋屋,由下岗的小女儿照顾度日。这段时间北京政协每月发给他近两百元的生活费,还报销医疗费用,最后一年多他坚决不报销了,说:“不要报了,政协对我够好的了。”他就是用那笔生活费供全家几口人生活的,在那样的穷屋陋巷,直到九十二岁的一九九五年去世,没有讣告,没有“单位”为他送行的告别仪式,悄然远行了。
(本文摘自《悦读MOOK》第42期,作者黑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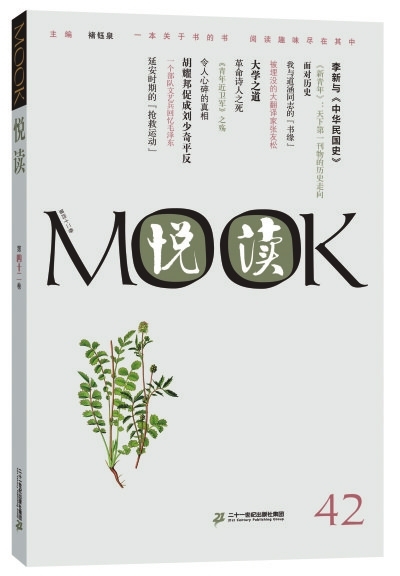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