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狼》是一部试图克服自己病痛的知识分子的忏悔录,这病痛是一种时代病,其结果造成了主人公精神上的疾苦,而治疗方法则是无情的自我剖析。这部杰作与其说是关于病痛本身的,不如说是关于疗伤之路的,是关于如何摆脱“疾病”的。
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是其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大家普遍认为是他的自传体小说。该书反映了作家在生命中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过程,它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期。1924年1月11日,黑塞第二次结婚,与年轻的歌唱家罗特·文格尔步入婚姻殿堂。然而这次婚姻也不成功,几周后作家离开瑞士的巴塞尔前往蒙塔尼奥拉。夫妇俩之间的关系在黑塞于1924年11月回到巴塞尔后变得紧张。他当时在巴塞尔的住宅以及女房东玛尔塔·林格也在作家的小说中得到了描写。别看关于女房东及其住宅在书的开头部分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作家对市民精致优雅生活的赞叹也是轻声的,但是作家其后却对市民群体与荒原狼等群体的关系作了在别的作家那里看不到的、最为深刻的剖析。“市民整洁、细致、认真、小事上尽责尽职……我嘲笑什么也不会嘲笑这种市民的生活方式与井然有序……我虽然憎恨市民,但这种气味一直有感动我的东西,“市民性”是人的常态……很清楚,(市民)这种软弱而胆小的人虽数量众多,但无法站稳,他们的特性决定了其在世上的角色只能在自由闲荡的狼群中充当羊群。然而我们看到,虽然在强者的专制时期市民马上受到排挤,但他们从没毁灭,有时看上去甚至还能掌控世界。这怎么可能……答案是:因有荒原狼们……在真正的市民阶层的原本人群周围有人类广大的阶层安营扎寨,有千种活法与才智,他们中的每个阶层虽然都已超越市民阶层,有能力过绝对生活,可都因稚嫩的情感而与市民性藕断丝连,深受其生命力脆弱的传染,多少固守于市民阶层,多少还隶属于它,对它有义务,臣服于它。”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要强调黑塞对市民或市民性的态度,是因为《荒原狼》当时和至今的现实意义都在于:知识分子在面临历史的现代性进程时,同时也会面临社会文化的庸俗化和平凡化,尽管社会的物质变得丰富且技术在快速提高,但是固守“经典”将使其产生精神危机并加剧“病情”;市民性增强是社会现代性增强的重要特点,也许能孕育出“新经典”。新经典也许会从帕伯罗演奏的音乐中、从赫尔米娜和玛丽亚的舞蹈中“别样”产生。也许知识分子的病痛可以由此得到治愈。
1924年12月夫妇俩到德国进行短暂旅行之后,1925年几乎整个冬季黑塞都在巴塞尔的大学图书馆埋头工作,编纂文集《德国精神的古典时代1750—1850》,于是他和罗特·文格尔见面次数就很少了,这些都在小说中有所反应,比如房东大婶和她的侄儿有时看到房客“荒原狼”的那位漂亮的女友来找他,看到他们见面有时恩爱,有时争吵等等。也是在这个时候,一种弃世的、无法与周围世界调和关系的感觉,一种毫无出路的绝望的情绪越来越经常地光顾他,控制他。自杀的念头不时在他的脑中闪现。还是在巴塞尔的时候黑塞就开始了《荒原狼》的创作,后来到了蒙塔尼奥拉和苏黎世,他仍继续这项创作。其实这部小说的一些场景和情节作家早在他的散文小品《摘自一个背弃者的日记》(1922)中就有预先使用,而更直接和明显的使用或化用则表现在《荒原狼》的“抒情诗平形体”中,即诗集《危机。赫尔曼·黑塞日记摘录》中。这部诗集写于1926年冬,其完全版则直到1928年才由费歇尔出版社出版。
《荒原狼》是一部试图克服自己病痛的知识分子的忏悔录,然而主要的是,这病痛是一种时代病,其结果是造成了主人公精神上的疾苦,而治疗方法则是无情的自我剖析,努力让这种病症成为描述和反映的客观对象。尽管书中暴露了一系列危机综合征,对于自我病痛的批判也是绝不妥协,但我们仍然可以断定,这部杰作与其说是关于病痛本身的,不如说是关于疗伤之路的,是关于如何摆脱“疾病”的,这才是作家常常予以关注的要点。在瑞士出版的《荒原狼》的后记中,黑塞这样写道:“自然,我不能,也不想规定我的读者应该怎样理解我讲述的故事。让他们每个人自己选取自认为是合适的和需要的东西吧!而如果大部分读者发现,‘荒原狼’的故事虽然也反映了疾病和危机,但却不是引向死亡的疾病,不是毁灭,而是其反面——治愈和康复,那么我将十分高兴。”
与此相关,应该指出有两个直接反映出作品具有自传性的实证:第一,作家在1926年年初曾和苏黎世著名的心理学家容格的学生,朗格博士,进行过几次心理分析方面的谈话,这些谈话无疑对作家在小说中描写如何寻找摆脱或克服精神危机的出路和方法产生了影响,当然,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小说的主人公当时都深陷这样的危机之中。第二个自传证据是书中所描绘的那个“初步感觉”的世界,这是那些年里黑塞在爵士乐中、在时髦的美国舞蹈中、在20年代的瑞士城市的夜生活中发现的一个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世界。黑塞曾经专门向舞者尤利娅·拉乌比-奥涅加(《荒原狼》中赫尔米娜的原型)学过跳舞,并且常常出现在苏黎世的纵情狂欢活动和化装舞会上。而那种笼罩着肉欲和令人迷醉氛围的通宵舞会,黑塞则在一家叫“伯罗拉克”的宾馆里特别体验过,其场景在小说中,通过作家对在“地球仪”舞厅举办的舞会的描述得以再现。
《荒原狼》脱稿于1927年1月,五个月之后,在作家生日前夕,该长篇小说由费歇尔出版社出版。
荒原狼这一形象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在作家创作中只有其历史发展的象征符号。狼的主题第一次出现是在黑塞的一个现实主义的小短篇《狼》(1907)中,它讲述了一头小兽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被瑞士乡村的农民们追猎并杀死的过程。后来,在20年代初,黑塞常常自比为落入圈套的“荒原野兽”,力图挣脱出来奔向自由,却又“迷失在文明的丛林中”,总在思念辽阔的“故乡草原”。然而这一“狼”的象征符号以在长篇小数中呈现的那个样子出现,还是在1925年出版的日记体抒情诗集《危机》中。
荒原狼这一象征符号除了具有隐喻的意义,至少还具有其他三重意义:神话学意义、哲学意义和心理学意义。
首先,在神话学意义上,狼是一个动物符号,常常出现在各民族的神话故事中,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恶魔的化身,是不屈从的夏娃的化身。在中世纪基督教的符号体系中,“狼”常常被等同于魔鬼,而在20世纪的文学中情况也是如此。
在哲学的意义上,“荒原狼”这一象征符号关涉到尼采的关于群居人和“差异性个体”之间的对比的论述,这种个体尼采在个别情况下称其为“野兽”,也会称其为“天才”。“狼”是从自我分析的斗争与冲突中诞生于世的,它同时也表现为要把狄奥尼索斯的感性世界从存在了多个世纪的基督教文明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努力,是个人渴望精神自由的表达。
在心理学层面上,“荒原狼”似乎代表了人的心理中通常被认为是被压抑到潜意识里的那部分。既然在小说《荒原狼》中讲到了消除内心生活的矛盾,讲到要达到心理和精神的完整、和谐、统一,那么“狼”的符号就指向了主人公心理的黑暗部分,它该从意识的深处被导引出来,该让它与有意识的生活进行和解。所以重要的是要理解,个人身体里“狼”的那部分的发展,在黑塞的这部长篇小说里,不是表现为人的堕落,而是对创造和谐、完整个性这一过程的推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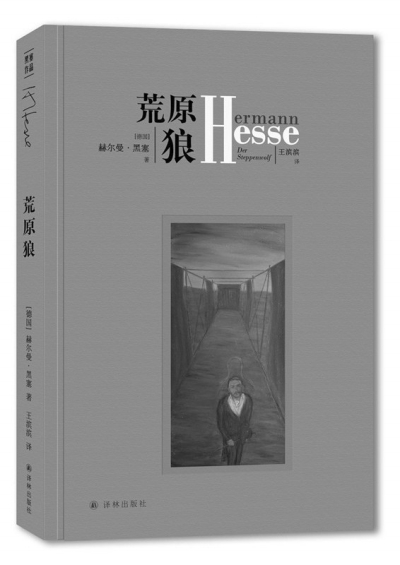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