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旅美科学史博士,《杂藏静思》作者) 傅玉芳(上海大学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
方向:处于无缝时代,微信让我们人在天涯,依然获得高朋满座的幻觉。最近,我在国外学术旅行,第一时间收到国内朋友转发的消息,《杂藏静思》入围2015年度中国影响力推展书籍艺术类书目。虽说本书是我三十年业余爱好厚积薄发的收获,但还是要与上海大学出版社分享,我认为本书是我们共同修炼的出版成果。
傅玉芳:确实如您所说,本书对上海大学出版社,同样意义重大,是我社产品第一次入围年度中国影响力推展书籍。由此可见,我们在《杂藏静思》的选题、编辑和出版等组织工作上,是有眼光、有实力的。但是归根结底,一部好的书稿还是出版的基础。
方向:尽管《杂藏静思》是我专业之外所作的大众阅读文本,而且还以笔名著述。但是,我在此书的准备与写作上,所花功夫绝对不亚于本职专业研究项目。最近几年,出于对考古、收藏类阅读的钟爱,我发现自沈从文先生、王世襄先生驾鹤西去,很难找到国内原创的、高雅的、适合大众阅读的收藏艺术专著。重构大众收藏出版内涵,是督促我用心写作的原因之一。
傅玉芳:早在阅读初稿时,编辑团队已经注意到,你在字里行间注重提升同类出版物阅读内涵的用意。本书前言标题“收藏·历史——藏品升值与学识沉淀”,已经充分表露了你的写作本意。正如你所说:“本书无意建构高深理论,重点在于和大家分享一个体会:收藏的魅力在于发现,发现的基础在于学识,成功的收藏青睐有学识支撑的藏家。”
方向:是的,当一项休闲或者经营活动,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继而群起仿效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十分的警惕与谨慎。按照个人经验,每逢关键时刻,惟有提升自我与提升藏品,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重要选择。一个随波逐流的收藏市场弄潮儿,最终被资本鳄鱼撕裂成千创百孔,在我30年经历中,见得太多了。好在收藏升值是一项所谓的文化盛宴,与股市、期货等纯金融技巧大大地不同,这就给有科学知识、爱文化历史的朋友,提供了用武之地。
收藏爱好者面临的首要核心疑问是,为啥收藏。老话说,古董玩家“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其实这句话只讲了一半,而且把最重要的一半遗漏了,结果制造了多少白日梦障碍者,耽误了多少幸福家庭本该祥和的生活。这句破釜沉舟的暗示,几乎冲着收藏过程的部分特点,无限夸大。勒紧裤腰带过了三年日思夜盼的煎熬日子,即使如愿将商品脱手,扪心自问,幸福在哪里?好日子去哪了?万一,三年后继续没有开张的话呐。所以,本书的第一部分开门见山,强调收藏的使用功能是“居有所依”,其实还包括了“思有所依”“读有所依”等融入日常生活的居家启示,提倡不影响基本生活,甚至改善日常生活等收藏元素。反对矮化收藏活动,仅仅将其理解为继房地产、金融投资以外的第三项投资理财渠道。我们不妨仔细观察围筑在大家生活圈的财经类媒体,正在有意无意地诱导大众收藏和金融投资密切挂钩。除了股票期货、黄金外汇,艺术品收藏居然也是财经投资大嘴巴们推荐的主要生财板块。试问,真有艺术和铜钱双栖的理财顾问吗?
傅玉芳:作为出版人,当初我们确实担心本书,一不小心就会做成市侩气十足的商业推销广告,类似充塞屏幕与网络的杂烩宝鉴,已经成了声誉扫地的鸡肋制品。读了你的初稿以后,我们发现事先的顾虑完全不必要。这样独创的深度写作,有史料、有启发,确实独树一帜。
方向:写作之前,我确实是认真做了读者调查的。以往,大部分的高端博物馆藏品录,主张客观的以图说话,目录式标注。这种传统的高大上收藏家模式,其实是针对收藏圈内人士的做派。行家一般自以为是,讲究有图即有料,此处无声胜有声,点到为止。但对于大众读者,这样的收藏类版本就是瞎子摸象,摸到哪里算那里。藏品图像背后的关键线索、举一反三的思维模式,在隐而不语的猜谜式阅读中,脑洞越来越模糊,收藏变得越来越神秘了。
而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研究的考古学与博物馆专家学者,基本上与大众藏家奔波在不同的跑道上。他们有各自的专业,有来自单位的研究考核要求,书写大众阅读文本,在目前的建制化学术体制内,对专家的生存与提升毫无帮助。或者,他们已经形成的技术性写作路径,也不一定适合深入浅出,书写既针对收藏热点,又满足轻松阅读的大众文本。
傅玉芳:我们注意到,除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积累和人类社会渐进的历史眼光,其实你也是个眼光独特的藏家,是否可以概括一下你的个人藏品特色。
方向:本书开宗明义,本人不是收藏家,不开博物馆,“把收藏体验当作历史来记录,是作者的写作初衷。本书仅仅展示了24件藏品,可见本意不在炫耀家底”。但是我也愿意强调,毕竟我从事科学史研究,涉及技术工艺的艺术品,理论上我必须有所涉略、关注和研究,最起码,对技术与艺术的鉴赏力,沉淀了三十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藏品还是有个性化特点的。
比如说,对于三十年前不被重视的景德镇浅绛画派瓷器,以及随后形成的珠山八友作品,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家族后代,我曾是这类藏品的慧眼识珠领路人。以我的“得月阁”珍品目录为例,程门、王少维、李子乔、蟠溪氏四位御笔高手合作的四方粉彩浅绛帽筒,有资格与景德镇瓷艺重器并肩而立,完整讲述中国瓷艺发展的血脉基因。
我的木器收藏也有些许特色。在紫檀、老酸枝狂热的时候,我已开始关注金丝楠等传统白木构件与家具。明末清初的早期工匠作品不仅用料巨大、而且格局大气。作为有机材料,金丝楠等植物类艺术品,在我的话语体系中,不仅是形于外的技术遗物,而且是秀于内的生命守望。从我擅长的生命科学史入手,在有图有史实地重构中国传统医学和养生理论中,得以借助此类藏品,回顾那些业已湮没的陈年往事。
其实,收藏于我是无心插柳,30年后柳枝成荫。当初源自初生牛犊的收藏好奇,本无商业企图。但是岁月流逝,无价的时间痕迹全部浓缩在用心选择的藏品之中。比如我在对医学史,尤其是眼科学的纯专业研究中,自然不断关注、收集传统眼镜,最早的制品可以追溯到明代,其镜片都是宝石级的用料。现在重新整理,发现得来全不费功夫,藏品价值自成系列。
傅玉芳:你的一半人生,是在海外学习生活。所以,你了解中西方文化,也懂得如何在西方世界,寻找华夏文化遗存。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为拯救海外流失珍品,贡献不少。
方向:您对我的表扬太客气了。一直以来,旅外侨胞都有强烈的爱国心。这种心境,人在国内是很难体验的。所以,我的所作所为,只是本分而已。让我们还是回到学术角度,从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西学东渐的视角,来解释《杂藏静思》的这部分写作内容。
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的第一批学人,我自然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有关国门开启、幼童留美、庚款留洋、华工出洋和洋务考察、操办洋务、出使西洋等历史细节。截至90年代初,美国华埠其实依旧相当封闭,既与美国主流社会沟通不畅,也与中国大陆沟通不畅。其结果是,华埠忽隐忽现早期华人移民社会的投影。比如唐人街女士的对襟服饰,老式家庭的黄花梨家具,这些文化符号,对100年前收入就已达美国中等水平的华人商家而言,习以为常。当年回到广东台山省亲,光宗耀祖地购置一些海南岛硬木家具等土特产,就像如今侨胞挑几幅真丝绸缎一样普通。100年后黄花梨稀缺了,造就了一批富翁。海外寻宝既有主动接触东方文化家庭模式,也有举牌世界一流拍卖行模式。
还是科学史权威江晓原教授原话一针见血,以科学史和科学文化开拓收藏视野,有助全面提升鉴赏层次。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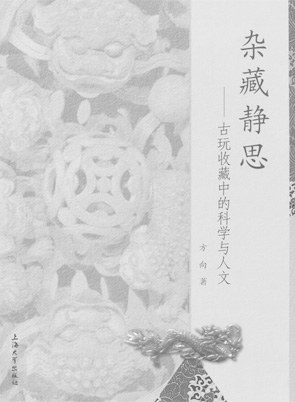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