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曾说:兴师动众的悼念是为了尽快地遗忘。但对一些至亲而言,死者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记忆可以伴其一生。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1936年生于巴黎,父母是在法国生活的波兰犹太人。在他四岁时,父亲死于“二战”战场;六岁时,母亲在一次大搜捕中被虏,后来亡于集中营。幼失怙恃的人生际遇深刻影响了佩雷克日后的创作。
在1975年发表的半虚构半自传性作品《W或童年回忆》里,佩雷克说:“我没有童年回忆。”战争遗孤的童年不言自明。不止于此,作者借助几张父母旧照、亲戚们的口述,以及诸多不确定的回忆与想象写就的个人童年史,似乎已完全湮没于笼统的大历史而无需赘述,“另一段历史,那段大历史,举着它巨大的斧头……战争、集中营”。有很长一段时间,佩雷克将自己“固守在一个孤儿的无辜形象中”。书中原封不动摘抄了他二十多岁时回忆父母的文章,十五年后,他对当年的文字加了些自认为必要的注释和评论。尽管作者说自己“只是在作无止境的重复”,但随着时光流逝,那些包裹在“陈词滥调”里的记忆碎片,在日益揭开的历史真相面前愈加显出分量,就像年近不惑的佩雷克所说:“找到它们愤怒的沉默,还有我沉默的愤怒。”
佩雷克的母亲没有墓碑。他起先以为1943年关在德朗西的母亲是第二年被运往波兰奥斯维辛后去世的。但在多年后的注释中,他又写道:“1958年11月13日,一项法令才正式宣布她死于1943年2月11日德朗西(法国)集中营。”葬身之地的“扑朔迷离”暗合着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在很长时间里法国官方都语焉不详。众所周知,“二战”对于犹太人不啻为灭顶之灾。在各种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活动中,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其中包括150万儿童。而当时战败的法国在维希政府的旗号下,助纣为虐,沦为侵略者的帮凶。维希领导人让法国警察、民兵与德军合作,特别是在巴黎地区,大肆搜捕犹太人,协助进行“最终解决方案”——德国纳粹提出的对欧洲犹太人系统化地实施种族灭绝的计划。维希政府将78000多名犹太人(包括上万名儿童)关押在巴黎东北郊的德朗西集中营,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用原本装运牲口的货车、分76批次将这些人再押送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战后仅有约2500人生还。在国家暴政铺就的天罗地网里,被捕的法国犹太人可能死于国内或国外的集中营,也可能死在押运途中,甚或死在最末随纳粹逃亡的撤退迁徙中。巴黎解放当天,戴高乐将军宣布维希政权无效。多年来,官方一以贯之沿袭这一“历史空白说”,维希法国和纳粹德国狼狈为奸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俨然禁区。“1959年11月17日的法令又明确指出,‘如果她拥有法国国籍’,她将有权加上‘她为法兰西献身’。”戴高乐总统时期,这条充满政治策略的法令赐予佩雷克母亲的“殊荣”,在今天看来,荒谬得让人痛心。
支离破碎的童年回忆不足以酣畅表达作者的心声,佩雷克将更多的思想天才般的融入两个假想文本:海难事件和“体育国”W岛。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后两则故事看似断裂跳跃,实则拥有相通的精神逻辑。
先说W岛。作者以上帝式的全知全能视角描述了一座狂热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理想的岛屿W。W的运动员参加各项体育比赛,为荣誉、为特权、为最基本的生存竞技厮杀,拉帮结派,弱肉强食,直至生命耗尽都对奴役他们的W体制懵懂无知。
再谈海难。佩雷克如写悬疑小说般娓娓道来的故事其实异常残酷。一真一假两个加斯帕·文克莱:假的是个年轻的孤儿,通过拒服兵役者组织使用真人加斯帕·文克莱的名字伪造证件,从而成功逃脱所服兵役,真的那个是后天聋哑(病因可能是童年的心灵创伤)且自闭的孩子,其母亲为享誉国际的歌剧演唱家。在为治愈儿子而持续数年却收效甚微的海上环球之旅中,海难降临——其他人都死了,孩子却神秘地失踪了。调查者根据失事地点、船速、航海日志推测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在极度混乱、集体恐慌中巨轮冒险折回(去找孩子?)而引发海难,在此之前孩子已不在船上,他可能是自己逃跑了,也可能是,被丢弃了。没有明确答案,但作者不厌其烦地对其他遇难者尤其是孩子母亲如同天谴般的死亡场景所作的恐怖描述,冥冥中给结局的天平倾向增加了致命的重量。
“孤儿”是解读《W或童年回忆》的密码。书中的“加斯帕·文克莱”与欧洲文学中的原型人物加斯帕·豪斯(KasparHauser)遥相呼应。后者真实存在,是个身世成谜、自幼遭弃的弱智少年,1828年突然出现在德国纽伦堡街头,1833年被刺杀身亡。这个被称作“欧洲的孤儿”的“加斯帕”弥散在佩雷克的精神血液里:他是作者本人,他是船上失踪的聋哑儿,他是W岛奴隶般的运动员,他是“二战”备受摧残的欧洲犹太人……
将弱势的“加斯帕们”淘汰出局的理念由来已久。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公然宣称:“劣等父母的子女,或者是优秀父母的残疾子女,则应该理所当然地被弃于神秘而不为人知的地方。”佩雷克笔下的海难事件俨然柏拉图观点的实践操作,而20世纪的德国纳粹变本加厉将其推向极端。希特勒奉行种族优生政策,妄图“清洗”德国民族里所有“不健全的元素”。“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T-4行动(“安乐死”计划)通过决定性的医学检查,将至少20万名在身体或精神方面有残疾的人判为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病人,用施药、饥饿、毒气等方式予以屠杀,这些人包括残疾人、智障者、精神分裂症、癫痫症、侏儒症、亨廷顿舞蹈症患者、同性恋,等等。 行动发展到后来,犹太人、吉卜赛人、波兰人、斯拉夫人等也作为“劣种人”而惨遭屠戮。
佩雷克苦心构建的W岛,并不仅仅是集中营的隐喻。任何一个遵循丛林法则的社会,都带有W的印记。W根植在人类集体疯狂的历史记忆中。《W或童年回忆》里,唱歌剧的母亲为治好聋哑的孩子带其航行各地,可以当作人类疗治战争创伤的寓言:向外寻找药方是徒劳的,因为治愈的彼岸根本就不存在;而遗忘也是不可能的,选择抹杀记忆(弃子)只能导致毁灭(海难)。徘徊于茫茫的历史海洋,进退维谷的人类究竟该何去何从?
佩雷克英年早逝,1982年死于肺癌。时隔13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终于打破长久以来的官方沉默,承认当年维希法国是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同谋。200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向部分在“二战”期间营救过犹太人的“法国正义者”授予荣誉勋团勋位。是他们,帮助当时法国四分之三的犹太人逃脱了被送往纳粹集中营的悲惨命运。迟到的这一切,在告慰亡灵的同时,似乎也隐隐彰显出真理的面相: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应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国家暴政才有可能避免——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此。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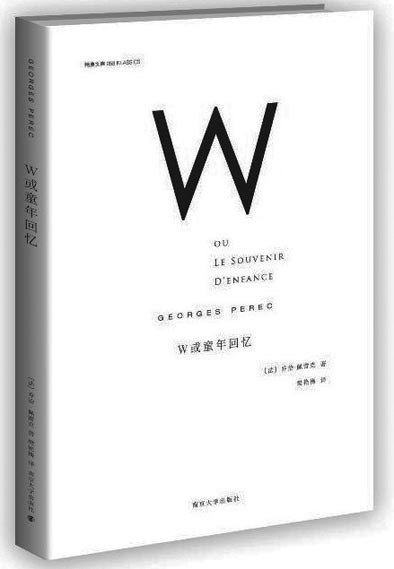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