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先秦文献,必须要重视异文,这些异文对于探求文本原貌、准确地理解文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诗经》来说,尤其如此。
先秦时期的《诗》文原本现在已无法得见,不过,我们从先秦时期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称《诗》引《诗》的情况,以及既有的古文字研究成果来看,因时间、地域的不同,其间肯定存在大量异文。现在可以见到最早的《诗经》文本是1977年出土的阜阳汉简《诗经》残本,全本则有唐开成石经《诗经》。将它们与今本相比,其间存在不少异文,而它们与先秦时期的古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更大。
自汉代起,学者就已经开始对《诗经》异文加以关注。汉代传《诗经》学的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齐鲁韩三家是今文经学,而《毛诗》是古文经学。汉代的《诗经》文本于今古文之间,甚至今文经学的每一家之间,在文字上应当都有一定的差异。当时传《诗》者应当知晓,各家各派所传的《诗经》在文本上存在有一些异文。不过,据现在仅有的资料可推知,应当是直到郑玄才对这些异文的学术价值有所关注。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其中有一篇《书证》,涉及当时《诗经》江南本与河北本在文字上的差异,这几处差异可能与南北学之不同有关。这是典籍中首次对《诗经》不同版本中异文的关注。比他稍后的陆德明,著有《经典释文》,其中有《毛诗音义》三卷,搜集了《毛诗》的不同版本间的异文,还搜集了《韩诗》中的一些异文。正因为当时《诗经》异文众多,影响阅读,唐人颜师古作《诗经定本》,以勘正文字。
《三家诗》于六朝时期逐渐失传,但是,其中有些文句保持在其他书中。南宋人朱熹曾有从《文选注》中辑录《韩诗》异文的想法,虽一直并未成专书,不过,他对《诗经》异文已有所关注则是无疑的。王应麟继朱熹之志,勒成《诗考》一书,是首部对《三家诗》异文搜集与研究并重的著作。随着文字学的发展,对《诗经》异文的辑录与研究,到清代已蔚为大观,主要表现在参与的学者众多,取得的成果丰硕。比如,专门以《诗经》异文为研究对象的就有:陈乔枞《四家诗异文考》、黄位清《诗异文录》、冯登府《三家诗异文考证》、李富孙《诗经异文释》、陈玉澍《毛诗异文笺》等;延至民国,有江瀚《诗经四家异文考补》、张慎仪《诗经异文补释》等。
还有很多诗经学著作涉及《诗经》异文的考证与研究,较为著名的有阮元《三家诗补遗》、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冯登府《三家诗遗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此外,一些笔记著作也涉及《诗经》异文。
前儒研究《诗经》异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将异文与今古文经过度地联系起来,以及过度突出本字、正字的概念,对异文形成的复杂原因认识不够。比如,被视为今文《诗经》学集大成的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将诸多异文归之于学派归属的差异,动辄以为某字属“鲁诗”、某字属“齐诗”、某字属“韩诗”,这就很成问题。很多时候,异文并非因齐鲁韩毛四家之间学派不同而产生的。先秦文献距现在时代久远,文字字体发生了好几次重大变化,文献载体也发生过几次转折,这就决定了异文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究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一是文字自身变化而产生的不同字形。比如,战国时代,齐系文字、晋系文字、秦系文字、楚系文字和燕系文字等在字形上有一定差异;秦始皇统一文字、隶古定、隶书楷化、俗字变为正体等等,都会在字形上产生一些变化,从而形成异文。比如,“昴”和“图1”,就是同一个古文字字形隶定出来的两个新字形。二是古今字,以及后世产生累增字、区别字,甚至避讳字等产生的异文。如“辗转”,本写作“展转”,“辗”是后世类化所产生的新字。三是后世文献中的同义转写。前人引文,有时会把古奥难懂的字词用当时通行的字词转写,这也导致了一些异文的产生。比如,先秦时期不、弗在用法上是有差异的,但是这个差异在汉代就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才会出现把“瞻望弗及”写成“瞻望不及”。四是传抄刊刻时产生的有意、无意或随意的更改,以及讹误。有时候,书手的书写心理不同或者写了错别字等情况,也会产生一些异文。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无需举例。
时至今日,学者对于《诗经》异文的研究取得了较前人更为深入的成果,撰成专书的有:台湾学者朱廷献《诗经异文集证》(1984年自印本)、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程燕《诗经异文辑考》(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也有不少论文涉及《诗经》异文的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两类。阜阳汉简《诗经》出土后约十年,整理者胡平生、韩自强发表《阜阳汉简〈诗经〉简论》,其中有对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异文的专门考察。此后,陆续有学者发表讨论阜阳汉简《诗经》异文的论文。这是一类。虞万里的《六朝〈毛诗〉异文所见经师传承与历史层次——以陆德明〈毛诗音义〉为例》(载第四届国际汉学论文集《出土材料与新视野》,台北,2013年)、《〈诗经〉异文与经师训诂文本探赜》(《文史》2014年第一辑),将六朝时期《毛诗》文本中异文的类型、产生原因与历史层次加以考察,并将其与汉儒传《诗》的家法师法联系起来。这其实探讨的是文字隶定以后的写本时期的《诗经》异文。因为隶定前与隶定后、写本时期与刻本时期的异文,无论是产生原因,还是表现形态,都有着明显不同。这又是一类。
在当下的《诗经》异文研究中,还有一本专著需要特别表出的,就是袁梅先生的《诗经异文汇考辨证》。总体看来,该书主要的突出之处有:
一是搜罗宏富。《诗经》流传久远,自先秦时期,时人就有称引《诗》文的习惯。汉代尊《诗》为经后,其地位更为学者推崇。因此,很多典籍都有引用《诗经》的情况。该书对传世文献中涉及《诗经》方面的异文进行了尽可能的搜集,也适当关注了出土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异文进行分析,是迄今为止,对《诗经》异文搜罗最为全面的一部专书。其中所引用的书遍涉经史子集四部,有历代《诗经》学名著,有石经研究著作,有语文学专著,有类书,也有今人的甲金文字专著等等。比如,《周南·汝坟》“惄如调饥”,这里的“调”,陆德明《经典释文》录一异文“輖”。这个词的意思,前人也有些争论。曾良《俗字与古籍文字通例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在目验了敦煌写卷的基础上提出,“輖”在敦煌文献中当是作“(图2)”,其实就是“朝”的俗字。袁梅先生在该书中指出《经典释文》中的“輖”应作“(图2)”,《蜀石经》《说文钞》《五音韵谱》所引《诗》文皆作“(图2)”。这就为曾良说提供了传世文献的证据。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韭花帖》中有“昼寝乍兴,(图2)饥正甚”,字正作“(图2)”。由此可见,“輖”本当作“(图2)”,是“(图2)”的俗字。曾良的观点是正确的。《毛诗》作“调”,是“(图2)”的同音假借字,二字草书字形也比较接近,这个“调”,可以训作朝,也就是早晨的意思。
二是全面爬梳。《诗经》历时久远,其中产生异文的情况又比较复杂,这就需要我们对其逐一考察,梳理相关文献,再在此基础上加以辨析,以期对异文产生的原因得出趋于合理的认识,并借以尽可能地厘清《诗经》文本的历史层次。该书在全面搜罗异文的基础上,对异文产生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爬梳,得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比如,《邶风·谷风》“黾勉同心”,这里的“黾勉”是双声联绵词,其字形无定,典籍中还可以见到如“密勿”“蠠没”等写法。袁先生对典籍中“黾勉”的不同写法作了勾稽,并指出《毛诗》“黾勉”使用最为广泛。又如,对《卫风·硕人》“衣锦褧衣”中“褧”字、《唐风·山有枢》“枢”“娄”“宛”字、《唐风·扬之水》“凿”字等等异文的梳理,广泛征引相关文献,作出分析,皆可见其爬梳之全面。此外,有些异文,历代说解颇多,各持己见,纠葛纷扰,莫衷一是,袁先生并不多录他说,仅录一二可用之说。如,《邶风·泉水》“出宿于泲”,《列女传》有异文作“济”。袁先生只引用段玉裁说,以为典籍中二字并用,并下按语,以二字为一字异体,甚是。还有些异文,历代说法大同小异,但未必得其要领。比如,《鄘风·柏舟》“实维我特”,《韩诗》“特”作“直”,诸家多说二字字异义同。袁先生则据《魏风·伐檀》直、特为韵,指出二字音近通假。我们知道,用作虚词时,特、直也都有仅仅、只不过的意思。音近通假较前人的字异义同说更精确。
三是准确辨析。该书既名之为“辨证”,其中自然要对所搜集的诸多异文加以辨析、考证,而这正是最能体现作者功力之处。比如,《周南·关雎》“钟鼓乐之”,这里的“钟”,写成繁体字是“鍾”,但是明监本作“鐘”。按照通行说法,鍾、鐘二字有别,指乐器的是“鐘”,“鍾”则一般用于钟情、钟意之类。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这两个字解释说:“鍾,酒器也。”“鐘,乐钟也。”还有个说法,也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钱钟书先生说他名字中的那个“鍾”字不能简化,否则就不能表达钟情于书的意思了。于是,很多出版物中就出现了“钱锺书”这样的字形。袁先生在该书中,对金文中的鍾、鐘二字加以考察,指出其中的“鍾”是“鐘”的或体。再对《诗经》中出现了16次的“鍾”加以分析,指出它“多为乐器之名”,或引申指“钟鼓之声”。所以,明监本中的“鐘”字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目。其实,这两个字混用,在其他的传世文献中也可见到,比如《左传》《荀子》中就用“鍾”来表示乐器名称,而《淮南子》中也有用“鐘”表示容量单位。这同时就暗示我们,汉中期以前的鍾、鐘二字在字形上有别,而用法上则混同;二字字义上有明确区分,可能至早要到汉代中后期才产生。许慎《说文解字》所作的区分,可能是出于对汉代用法已然有别,或者《说文》撰著体例的考虑,并不符合先秦文献中用字的实际情况。一些字典辞书,如《王力古汉语字典》等以为二字互相假借,亦不如袁先生的或体说稳妥。
此外,该书将《诗经》中所有异文的条目和单字列出,具有索引的功能,颇便于学者翻检使用。
当然,不可避免地,该书也存在一些小问题。首先,袁先生年事已高,完成此书时已经88岁高龄,有时候知识不能及时更新,从而产生一些本不必要的失误。比如,该书有《错简质疑》一篇,作为附录,袁先生的按语很见功力。不过,据现有出土文献的情况,一般竹简的背面会有划痕或者明确的顺序标记,这样出现错简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会存在的。而且,从《诗经》的传承情况来看,在汉代出现错简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其次,还有些地方判别错误。比如《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李”,《白孔六帖》引此作“邱中有黍”。袁先生以“黍”是“李”的譌字,很正确。但说丘、邱为古今字则不够正确了。考袁先生所引《白孔六帖》为《四库全书》本,而清人为避孔丘讳,或缺笔,或改作“邱”。还有,书中也有少数异文没有列出。比如,《邶风·燕燕》“瞻望弗及”,阜阳汉简《诗经》作“彰望”,是音近通假。该书于此一异文失录。
尽管该书存在一些小的问题,不过小瑕不掩大瑜,作者搜罗之全、爬梳之勤和辨析之精等都值得表出。袁先生专守一经数十年,早在1985年就在齐鲁书社出版过《诗经译注》一书,在学术界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又以耄耋之龄,健笔凌云,完成这部逾70万言的巨著,其学术价值自然不容小觑。袁先生身居齐鲁大地,为孔孟之乡,孔子说:“知者乐,仁者寿。”袁先生执着于《诗经》研究数十年,以智得乐,以仁享寿,以88岁高龄完成了这部《诗经异文汇考辨证》。该书的出版,令我们感动的,并不仅仅是袁先生以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嘉惠学林,更在于袁先生以坚守执着、勤勉学术的奉献精神,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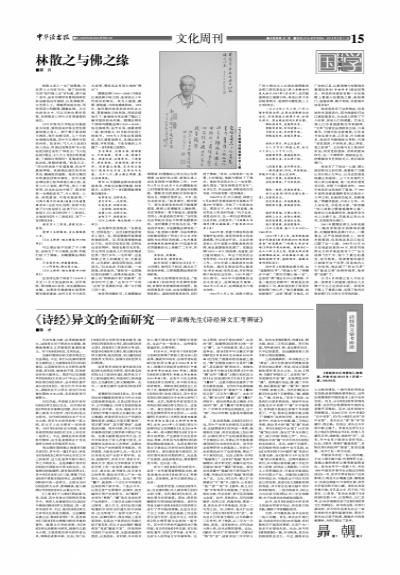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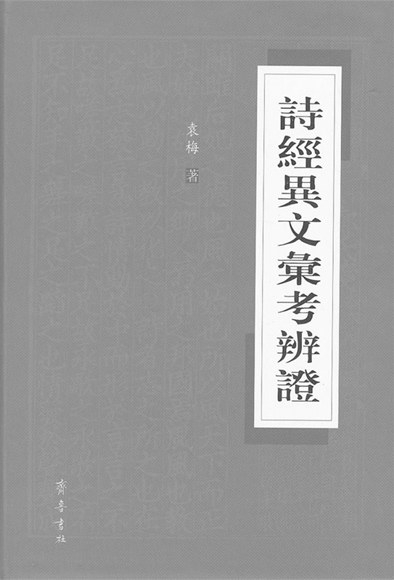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