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时期起,有一批大师不远万里,亲临中国,通过讲演、谈话和著述,带来新学说,传播新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的名字是:内山完造、杜威、罗素、泰戈尔、萧伯纳、萨特与西蒙·波伏娃。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的“亲历中国丛书”,收集了这些大师的讲演和谈话,记录了他们在华活动的行迹,选编了当时及之后的种种评论,以纪念这些大师,回望我们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
他们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
这些大师之中,来华时间最早的是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从1913年到1945年,他长期住在上海,广泛接触中下层民众,成为杂学大家,著有《活中国的姿态》,并与鲁迅等人相交甚厚;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11日在华讲学,留下著名的《杜威五大讲演》;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在华讲学,留下轰动一时的《罗素五大讲演》和后来的《中国问题》;印度文学家泰戈尔,1924年4月12日至1924年5月30日在华,发表了《在中国的谈话》;英国文豪萧伯纳,1933年2月来华,引起了各方关注;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西蒙·波伏娃,1955年9月访华,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国的国庆庆典。
这些亲临中国的大家持有的各不相同的中国观,很值得我们重视。
如果说内山完造并不是某一方面的“大家”,那么,他的的确确是一位“杂学大家”。他“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长期接触长江沿岸中下层民众,对中国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开书店,使内山完造得以博览群书;书店内“漫谈会”的交流探讨,又使内山完造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观。因而,他的“漫文”,从鲜活的现实出发,注重中日文化的对比,观察细致,立意深刻,文笔生动,充分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鲁迅先生高度称赞:“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真相,介绍给日本的读者的”,称“内山氏的书,是另外一种目的,他所举的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
罗素访华回国后,曾在英文报纸发表不少文章,阐述他的中国观。1922年,他出版了自己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罗素以其博大精深的思考和豁达坦诚的心态,为西方读者系统阐述了中国问题:立足中国的立场,谈中国的政治、经济、工业和教育,又一次呼唤中国重视实
业、重视教育,呼唤“少年中国”的崛起。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初撰写的著名的《民族主义》一文中,评价罗素是真正了解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方人之一:“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样的人,有很好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欧美,才赞美中国。”
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语言如诗一般流畅,充分表达了泰戈尔的哲学观和文学观,同时表达了他对东方文明、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之情,强调在教育中要注重自由、个性和人格,呼吁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注重理性和人类和平。
萨特则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高度称赞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西蒙·波伏娃更是出版专著《长征》,以亲身经历和大量事实,记录中国之行,介绍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是大师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他们总是在比较之中探究这个问题。
内山完造在中日两国之间作了对比。内山完造指出:“日本人的生活是直线的,所以名日本人的生活为直线生活,支那人的生活是曲线的,所以名支那人的生活为曲线生活。”鲁迅先生同意这个观点:“中国四万万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行的不认真的态度。”
内山完造充分肯定了中国下层百姓的一些优良品质,比如同情穷人、互相扶助、互相团结等等。这样的文章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以至于鲁迅先生评论该书“太偏于写中国的优点了”。同时,他揭示了中国国民性的缺点,比如缺乏公众精神、爱占便宜等等,不少文字相当犀利。在这方面,他与鲁迅先生的文章即使不能说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互相映衬,互相影响,其中不少是“漫谈会”的结晶。
罗素则专门写了《中国人的性格》一章,称赞中国人的快乐、冷静、安详。同时,他也坦言中国人的缺点:怯懦、贪婪和爱面子。他充分肯定“少年中国”的进取精神,认为“现在中国的青年,颇富于进取的精神,是件可喜的事”。对于西化问题,他认为“中国人要不去专事摹拟西方的方法,始可为自己的国家或世界图谋幸福”。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旧文化时,他又重申:“既不要盲从西方的文化,也不要保存中国残留的文化。”他主张中国办教育、办实业,提倡爱国精神、公共精神和民主精神。
做中国人的朋友,关注中国的前途
内山完造是中日两国友好活动的先驱,曾经多次保护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后来,他又担任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1959年9月,内山完造来中国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因病逝世于北京。按他的遗愿,一半骨灰葬在上海的万国公墓。
罗素对中国也十分友好。他自幼便从父辈的藏书中了解中国文明。在国际问题上,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谴责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并曾在1962年中印边界问题上,担任中印双方的调停人,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1937年他致电蔡元培先生,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我和我的人民完完全全的同情你们国家。”同年,在写给日本“爱国诗人”野口米次郎的公开信中,他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认为“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日本今日之所作所为,将自食其果”。他于1938年6月发表《致中国人民书》,再次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表示声援。周恩来曾在1956年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时予以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有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萧伯纳对中国人民也一直十分友好。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他曾与人联名发表公开宣言,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1933年以77岁高龄访华时,在香港研究革命书籍,并劝导和鼓励青年学生投身革命。1943年,萧伯纳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电文写道:“中国之前途则已充满希望,愿勿令此希望复陷于失望。”
萨特认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而法国人民对这个“伟大国家”,“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直到1975年,萨特还在其《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中谈到中国。当记者问他“在你的同时代人中,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予以完全的器重?”他的回答是:“毛。我给予毛以完全的器重。”
他们在中国的命运起伏
这些大师的来华,尽管引起过轰动,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几十年来,杜威哲学在中国起起落落,从开始的盲目崇拜,到后来的盲目否定,再到如今的“重读杜威”,可以说,杜威的理论伴随我们走过了这些岁月。
罗素访华时,没有从中国的现实政治着眼去谈“社会改造”,而是偏重于理论上的阐发。毫无疑问,中国的听众对罗素是失望的。正如罗素在1920年10月18日的信中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对报纸上出现的罗素主张教育和实业而非社会主义,陈独秀曾给罗素写信询问,但没有收到回信。毛泽东在湖南听了罗素的讲演,同样也感到失望,1920年12月1日他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说,他对罗素的主张的评论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泰戈尔访华引发了“泰戈尔热”,人们争相传阅泰戈尔的诗作。但另一方面,泰戈尔提倡东方文明,以及他的“泛爱”、“诗化人格”和宗教神秘主义,与当时复古派的“国粹主义”、“调和论”和“尊孔读经”、“整理国故”等论调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因此,有梁启超、徐志摩、郑振铎等欢迎和接受泰戈尔的主张,却也有人认为泰戈尔的观点与中国当时的现实政治脱节,而提出批评意见,有些文章语言还十分激烈。
泰戈尔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两种不同意见。一方面,他欣然在北京度过了他64岁的生日,接受了梁启超的赠名——竺震旦,并观看了自己的剧作《齐德拉》的演出;另一方面,他也在《告别辞》中表达了他的失望。不过,泰戈尔对中国仍然十分友好,在离开北京时,有人问他有没有失落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没有了,除了我的心。”
萨特和波伏娃访华时,他们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并没有广泛为人知晓。因此,萨特和波伏娃不免有些失望。萨特的存在主义广泛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是在萨特去世之后。1980年代中期,有一场关于存在主义的讨论和论争。正如“二战”之后存在主义在西方广泛传播有当时的社会心理原因一样,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迎合了刚刚从十年浩劫走过来的中国人的心理,因此颇为流行。然而,尽管萨特的哲学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一致的地方,他本人也曾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存在主义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论争便因此而起。
“亲历中国丛书”追寻大师行迹,记录大师风采,充分反映了这些大师的中国观,以及中国对这些大师曲折的认识过程,有助于我们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启发我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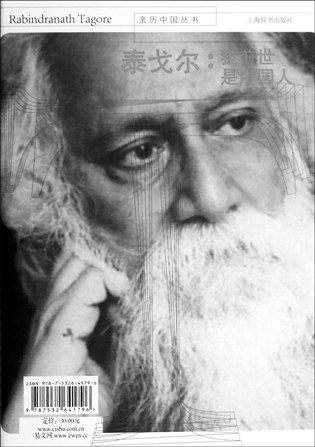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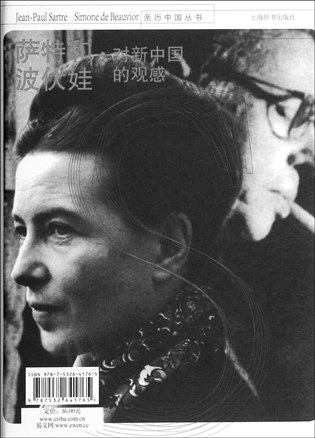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