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北京大学教授)
这些年持续关注的话题之一是经典阅读问题。
在各类文学经典中,诗歌阅读更是成为了20世纪的世界性难题,现代主义诗歌也由于所谓“晦涩”“难懂”以及鲜明的个人性成为“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西班牙诗人希门内斯语)的志业。如何透视诗人的文学思维和艺术逻辑,如何在诗人的自律法则、诗歌的内在逻辑与普通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之间搭建连通的桥梁,也同样构成了世纪性与世界性的难题。
洪子诚主编的《在北大课堂读诗(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的理念和设计也可以放在这个难题和背景中理解。洪子诚教授在北大主持的读诗课程,解诗的性质“和通常的诗歌赏析并不完全相同”,直面的正是“现代诗”与读者的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有关诗歌“晦涩”和“难懂”的问题。因此在北大课堂读诗的过程中,洪子诚和学生们一直保持对“读者意识”的关切。这种“读者意识”的自觉并非是完全以读者为本位,洪子诚认为:“在诗与读者的关系上,固然需要重点检讨诗的写作状况和问题,但‘读者’并非就永远占有天然的优越地位。他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阅读态度,了解诗歌变化的依据及其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洪子诚赞同“重新做一个读者”的说法,在北大开设诗歌阅读课的目的,“也是要从‘读者’的角度,看在态度、观念和方法等方面,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检讨”。
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注释版)》(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也表现出了同样的问题意识。注释版《凤凰》比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凤凰》多出了一百三十四条注释,注释文字加在一起有一万三千多字。由此《凤凰》也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可能性,即“注释性阅读”。欧阳江河认为,所谓“注释性阅读”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诗话式阅读,更从属于作者写作的一部分,有助于还原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表意实践的具体性。欧阳江河称:仅仅注意到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变化是不够的,一定要促成批评和阅读的变化。如果没有阅读的变化,就理解不了写作的全方位和深刻性。“仅用诗歌史上的某个诗人的标准阅读我的诗,是进不去的。如果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标准就读不出当代诗歌的复杂性和处理文明的抱负。当代新的诗歌写作对阅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注释性阅读也应运而生。当然,注释性阅读首先取决于文本的承受力,取决于注释对象内部的丰富与复杂的“玄机”。之所以给《凤凰》进行注释工作,也取决于《凤凰》是诗人精雕细刻的结果,字里行间也充满着设计感,暗藏大量指涉、典故、事件、“本事”、“重影”,其中很多微言大义只有作者才能提出解答,普通读者甚至与诗人不熟的专业读者也无法参详。对这首诗的背景知识的注释就成为一件必要的工作。而注释的工作并不意味着把刚刚问世的《凤凰》塑造成一个当代经典,而是说,既然诗人在劳作的过程中投入了如此多的精力,前后大约花了两年时间,七易其稿,也就期待同样的批评、阐释与阅读方式的变化。诗作者对文本创生过程的讲述本身就是一个循迹的过程,从而使注释也构成了写作的一部分。不用注释的方式,这些踪迹恐怕就无迹可寻。诗歌,尤其是篇幅浩繁的长诗,其实生存在细节和诗句的碎片中,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一目十行地泛读。
诗歌经典阅读的难题可能更表现
在对外国诗歌的阅读方面。普通读者必须经过翻译的中介,译本的优劣就显得相当关键了。而诗歌对译者的要求往往比小说类作品更高。这也是我相对而言更信任诗人亲身参与的翻译的原因。2014年阅读与重读诗人的翻译有《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诗集》(作家出版社2014年6月)、《重新注册——西川译诗选》以及台湾诗人陈黎翻译的《万物静默如谜——辛波斯卡诗选》。从诗人的翻译反观诗人自身,也成为一个不失有趣的视角。譬如对照王家新和西川,两个人的翻译对象的选择首先就耐人寻味。王家新译诗集汇集了诗人20余年的诗歌翻译,有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叶芝、奥登、阿米亥、策兰等,其中俄罗斯诗人尤其占了较大比重。从中可以见出王家新对经典认知的个人性尺度,见出翻译与王家新的诗歌生命之间的一体性:“我的翻译首先出自爱,出自一种生命的辨认。”“我最看重的技艺仍是‘精确’——尤其是那种高难度的、大师般的精确。纵然如此,翻译仍需要勇气,需要某种不同寻常的创造力,需要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在密切注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中‘承受自身语言降生的巨痛’。”相比之下,西川的胃口则更为驳杂。如果读者根据西川的译诗阐释西川自己的创作的话,那多半会掉进“影响”的陷阱。西川显然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陷阱,在译诗选的“说明”中西川写道:“没有这样的道理,即我翻译了谁的诗我就受到了谁的影响。我的阅读面比这些译诗要宽得多。”在为诗歌读者提供经典化和多元化诗歌翻译与阅读的意义上,王家新和西川堪称功不可没。
而从普及诗歌经典的意义上看,2014年被广泛关注的一本书是诗人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这是北岛有感于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朗诵节上朗读“伤害孩子们的想象空间”的诗歌,“把鼻子气歪了”之后,自己花了两三年的功夫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北岛认为:“让孩子天生的直觉和悟性,开启诗歌之门,越年轻越好。”这或许是第一本真正由诗人编选,从孩子们的阅读角度出发的诗选。
2014年的诗歌和诗歌研究著述的阅读是令人怀念的。最欣喜的诗歌阅读经验之一是读孙玉石教授编选的《林庚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林庚有大量的佚诗散见于当年的报刊杂志,新诗研究者每每以无法读到林庚全部的诗作而抱憾。这本《林庚诗集》不仅收录了林庚已经出版的六种诗集,最重要的价值是孙玉石独立完成搜集整理工作的《集外集》部分,有一百余首诗。此外,印象深刻的还有高恒文的《周作人与周门弟子》(大象出版社2014年7月),洪子诚主编的“汉园新诗批评文丛”中姜涛的《巴枯宁的手》、周瓒的《挣脱沉默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以及翟永明的《完成之后又怎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王家新的诗文集《塔可夫斯基的树1990——2003》,以及臧棣的诗集《小挽歌丛书》、欧阳江河的《黄山谷的豹》、蓝蓝的《蓝蓝诗选》、秦立彦的《地铁里的博尔赫斯》、陈均的《亮光集》、王东东的《空椅子》等。
2014年还集中翻阅了大量台湾诗人的著作。唐捐的《暗中》、杨佳娴的《金鸟》、简政珍的《放逐与口水的年代》、陈家带的《城市的灵魂》、曾淑美的《无愁君》、须文蔚的《魔术方块》等都给我以惊艳感。2014年10月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参加“两岸新诗国际论坛”以及随后在台北纪州庵参加“两岸新诗的分融与交流”以及“现代汉诗的当代处境”座谈会,深感台湾诗人在营建与读者交流的诗歌小环境和小传统方面倾注的热情和心力。或许在破解诗歌阅读这一世纪性兼世界性难题的过程中,台湾诗人已经走在了前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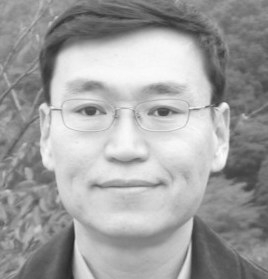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