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的香港,虽已是冬天了,但对我这个刚刚南下的人来说,却觉得天气相当不错。
这次应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邀请,来参加“书写中国翻译史”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一位来自日本的青年学者提交了讨论“解剖学”汉译源流的论文,中日文以及相关翻译的资料都相当丰富,显示出“翻译史”与“概念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巨大学术潜能。这篇论文提到,尽管早在1895年5月20日的《申报》上,一篇考察日本学校教育的文章(《日本学校考实》),介绍日本医科分科目时,“解剖”就作为学科名出现了:“医科分目五曰察验曰解剖曰内科曰外科曰目科”,然而,一直到1916年,联合医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才在有着德国和日本留学经验的汤尔和推动下,才把“解剖”作为“医学分科”的“科目”确定下来。姑且不论作为“学科名词”的“解剖学”为什么在近代中国需要花20年的时间才能得以确立,这背后当然有相当复杂的原因。仅就现象而言,意味着从专业的“医科教育”到普通的“新式教育”,可能都无法准确传授与现代“医学”或“卫生学”相匹配的“解剖学”知识。这也解释了鲁迅1904年求学于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时,教授“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为什么要特别关照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亲自为他批阅、修订课堂“讲义”,很显然,医学生鲁迅与老师藤野先生在仙台医专的相遇,并非简单的师生因缘,同时也显示出中日医学教育在“解剖学”知识上的“落差”。
更重要的是,熟悉鲁迅研究的人都知道,由于藤野先生给他修订讲义,以致于鲁迅的日本同学认为藤野有“漏题”之嫌,使得他“解剖学”考试得以过关。虽然此事查无实据,最终不了了之,但不难想象对鲁迅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日本学者竹内好甚至认为,“漏题”事件(他称之为“找茬”事件)对鲁迅的影响远远要超过著名的“幻灯片”事件。竹内好准确地把握了鲁迅对这两个“事件”的自觉意识,就像《藤野先生》所展露的,尽管“漏题”事件与“幻灯片”事件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学期里,间隔了一个假期,但鲁迅还是有意通过一段“中国是弱国”的议论把两者联系起来。
“中国是弱国”,似乎也表现为中国与日本相比,在掌握“解剖学”知识上存在着明显的“落差”。那位青年学者的论文虽着重于文献的考辨,却也不忘指出1895年5月《申报》报道日本医科中已有“解剖”科目,其背景自然是“甲午战争”,“文章发表于《马关条约》缔结之后”;而青年鲁迅1904年求学于仙台医专,接连遭遇“漏题”事件和“幻灯片”事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两者都与“战争”和“解剖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出于偶然的巧合,是因为“解剖学”知识的发达恰与现代“战争”对“野战医学”的重视互为表里,关系密切。他的“学医梦”可以自由地在“医生”和“军医”之间游走,颇能体现当时日本医学教育之风气。
如果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甲午”前后日本医科的正规化(“医科分目五曰察验曰解剖曰内科曰外科曰目科”),其实是其举国“军事现代化”(后来称之为“总体战”)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媒体各类文章也算做了不少。除了一些应景之作,比较有影响的,就我的目力所及,一本结为《甲午一百二十年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另一本则合成《甲午殇思》(上海远东出版社,2014年5月)。前者学者议论,步步为营不免失之琐碎;后者军人发声,腔调粗豪难免流于意气。不过好处在于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相当明确地显示出仅仅用“战争”来解释“战争”是远远不够的。假如要全景式地了解这场战争及其相关背景,光看媒体文章,显然是不够的,戚其章先生的《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作为一部“全史”,比较详实地描绘了战争前后以及战争过程的全貌。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写一部完整的甲午战争史,斯事体大,无论是资料的积累还是研究的深度,都需要长时间的准备。而戚先生正是利用担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卷》主编的便利,首先在史料的占有和使用上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光引用的第一手史料,就达一百二十余种,使得向以史料见长的日本学者也不能不表示佩服。当然,甲午战争涉及中日双方,如何进一步使用日本方面的史料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问题,宗泽亚先生的《清日战争》(甲午纪念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8月)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著作,正文没有给出任何材料出处的注释,只是在文末列出相关参考资料,但作者声称自己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中收集了大量华语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史料和大量弥足珍贵的图片。作为非专业著作,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就是运用了大量日方的数据和资料,几达事无巨细的程度,甚至连日军炊事班使用什么炊具都一一罗列出来,而书中所附的大量照片,则进一步提醒人们注意战争与摄影术的密切关联,就像书中所说,百年前照相技术的发明,记录了这场战争发生的一幕又一幕。鲁迅与日俄战争期间遭遇“幻灯片”事件,只不过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战争摄影术”合逻辑与合历史的发展……这些相关细节想必会极大地丰富后来者对历史的感知。
然而,历史并不简单地等于细节的堆砌,有时,某些细节的放大和错误甚至会遮蔽对历史的探寻。譬如,在讲述甲午战争的历史时,人们往往会提及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时,虽然铁甲舰威风凛凛,但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发现清朝海军军人在“定远”级军舰的主炮上晾晒衣服,由此得出北洋海军管理混乱、纪律松懈,中日海军如有一战,清朝海军必将不堪一击。这样的“故事”很有戏剧性,也确乎满足了某种自以为是的历史叙述,可在专业的海军史研究者眼中,如此荒谬的说法几乎不值一驳。陈悦(《甲午海战》,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在《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说考辨》一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根据‘定远’级铁甲舰的原始设计图进行测算,其305毫米口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接近3米,而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的长度不足2米(“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口径,主炮属于旧式架退炮,平时为了方便保养,炮管大部分缩回炮罩内,装弹时再将火炮向外推出)。可以看出,攀爬到一个离地3米、长度仅不到2米,而直径接近0.5米(305毫米为主炮的炮膛内径,炮管外径则接近0.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艰难,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而危及生命的可怕事故。纵观‘定远’级军舰,无论是栏杆、天棚支柱均为可以用来晾晒衣服的方便设施,任由北洋舰队官兵军纪真的涣散、智慧真的愚笨,似乎也尚不可能为了晒几件衣服,而甘愿冒生命危险。”面对“甲午战争研究”中类似的比比皆是的错误,难怪马幼垣先生(《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上下),中华书局,2013年3月)要大声疾呼:“海军史科技性高、变化幅度大且速的兵种,研究某时段历史者自当熟悉该时段的海军专业知识,而不应仍采取过去的手法,继续让海军史屈居为政治史、工业史、文化史、教育史等等的附庸”。具体而言,海军是充满技术内容的军种,研究它的兴败,对海军技术的研究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无法想像在对舰船、海战技术知识没有深入了解的前提下,能够对一支海军做出全面的评价。长久以来有关北洋海军兴败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事件、人物本身的探讨上,缺乏严谨的技术史研究以相辅相成,由此导致对于北洋海军失败原因的分析,很多时候都过于强调“人”层面的因素,而忽视或弱化了同等重要的“器”这一层面。可喜的是,这种现象近年来有所改观。姜鸣在他研究清朝海军的重要著作《龙旗飘飘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甲午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8月)特别增收几篇对马幼垣先生、王家俭先生(《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12月)和陈悦著作的书评,就是为了显示“海军史”的视野如何拓展了近代史研究的空间。
对“器”的重视既可能导向“技术决定论”,也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对导致战争的“现代性”逻辑予以反思。由于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现代海军技术和战术发展和变化极为快速,尚未完全定型,因此,发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方胜利、中方战败或许有某些偶然性,而不是形成后来历史叙述津津乐道的“失败必然论”。正如孟悦(《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9月)在《什么不算现代:甲午战争前的技术与文化——以江南制造局为例》一文中提出质疑,为什么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的成败,似乎不仅奠立了当时日本在亚洲的海上军事权威,而且奠定了后人对中日两国历史进程的记忆、判断和断代标准,甚至成为史学家们论证中日之间现代化差异的一个标尺?为了突破这种“失败必然论”,必须重返“科学技术”在中国十九世纪后半的变迁以及由此而生的文化历史断代等方面的问题。其目的不在于讨论甲午战争中中日海军实力的高低,更不在重写中日之间谁“发展”谁“落后”的历史,而是旨在反思这场战争的成败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我们对历史、时间、文化和所谓“科学技术”及其“进程”的阐释,又在多大程度上抹却了我们对另外一种同战争无关的历史发展线索的记忆,即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种理解和组织方式。这种视角不仅关乎搜集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而且关乎如何想象和分析历史和“现代”的诸多问题。比如,战争的胜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有关“现代性”的历史叙述?如果不以甲午战争的成败为准绳,我们是否仍然能够分析历史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种战争决定的叙述到底抹煞、“不算”了哪些历史脉络?
可惜的是,这种由“战争”胜负决定的“成王败寇”、“谁现代谁落后”的论述直至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宰制力量。冬日的香港虽然阳光明媚,却也不时遭遇阴霾,“南京条约”和“米字旗”隐约闪现在“自由”和“民主”口号的背后,不断地提醒人们,有形的战争形态或许远未到来,无形的战争逻辑却一直延续至今……这让2014年关于“战争”的阅读变得更加迫切和艰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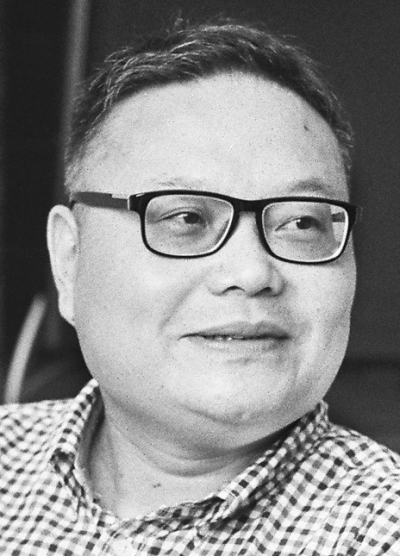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