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万麟:《老而弥妖》
我们拥有共同的根系,有形的自然是复旦,是上海,是相识时特定的年份。无形的又是什么呢?且归于道吧,因为大道无形。我们的心路、我们的感悟、我们的彷徨、我们的困惑,在我看来都有约略一致的来路。
这个班基本的特别处,在于学的是中文,而且是在上海滩、复旦园。本就是中国人,却还要执意学中文,说明我们不满足于说一般的中国话、看一般的中国书、写一般的中国文。对真善美比较懂、有追求,对不真不善不美也容易生气。大学期间遭逢时代的文学热、美学潮,感觉是代表全国人民在深造,我们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激励着我们去关注古今中外美的历程。上海是风花雪月的,复旦是浪漫小资的,跑到那里去学中文,又格外锤炼了我们见雨惊心的敏锐。抱着一段粗腿,即以为全象;拾得一片落叶,乃大呼秋来。兴观群怨,恨不能逢人便说、见鬼就唱。这是一种本领。
陈启松:《我是谁》
大学四年,我才见识了什么是人中翘楚,什么是文化积淀。上海、浙江、江苏、河南文科考分第一名的同学周松林、蔡万麟等人在我们班,上海语文竞赛第一名陈小云在我们班,全国大学书法比赛一等奖获得者王鸣文在我们班……在复旦图书馆浩瀚的书海中,在中文系丰富资料的指引下,我开始了解文学为何物,以及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艺术、文学与美学等一些基本、也很深刻的学术理论问题。
吴俊:《与我的复旦读书有关》
崭新的知识和学术天地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充分展现出来了。为读一本好书而疯狂的事,那时是很普遍的。最壮观的景象就是每天晚饭后,在每个学生寝室楼通往图书馆或教室的校园小道上,总是络绎不绝地匆匆行走着要赶去占自习座位的大学生。只要稍微晚些,图书馆或教室里就不会再有空位了。后来,为免无序的拥护,图书馆开始每天排队发牌子,凭牌就座。这真是一个读书的时代。
我们如饥似渴。每本好书都在同学间引起讨论和流传。这里要着重提到的是李泽厚对我们这代人思想成长的重要性,或者也可以说李泽厚在1980年代的不可替代的思想领袖的作用和地位。他不仅作出了崭新的具体贡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总是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库而发挥影响的。我们这代人是读着他的《美学历程》和那几本思想史论、哲学批判书等,完成我们的大学和研究生学业的。他的书对我们的思想有塑造的作用。
汤建强:《转身之间》
复旦的四年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那么美好和永恒——梧桐树叶飘飞的“南京路”,灯光下宁静安详的阅览室,古老而韵味十足的中文系小楼,迎考时的烦恼和考后的轻松愉悦,周末与兄弟们就着食堂买来的一桌子菜和从五角场用热水瓶打来的散装酒,来一场寒酸而放肆的开心,课后球场上奔跑着的青春身影和寝室之间互不买帐的比赛,还有因青春萌动而半懂不懂地为情感开始的忧郁和伤感……这一个个画面构成了我回忆中的复旦。除了这些回忆和一张文凭,让我真正受益一辈子的东西,在于复旦给了来自农村的我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对图书馆浩瀚的知识感知到了自己的渺小,8011其他92个优秀的同学,也如来自不同地区的标本,从这批汇集的精英中看到了自己的平凡,让我看到以前自己无法看到的风景,听到各种给我启发或者思考的声音,可以沐浴在来自东南西北的风中,让自己自由地感知、思考和汲取,让我年轻幼稚的心智慢慢成长和成熟,让我在今后的人生中独立思考、正确分辨、果敢取舍。这一切因这份积淀而成为可能。
周松林:《迷失在不知所往的旅途》
同寝室的几位室友,性格各异又臭味相投,学业上自然各有用心之处,然各行其是,生活上更是自由散漫,乃至吊儿郎当,四年里闹出了不少笑话,现在想起,还不免让人忍俊不禁。记得当时还有所谓“生活指导老师”,学生中也有“生活委员”,不过连他们也没有摆出管教者的嘴脸,大家各自自在,这样的气氛,合我的口味。我们寝室曾被评为全校最脏乱差寝室,照片张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里,不以为耻,反以为乐,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那种自由探索、胡思乱想的氛围,最是让人怀念。其实,四年里除了个别老师之外,学校课程并没有教导我们,或指导我们认识、思考什么重要的东西。但在那种气氛下,我们有自我教育、自由生长的空间。
不过那个时候,真正能启人思考的书并不多,一册《理想的冲突》已足以引发一场波及面很广的地震。吴寅菁陆续借给我一套四大册《美学》杂志,又偶然得到一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真地、吃力地读着,似懂不懂,自以为大受启发,壮起了思辨的胆气,一些基本概念开始在脑子里盘旋起来,装模作样作思考状。
选自《1980我们这一届》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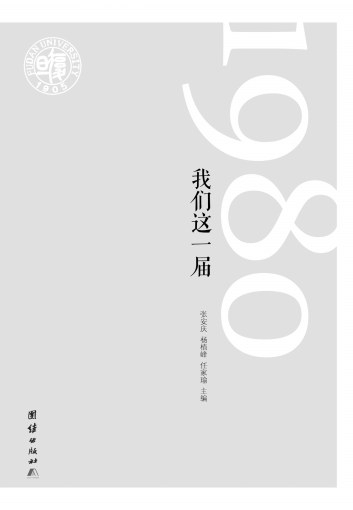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