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三驾马车”之后,河北文学的又一次集体亮相,是被称为“河北四侠”的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他们的创作面对新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既有文学的共性成分,又各具作家自身鲜明的特色,呈现了文学能够带给读者的无限可能性。
谈到河北文学队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导、评论家郭宝亮认为,铁凝是河北新时期文学的一面旗帜。她的创作贯穿新时期文学始终,无法把她归入任何梯队,她的创作具有全国影响。迄今为止,铁凝的创作大致经历了单纯、乐观的“香雪”时期,复杂、混沌的“玫瑰门”时期,生命、本真的“大浴女”时期和综合、浑厚的“笨花”时期。她以无可争辩的创作实绩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最有实力的作家之一。
除了铁凝之外,新时期河北小说创作队伍主要由三个梯队构成,出生于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家贾大山、汤吉夫、陈冲、张竣、潮青、申跃中是新时期河北小说创作队伍的第一梯队,第二个梯队作家是出生于五十到六十年代初的一批作家,主要有何申、谈歌、关仁山、何玉茹、阿宁、贾兴安、康志刚等作家。被称为“三驾马车”的何申、谈歌、关仁山成名于九十年代中后期,他们的小说直面现实,关注国有企业与乡镇的困境,表现出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在当代文坛掀起了一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之后,他们分别转型,关仁山渐渐把主要精力转向长篇小说创作,先后创作出版了6部长篇小说,其中以《麦河》、《日头》影响最大。何玉茹的小说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叙事中表现出一种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注。河北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三梯队是一批出生于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的年轻作家。他们主要有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刘燕燕、曹明霞、王秀云、唐慧琴、常聪慧、梅驿、左小词等。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被称为“河北四侠”,主要是从他们的创作姿态上来考量的。
河北文学的传统是农村题材和现实主义。当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和先锋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河北文学除了铁凝等少数作家之外,并没有适时地跟上来。郭宝亮说,铁凝作为河北文学的旗帜,适时地找到了孙犁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进而走出河北,冲向了全国。然而,河北的其他作家却在坚守传统中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贾大山的农村题材小说,陈冲的改革小说,实际上都强化了河北文学的固有传统。“三驾马车”在九十年代的出现和走红,是现代主义先锋文学落潮之后,人们重新呼唤现实主义的结果,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再次闪烁出耀眼的光彩。
“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这四位作家,在九十年代陆续登上文坛,他们所面对的正是先锋落潮,而现实主义传统异常坚固的实际。他们一开始便秉承先锋文学的流风遗韵,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了对现实主义这个河北文学传统的反叛。”郭宝亮说,来自于坝上草原的胡学文,小说创作最接近现实主义传统。他写了许多的底层人,底层人的苦难、命运的“不公”种种,但这都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奔走”才是这些人的基本存在状态。“奔走”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主题层次,而接近了现代主义。可以说,胡学文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反叛了河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胡学文的写作,多数与故乡有关。故乡与童年于他而言如同土壤之于植物,不仅是胡学文一生难以掘尽的矿藏,而且对他的创作风格有着难以言说的神秘影响。在写作超出故乡题材的作品时,他也常常要返回写一篇与故乡有关的小说,否则就感觉断了根基。“写到乡村,大脑里便会呈现完整的图景:街道的走向,房屋的结构,烟囱的高矮,哪个街角有石块,哪个街角有大树。如果写到某一家,会闻见空中飘荡的气息。”胡学文的写作几乎不需要想象,而是自然而然的呈现。故乡提供了可能,但万物都有两面性,他在利用这些可能的同时也有不安。所以,胡学文觉得,写作需要难度,轻松获得有时对写作是一种伤害,怎么处理故乡经验可能比故乡经验本身更重要。
胡学文的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获第六届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如果说每个人的写作都有自己的敏感点和情感穴位,那么胡学文的“穴位”在“小人物”。在他眼里,人物没有大小之分,他们的身份不过是某种社会标识,如果必须正视这种标识的存在,他须努力写出小人物的大来。这才是最要的。
在郭宝亮看来,刘建东与李浩的创作是以激进的方式,“挑战与冒犯这个现实主义传统。”刘建东一开始就心仪于先锋文学的写作方式,他甚至对现实主义这个传统不屑一顾。他的小说总是在细密的叙述中寻找张力,在荒诞不经中享受模糊,对存在的可能性密码进行着加密和解密的工作。相对于刘建东的激进,李浩简直就是决绝,他傲慢地宣称:“我对现实主义有不可理喻的轻视”。
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有几句略带戏谬的、对柯西莫男爵一生的概括:生活在树上——热爱着大地——最后升入了天空……这恰恰是作家李浩写作的理想状态,他希望自己一生如此。
和大多数70后作家不同,李浩对生活、自我和人生更多是审视和俯视性的,他希望自己是种在树上的观察,这样的位置让他得以不困囿于具体,不因为经历而过于情绪化,却有对大地的爱和悲悯。对李浩的作品有着系统阅读的读者会发现,李浩在小说中从来没有过对任何人的外貌描写。他不允许自己把它变成“自我”或只有单一具体化指向,他写下的是人的内在。他的写作,不仅是一个“我”,而是在书写众人,有着某种普世性,虽然它有强烈的个人面目和个人特点。他迷恋的从来不是自我,甚至对这个“自我”有着小小的厌恶;他迷恋这个世界上所有未知的谜。
《侧面的镜子》《父亲,镜子和树》《镜子里的父亲》……镜子在李浩的写作中成为一个“核心意象”,也是李浩对文学的部分理解。“我把文学看成是放置在我侧面的镜子,我愿意用一种夸张、幻想、彼岸、左右相反的方式将自我‘照见’。”他认同诗人塞菲里斯的一句诗:“如果要认识自己/就必须/审视灵魂本身/我们在镜子中窥见陌生者和敌人……”李浩将此诗视为对写作对镜子的理解的佐证。
作家张楚几乎所有小说的叙事空间都是小城镇。在青年批评家饶翔看来,中国北方小城镇往往被张楚被命名为“桃源县”或“桃源镇”。饶翔评价张楚的“桃源”并无鲜明的个性标识,它灰扑扑,乱糟糟,粗俗、浮夸、暧昧、无聊,带有过渡时期的普遍特征,甚至可以说,它是转型期中国广泛性的生存空间。而在郭宝亮的阅读印象中,张楚的写作是一种诗意写作,令他不时想起诗人海子,那个忧郁的、怆然的、撕裂的诗人海子,他在对生命对存在的深刻的体验中联通了张楚。忧郁、难于排解的忧郁和哀伤同样构成张楚小说的基调和底色。这种基调与底色,成就了张楚的先锋品质,但张楚的先锋与早期先锋派小说不同,早期先锋派小说基本属于观念写作,而张楚是属于生命的体验写作。“我不了解张楚的实际生存,但我在他的小说里读到的是一种源于生命生存本身的忧郁和哀伤,这是一种接通了地气的有活力的忧郁,一种源于血肉的文字舞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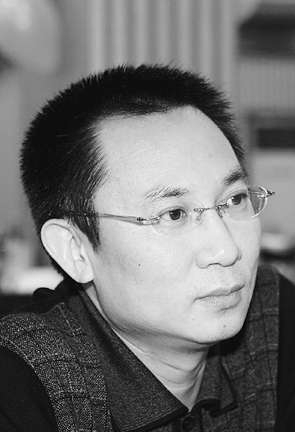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